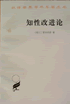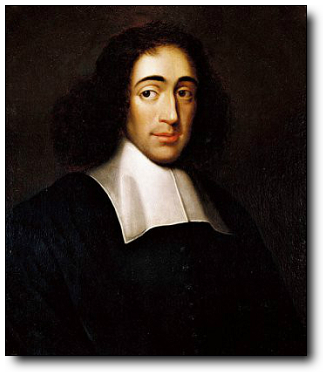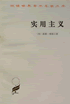 |
编号:B86·1970315·0359 |
| 作者:(美)威廉·詹姆斯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79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13.80元 | |
| 页数:224页 |
威廉·詹姆士对“实用主义”作过如下定义:“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和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元诗等等。”这是威廉·詹姆士试图对哲学的难题进行解答,试图以实践的方法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真理这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既然是抽象名词,当然要求抽象地为人所承认,但是各种具体的真理就只有在被认为是方便的时候才需要承认。
——《第六讲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真理如何命名一种存在?它是一种观念还是一个事实?它是在一个已经确定的永恒世界里,还是在不断确认的认识过程中?它指向的是经验主义的实在,还是指向理性主义的纯粹?而当真理只是一个以大写T开头的词,一个单数的词,一个抽象的词,是不是会永远陷入到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中?
形而上学的争论,是关于“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一只树上的松鼠,一个树下的人,他们在相互对立而不可见的两面,这个两面制造了这样一种争论:人是绕着树看那松鼠,但是松鼠总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到他的反面去,也就是说,人和松鼠总是隔着不可见的那棵树,所以最后被争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人是否绕着松鼠走?或者说当人绕着树在走,松鼠绕着树在跑,是因为人绕着树而追着松鼠,还是松鼠绕着树追着人的反面?
对于这争论的问题,威廉·詹姆斯给出的方法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所谓的“绕着”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松鼠在从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再到北面,在一种循环中人就是绕着它跑的,因为人也完成了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人先在松鼠的前面,然后再到右边,再到前面再到左面,当回到前面完成一个循环的时候,就不是绕着松鼠跑了,相反,而是松鼠绕着人在跑。所以在这两种差别的解释里,詹姆斯很明确表示:松鼠和人都是在相对运动,那个这个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又对又不对”的解释是缓和了争辩,但是缓和是不是消除?詹姆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折中,或者是一种妥协,找出矛盾中的差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实践,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从所谓的真理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是被一棵树挡住而对立成了两面,因为对立面就可能建立起了不同的原因体系,是先有人跑这个原因而导致了松鼠绕着跑的结果,还是先有松鼠跑的结果才导致了人绕着跑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争论的产生就是把人和松鼠放在了不同原因下,当一个问题被放置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中,它永远是被争论的,而詹姆斯的态度很明确,这种争论需要的是调和,需要的找出差别,而实用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最本质的意义就是给出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的任何一对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可能适用于又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是无止境的。”很明显,实用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争论的终结者,就是把无止境不同原因的现象放置在一个必然要终结的体系里,当终结的时候,一还是多,宿命还是自由,物质还是精神,就没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的确,在詹姆斯的观念体系里,哲学就是遭遇了“两难”,哲学是什么,他认为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多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悟”,感悟是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而个体具有不同的气质,它是崇高的,也是平凡的,它鼓舞我们的灵魂,它又制造疑惑和劫难,它能照亮世界的前景,但是它有时又常常让我们讨厌。而在这种气质主义下,哲学就呈现为两难,詹姆斯把相似的对比用两个名词来概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是对于信仰抽象和永远原则的态度,经验主义是对于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观点;理性主义者赞成所谓的意志自由,经验主义者是一个宿命论者;理性主义具有宗教性质,但它不解释具体的世界,“同具体的事实和快乐与痛苦,毫无实际接触”,经验主义是和具体事实的经验有关,但是又带有非人本主义和非宗教色彩;理性主义具有高尚纯洁的特色,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指向的完善变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经验主义者常常关注单独的、实际的特殊的事物,甚至是那些可怕的纷乱、惊奇、暴虐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粗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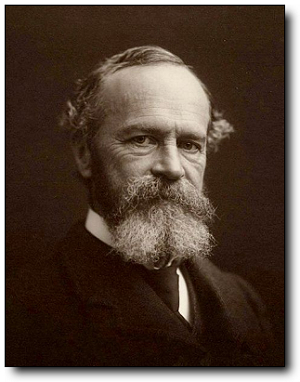 |
| 威廉·詹姆斯:人其实是绕着实用主义在跑 |
一种是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种是悲观主义的;一种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无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意志自由论的,一种是宿命论的;一种是一元论的,一种是多元论的;一种是武断论的,一种是怀疑论的……而把这哲学上的两难区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划分?詹姆斯也说到了这种区分方法,“哲学是充满了种种精微的推理、剖析和审慎,哲学领域里有各种结合与转变,现在却把它的冲突场所说成是两种敌对气质的横冲直撞的混战,这是多么无情的讽刺,竟把最高级的事物用最低级的表达方式说出来:这是多么幼稚的皮相之见!”但这是所谓哲学专业人士的批判观点,而把哲学“粗鲁”地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詹姆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完全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调解——似乎越是粗浅,越是粗鲁,越是“难以饶恕”,就越能体现实用主义的意义,因为,他说:“我提出这个名称古怪的实用主义作为可以满足两种要求的哲学。它既能象理性主义一样,含有宗教性,但同时又象经验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关系。”
“我所描绘的图画不管如何粗俗简略,却完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才是真正具有真理性质的观点,才能认识世界的本真,才能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刹车而走向终结。实用主义从希腊词派生而来,意思是行动,是实践,引用德国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就是:“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对我们说来,那影响就是实在的意义。”实践而实在,就是把一切的理论都变活,在詹姆斯看来,实用主义本质上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注重特殊事物上,它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而在抛弃形而上学抽象问题上,它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就如副标题,实用主义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但是,让旧思想穿上新外衣,并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置换,而是给所谓的哲学难题找到活起来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差别论”,就如“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的这个形而上学争论,其真正的差别就是每种说法背后的原因,而差别最后的作用是消除无休止的争论,找到最后的终点:“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它走在最后,所以它是目的论的,而这个目的就是真理,就是那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并把它从抽象名词变成一种具体的存在,“因此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
实用主义为什么会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实用主义是关于实践、实在的方法论,在詹姆斯看来,不论是具体的物质实体,还是与思想、感觉、灵魂有关的“精神”实体,都是实用主义的对象,也是实用主义的主体,而且用实用主义考虑形而上学问题,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用主义者看见的是一个通向无限的上帝。“我个人相信要证明有上帝,主要乃在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当这些经验使你相信你有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最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在这里个人经验主义中的上帝取代了那个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不仅是一种“有神论”的现实实践,“如果我们的信仰把它具体化起来,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东西,它便成为一个有希望的名词了。”而且,也取消了唯物主义的意义,在詹姆斯看来,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世界已经完成,另一部分的世界没有完成,完成的世界里,不论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世界已经发生而且完成了,寻找原因就没有了意义,重要的是未完成的世界,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会毁灭的,也就是说最遥远的那个宇宙的终点注定是走向毁灭的,这种毁灭无法保证我们理想的利益,无法实现遥远的希望,所以,“这种完全的最后破裂和悲剧就是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
也就是否定了世界的唯物性,而只有上帝,可以“保证一个理想的秩序可以永久存在”,也就是说,只有有神论才能保证永恒性,而实用主义在自己内在经验中树立的那个上帝就是把希望带进经验中,“对于将来便有一个更可相信的看法。”所以,实用主义的本质是向后看的,看到在事实之上永久存在的“庄严高尚的东西”: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詹姆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让实用主义成为一种统一体,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无论是高尚还是低微,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只有用实用主义的这种折中、功利、甚至妥协,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这种调和在《一与多》里有了进一步的阐述,一元论和多元论,也是一种争论,但是其实在詹姆斯看来,一与多只不过是不同的立场而已,就像人和松鼠的争论一样,“世界是一”其实不是起源论,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目的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在这个目的下有多元的可能,但是这一切的多只是系统的组成方式,它是相互依附、相互连接的宇宙,而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就在一个目的中“为他讲一个故事”,而这个统一成整体的目的论就是实用主义:“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着人类不断的努力而组成的联络系统,世界正日益统一起来。”
这种统一性,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它吸纳了常识,在“永远是不完整的,时有增损的”情况下,实用主义把新事物加进去,从而形成新的经验,与就真理结合之后、互相修改之后,就变成了趋向最终结果的新真理;实用主义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因为,“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在以内在经验形成上帝的过程中,实用主义又具有了宗教特色,因为是趋向于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把不完整变成完整的整体,所以它是改善主义的,和宗教一样,它最终是为了终极的善,“只要你承认宗教可以是多元的或仅仅属于改善性质的,实用主义就可以说是宗教性的了。”
实用主义是对于常识的统一,但是一种人本主义,是具有宗教特色的,所以实用主义必然是一种真理,“真理是善的一种”,这种善也是真的,“凡在信仰上证明本身是善的东西,并且因为某些明确的和可指定的理由也是善的东西,我们就管它叫做真的。”实用主义的真理性在詹姆斯看来,更重要的意义是观念和实在的“相符”,只有相符,它就是在临摹实在的——具有经验主义的特色,而且,实用主义的真观念是一种“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的”观念,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永远面向将来,这就超越了面向过去的那个理性主义。
取代经验主义,超越理性主义,变成上帝,变成真理,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是作为一种主体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以大写T开头、单数、抽象名词的真理,在统一了逻辑与崇高、事实和经验,统一了神秘和实用、物质和精神,统一的一和多、宿命和自由,也统一了绕着松鼠跑的人和绕着人跑的松鼠,最终在世界的最末端找到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甚至找到了不再引起争论的那个上帝:“实用主义愿意承认那生活在污浊的私人事务里的上帝——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上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