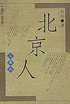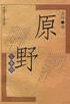 |
编号:X26·2000519·0524 |
| 作者:曹禺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180页 |
受奥尼尔《琼斯王》的影响,《原野》创作于1937年,这是一部关于复仇的戏剧,焦大的命运是悲剧,他选择盲目的报仇,最后却付出成倍的代价。这部人物不多,情节不复杂的剧本却是曹禺最受争议的一部。另外,仇虎杀死大星后逃进森林中的心理活动,堪称30年代心理戏剧的经典。
仇虎 (苦闷地)不是我要想,是瞎子,是小黑子,是大星,是他们总在我眼前晃。你听,这鼓,这催命的鼓!它这不是叫黑子的魂,它是催我的命。
——《第三幕·第二景》
谁在叫魂?谁在催命?夜半一时的黑林子里只有深邃的树丛,夜半二时半的土坡上只有被雷火殛死的老树,夜三时的野蒿里蛙声骤然停歇,而在破晓的六点钟,大地依然莽莽苍苍,可是分明看见了明明灭灭的红灯,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鼓声,看见和听见,让黑暗的林子变成了另一个恐怖的舞台,仇虎说:“这简直是到了地狱”,焦花氏说:“天是没有眼睛的。”看是看见生命的恐怖,听是听见死亡的呐喊,对于一个杀了人、沾满血的复仇者来说,恐惧到底来自何处?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巨树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无声震动着翅翼,地面昏暗地升腾起灰舞,秋幕覆盖着老屋,一切都是沉寂而苍老的。在这巨大的原野里,藏在里面的生命如何找到一个呼吸的出口?这生命是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的巨树,“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这生命是垫高了路基上用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铁轨,“铁轨铸得像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霭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这生命也是孤独的老屋里点上的“红红的灯火”。而真正打破沉郁大地的则是复仇者仇虎的出现。
“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不哼。”这是仇虎到来的形象,叉腰、仰望、沉默,其实在内心来说,隐含着巨大的力量,当他用石头掷落到野塘里,那种沉郁的氛围就被打破了,“他狂喊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像住铅块,失望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伤着脚,戴着镣铐,肉身被一种沉重所束缚,他的喊叫就是要彻底将这种沉重的压抑破解。但是对于一个逃犯来说,暂时的自由并没有解除身上的桎梏,但是当他用凝聚起来的力量呐喊的时候,体验的就是一种生命的爆发力。
仇虎无疑是生命被摧毁的代表,十年前自家的地被焦阎王霸占,父亲被绑架,因无法凑足赎金,父亲被杀死,妹妹则被卖到了妓院,十五岁的姑娘活活被人折磨致死,而自己,则是被送进了牢笼,还被打断了腿,甚至,已经许给了自己的焦花氏又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所以对于仇虎来说,这不仅是个体生命被摧毁,甚至是整个家族的仇恨。所谓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当仇虎在牢里弟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便走上了复仇之路。
但是家族和个人的复仇计划对于他来说,却变成了一种遗憾,因为焦阎王已经死去。当复仇的对象不在自己手上死去,那种折磨他、看着他慢慢痛苦死去的畅快感就不复存在,甚至连复仇本身也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当仇虎遇到白傻子听说焦阎王早已归天之后,遗憾变成了愤怒:“可他——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藏在这个地方,成年地想法害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当积蓄了所有力量回来,却变成了迟到的复仇,甚至是缺席的复仇,对于仇虎来说,他似乎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
这便是另一种复仇的开始。而这新的复仇似乎比杀死焦阎王更复杂,焦阎王虽然已经死去,但是还有焦阎王的妻子,还有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还有焦大星的媳妇焦花氏,甚至还有他们的孩子大黑子,焦家的三代人似乎又成为新的家族序列,当自己的一家人被焦阎王害死,似乎可以以血还血的方式完成复仇。但是这却并非可以简单地进行报仇雪恨,因为焦花氏是自己曾经喜欢的女人,而焦大星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友,虽然懦弱但是人并不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焦大星也是焦阎王恶势力统治的一个牺牲品,他娶了焦花氏,但是焦花氏并不爱他,而且焦母和焦花氏不和,甚至两个女人明争暗斗。对于焦花氏来说,在这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婚姻里,她有着最原始的反抗精神,而焦母为了维护秩序,以另一种强力来约束甚至压制焦花氏,在焦花氏的反抗中,她甚至刻出了木头人,偷偷用针扎的方式诅咒焦花氏。
所以当仇虎闯入焦家开始另一种复仇的时候,他必定会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在十年之后重新见到了心爱的女人,渴望和她远走高飞,另一方面,内心积蓄的复仇火焰会寻找另一个替代者,一种是爱,一种是恨,矛盾的交织,其实最后的复仇像是被动推向了矛盾的顶点,他和焦花氏偷偷打算好了复仇之后的生活,却被焦母发现,而焦母告诉了焦大星之后,深爱着焦花氏的焦大星却又产生了属于他自己的仇恨:那就是自己爱人的背叛,那一刻,焦大星从懦弱变得愤怒,甚至将一把尖刀插向了桌子,“我要杀了他!”所以仇虎回来复仇,自己反而也成为焦大星复仇的对象。
爱与被爱,复仇而成为被复仇者,在这种交织着矛盾的世界里,仇虎对于复仇的强烈欲望又压过了和爱人逃离的想法,但是在空缺了焦阎王的现实里,一心想要复仇快感的仇虎终于对准了焦大星,在他看来,父债子还是正常的事,“这次我明地来不暗地里走。我仇虎憋在肚里上十年的仇,我可怜的爸爸,屈死的妹妹,我这打瘸了的腿。金子,你看我现在干的是什么事。今天我再偷偷摸摸,我死了也不甘心的。”内心只有恨,只为一个复仇的目的,焦大星已经不是他曾经的好友,完全变成了新的仇人。但是这种复仇的合理性到底在哪,连焦花氏也反问他:“可是阎王死了。”而当求胡说:“阎王死了,他有后代。”焦花氏再次提醒他:“阎王后代没有害你。”
一个连蚂蚁都不肯踩死,一个拿着尖刀就颤抖的人,也被无情地卷入到这一场家族恩怨中,仇虎的那一句“我对我爸爸起过誓,(举拳向天)两代呀,两代的冤仇!我是不能饶他们的。”将他推向了死亡,而这个复仇的链条也并没有随着焦大星之死二而断裂,当小黑子被放在床上,当焦母的铁棍砸向他的时候,另一个无辜的生命也停止了呼吸。当仇虎看见自己满是鲜血的手,完成的复仇里却在颤抖,“我的手,我的手。我杀过人,多少人我杀过,可是这一双手,头一次是这么发抖。活着不算什么,死才是真的。他连哼都没有哼,闭上眼了。人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值的东西,一把土,一块肉,一堆烂血。早晚是这么—下子,就没有了,没有了。”
当复仇最后变成了眼前的一摊血一堆肉,对于仇虎来说,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开始。十年之后的复仇对于仇虎来说,更像是一种象征,只有亲自制造一种死亡,才能让自己解恨,可是那墙上挂着的焦阎王,似乎用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当仇虎满腹仇恨地要让焦阎王看着自己回来,焦花氏却出现了幻觉:“阎王,阎王的眼动起来,——他,——他活了,活了!”当杀死了焦大星,仇虎又抽出手枪朝阎王像连发死枪,掉落的相框似乎在表明焦阎王已彻底死在自己面前。可是因为仇恨制造新的仇恨,对于仇虎来说,却变成了煎熬,变成了痛苦,变成了无法抹去的阴影。
仇虎带着焦花氏逃奔,是为了去那个黄金铺满地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相爱,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神秘、深邃的森林里,生命却以死亡的方式让他们进入到了恐惧的世界中,“这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于是森林里到处蹲伏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里伺藏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风来时,滚来滚去,如一堆一堆黑团团的肉球。”是看到了背后一直跟着的红灯,是听到了总是不绝于耳的鼓声,当焦花氏说起大星,说起小黑子的时候,仇虎陷入了某种恍惚中,而这种恍惚让他从复仇的深渊中渐渐爬起来,但是又一种强大的力量将他推了下去,生命之死,要用另一个生命去偿还,仇虎无疑制造了新的仇恨,“啊,大星,我没有害死他,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而他寻找解脱的理由依然是焦阎王作恶多端上:“大星!我们俩是一小的好朋友,我现在害了你,不是我心黑,是你爹爹,你那阎王爹爹造下的孽!小黑子死的惨,是妈动的手!”
焦大星是焦阎王“造下的孽”,不管是善良还是邪恶,不管是懦弱还是勇敢,必须为缺席的仇人填补位置,但是红灯、鼓声以及咒语总是阴魂不散,对于仇虎来说,则变成了一种新的折磨,丧失理智的复仇,却也使得他丧失理智地出现了幻觉,从夜一时半到破晓的六时,在无法走出的黑林子里,仇虎看见了撑着伞的神秘蓝布人,看见了直瞪着他的焦母人形,看见了自己死去的父亲,看见了那些帮他越狱的囚犯,而最后看见的是审判的阎罗。
没有星光,没有人声,如死寂的黑暗中,仇虎其实希望在阎罗的审问中得到彻底的解脱:“我仇虎生来是个明白人,死也做个明白鬼。要我今天死了,我死了见了五殿阎罗,我也得问个清楚:我仇虎为什么生下来就得叫人欺负冤枉,打到阎罗宝殿,我也得跟焦家一门大小算个明白。”这是他寄予的最后希望,当牛头马面两边排,当阎罗做中间,当仇虎将焦阎王的罪恶一一陈述,最后却依然是现实的翻版,仇虎的父亲和妹妹被宣判,而焦阎王却得意洋洋,最后仇虎才发现,阎罗就是焦阎王:“好,好,阎王!阎王!原来就是你!就是你们!我们活着受尽了你们的苦,死了,你们还想出个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想出这么个地方来骗我们!”
阎罗审讯当然是幻觉,对于仇虎来说,却希望是一个公平的结果,但是当自己杀了人,何来公平?而对于仇虎来说,家族的恩怨压在他个体上的时候,这种仇恨或者已经变形了,十年的等待最后得到了机会,从此便是不计成本地要达到这个目标,当焦阎王已经死去,复仇失去了意义的时候,他又在家族的仇恨中为无辜者送葬,而不管是自己家人生命被摧毁的仇恨,还是焦大星和黑子命丧自己之手,都是无法从仇恨的链条中挣脱出来,而对于仇虎来说,真正横在面前的并非是一个死去的焦阎王,而是那个无法得到公平、获得自由的社会,是那些悬赏他的巡警队,是套在他身上的桎梏,是父债子还的宿命。
但是,破晓的天际有一把火,烧起了一道红光,当经历了噩梦的他们走出鬼魅的黑森林,站立在原野铁道旁,看见的“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也将延伸到更遥远的地方,“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焦花氏无疑是仇虎在生命最后时光里看见的希望,连同他肚子里的生命,延续了仇虎的另一种生命。“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焦花氏在仇虎枪声响起的时候走向了黄金子铺的地方,就是走向一种新生,那或者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但是由仇虎的希望支撑,那一定是另一个开始。而仇虎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金子!孩子生下来,告诉他,他爸爸并没有叫这帮狗们逮住。告诉弟兄们仇虎不肯(举起铁镣)戴这个东西,他情愿这么——死的!”
不是重新成为不公平世界的牺牲品,当他把匕首插进自己的心口,他选择了死亡,这不是屈辱,而是饱含着希望,饱含着爱,一个人也许在这个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当他看到焦花氏的背影消失,在更密的枪声里,“忽然把铁镣举到眼前,狞笑而快意地——哼!”挣脱了十年来套在身上的铁镣,就是挣脱了一生的桎梏,“仇虎的尸身沉重地倒下。”在沉郁的大地上,在深邃的原野中,他就是那一棵经历了折磨,遭受了痛苦的巨树,“巨树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