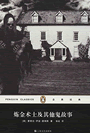 |
编号:C38·2151109·1230 |
| 作者:【英】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 著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26.20元亚马逊12.10元 | |
| ISBN:9787532152407 | |
| 页数:197页 |
著名恐怖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说:“老派的鬼怪惨白庄严,主要通过视觉进行展现,而詹姆斯笔下的鬼怪一般都是消瘦、矮小,而且毛茸茸的——一种迟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怪物,处于野兽与人的中间地带——而且常常在被看到之前,就会被触碰到。”消瘦、矮小、毛茸茸,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笔下的鬼故事多与宗教及历史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的真实感,而主角一般是考古学者,他们往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这样一种错乱的氛围里,鬼怪故事更具有一种颠覆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收录《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失去的心脏》、《铜版画》、《白蜡树》、《第十三号房间》、《马格纳斯伯爵》等故事。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来的到底是谁
十四号房间旁边的是十二号房,也就是他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什么十三号房间。
——《第十三号房间》
十二、十三和十四,是一个完整的序列,是一个系统的秩序,可是当十四号房间的旁边却只是十二号房间的时候,当十三号房间变成一个虚幻的数字的时候,序列和秩序就开始混乱,而这种混乱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避讳,也并非是顾客拒绝而进行的调整,而并非是关于数字的消失,它一直存在,它偶尔出现,最后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变成了现实之外的一种可怕现象——甚至它以必然的方式闯入和改变那个完整的序列。
十三号成为避讳的数字,这是一种非常常见、“普遍且强烈”的现象,它甚至成为了在宗教以外,却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现象,但是在我的表弟安德森那里,却变成了好奇,“他打算问问老板,是否他以及他的同行们真的遇到过很多拒绝住在十三号房间里的顾客。”因为好奇,便以闯入的方式进入了神秘的数字世界,对于安德森来说,十三号房间却是被看见的,以及被听见的,白天那房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令人联想的数字,而且靠近房门的时候,却听见了里面的脚步声、说话声,一种存在的正常声音。但是令人恐惧的却是,这种声音只是听到,那个房间上的数字只是白天看见。而当夜晚来临,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十三号却完全变成了诡异事件。
安德森居住的十二号房间长度缩短了,高度增加了,以前一直忽视的旅行箱现身了,这一系列的变化或者可以归因于安德森自己的某种主观感受,是一种“似乎”发生的故事,但是当他在睡觉前将烟头熄灭在三扇窗户的最右那扇,却在第二天发现烟头在中间那扇——两扇窗户变成了三扇,烟头移动了位置,而且这完全是确定的事,“他可以发十次誓,保证自己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右手边的窗户旁抽烟。”因为太确定,所以会很恐怖。夜晚抽烟时看到旁边的住着的是女士,但是第二天却发现变成了男士,而那个男士的惊奇在于,安德森以为房间里发出的噪音是男士所为,而实际上,男士没有发出过声音,他以为声音来自隔壁房间,也就是安德森居住的房间。
是男士而非女士,中间的烟头而非右边的烟头,那声音来自何处,那窗户为何神秘增加?甚至在他们一起看见的时候,十二号的旁边是十四号,十四号的旁边是十二号——消失的十三号去了哪里?神秘之物的最恐怖指出不是因为消失,而是因为出现,“此刻詹森正背对着房门。这时门开了,一条手臂伸了出来,抓向他的肩膀。那手臂包裹在一层破烂发黄的亚麻布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十三号房间了的门开了,十三号房间突然出现,十三号房间伸出一只手,被包裹在亚麻布里,长着长长的灰猫,不是安德森的手臂,也不是詹森的手臂,当避开了那只手用工具敲开十二号和十四号中间的那堵灰墙的时候,十三号的世界才被真正打开,“他们在支撑木板的横档之间发现的是一个小铜盒。里面有一份折叠端正的羊皮纸文书,上面写着大概二十行字。”
不认识的文字,不知道的意义,不设防的秘密,就像十三号这个数字一样,把所有人都推向了神秘的想象中,却并不完全在想象中,它变成了一堵墙,一只手,一份羊皮纸,一段文字,想象终于变成了真实存在,而这个不被破解的故事最后却以档案收藏的方式进入了博物馆。这是一种对于神秘的压制,或者对于未知的封闭,它看起来是以消失的方式远离了现实,可是十三号房间的神秘意义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一天,它又会以诡异的方式再次被唤醒。
 |
|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对超自然天生的热爱 |
唤醒是打开,是看见,是亲历,而那十三号房间也会变成剪贴册,变成铜版画,变成白蜡树,变成金属哨子,而所有的唤醒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现实以有限的方式打开了封尘在博物馆、教堂以及古老羊皮纸上的那些文字,那些故事,那些手,那些想象。在《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英国人丹尼斯通就是在“一本奇书”里看见了神秘和恐怖。那个负责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作为教堂管理员,似乎就在这个神秘世界里,他以两百五十法郎卖给丹尼斯通,是要逃避那本书中的诡异图画,而丹尼斯通购入这本图册的目的是研究。研究是需要深入其中的,最后页码里的那张照片,照片草图里的拉丁文,都是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是被封存在那里,但是当被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或者再不能被合拢了。照片里那个可怕的躯体终于在丹尼斯通放下十字架的时候,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在极短的一瞬间,他已经看清了那只手。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粗糙的黑毛,比任何人类手上的毛都要长;手指顶端长着尖锐的指甲,指甲朝前屈伸,灰色、粗硬并且弯曲。”和画中的一模一样,它出现便是复活。而在《铜版画》里,这种复活是被看见。那一张第九百七十八号的画作描绘的是本世纪早起的宅邸景观,但是当以收集艺术品的名义看见这个惊险故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见证者。
一开始,画面上有一个小黑点,有一个男人,以及衣服包裹着的头,但是后来无名宅邸前面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全身裹在一件奇怪的黑色衣服里,背上则有一道白色十字架。”再后来,画面中有了月光,大门左边的一扇窗户也被打破了;再后来,月亮底下,出现的是一个孩子……一张本来处于静止状态、已经被定格的铜版画,却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见证者面前,却变幻出种种不同的内容,甚至这种内容本身也变成了运动状态。运动意味着即时性,而在这种现在时的复活却指向了历史的一个谜团,而在追溯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复活的就不仅仅是想象,而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家族的最后一名继承人失踪,他的父亲在彻底隐居之后,最终也在三年之后被人发现死在画室中,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的人是抱着一个婴儿一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个历史悲剧的密语,而这个谜团带来的不仅是隐居的父亲的死亡,也在一种阴谋中将另一个可怜的人变成了牺牲品,“可怜人啊!他是家族的最后一支血脉啊,有种家族最后的希望的那种感觉。”
现实是为了复活历史,看见是为了揭开谜团,在《白蜡树》里,一个历经三代的谜案最后浮出水面,也是被看见,当那个神秘的树洞被破开,当干枯树叶以及垃圾焚烧之后,当白蜡树最后着火而化为灰烬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在这蜘蛛巢穴靠近宅邸墙壁的那一边,蜷缩着一具人类尸体,或者说是骷髅,尸身的皮肤已干枯,紧贴着骨头,依稀还有些黑发残留。”这是一具女尸,而且已经死了五十多年的女尸,而五十多年刚好是距离第一代的马修爵士把怀疑的马瑟索尔夫人送上断头台的时间,因为白蜡树里跳出一个野兔一样的怪物,继而钻入马瑟索尔夫人家的那个洞里,马瑟索尔夫人便被审判并施以绞刑。“宅邸将有宾客至。”这是马瑟索尔夫人临死前说出的话,而这也印证了这个家族之后的莫名死亡,小马修爵士时代的家畜纷纷死去,理查德爵士本人全身发黑而死去,似乎都是马修爵士时代那次不公正审判的结果。而最后在树洞里挖出的五十年的女尸,以一种恐怖的状态将历史的谜团完整揭露出来。
这似乎就是一种事关道德的报应。鬼之为鬼,是在人世之外的,也是在现实之外的,甚至是在复活之外的,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从现实又返回到那个现场,所以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笔下的鬼怪是联系着历史和现在,它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对于历史的谜案做出回应。《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的那句拉丁铭文里写道:“圣贝特朗如何解救一个被恶魔追杀的人。”圣贝特朗是教堂,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这些历史的文本,发现这些历史的谜团,就是希望用宗教的某种力量来实现道德的平衡,所以在鬼怪的报复中,那些像恶魔一样的人也遭到了必然的报应。那个令人恐惧的骷髅只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承受煎熬的一种写照,“所罗门王与夜魔之争。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绘制。《短歌》。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诗篇》。无论谁居住( 91)。圣贝特朗放出恶魔,望我厄运当头。1694年12月12日首次见到此物:很快我将最后一次见到它。我有罪,也已为此承受痛苦,还有很多痛苦等着我。1701年12月29日。”有罪,痛苦,最后是在这样的恐惧中“安睡时突然暴毙”。
而在《失去的心脏》里,这样的因果报应更加直接,作为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第一篇以浮土德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很明显指向的是对罪恶的惩罚,林肯郡中心的奥斯沃比大宅里,有过一个小男孩的失踪,也有过一个小女孩的失踪,而当孤儿斯蒂芬·艾略特来到这里寄养在表兄阿布内先生的大宅里的时候,他其实也面临着和曾经失踪的小孩同样的命运,而他的到来在另一方面却见证了真相。池塘彼岸传来的古怪叫声,路边走过来的男孩与女孩,都让斯蒂芬·艾略特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但是最后却反而是阿布内先生的死去,“他双手举起站在那儿,显露出了一片可怕的景象:他的左胸上有一个黑漆漆、大开着的口子。”一个开着的口子,是心脏失去的地方,而两个孩子的失踪就是被掏出了心脏,甚至斯蒂芬·艾略特也面临着这样的死亡,所以最后的报应揭开了这个被隐藏的罪恶——因为阿布内相信只要食用不少于三个二十一岁以下之人的心脏,就可以超越控制我们的神力等级,“能够飞翔、可以隐身,还能变成任何他希望的形状。”这种为了精神释放和升华,为了摆脱人类正义约束的力量,为了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本领,阿布内先生采用了这种罪恶的实验手段,并且最终按照计划将魔爪伸向斯蒂芬·艾略特。
“阿布内先生被发现坐在椅子里,头后仰着,脸上笼罩着一层愤怒、惊恐以及凡人的痛苦表情。他左胸上有个可怕的撕裂伤口,心脏暴露在外。他双手无血,桌上的一把长刀也光净如新。”但最后,罪恶的阿布内先生却以相同的方式被杀死,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和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人物一样,和白蜡树下的尸体一样,无非在循环中建立起一种轮回的宿命,无非是解救被恶魔追杀的人。而《施展如尼魔咒》里,这种因果报应似乎更为明显,气量极小、从不宽恕他人的卡斯维尔先生,仅仅因为约翰·哈灵顿批评他的作品就“施展如尼魔咒”将人置于死地,而这次邓宁又将他的稿件退回去,所以他开始制造“允许他三个月时间”的阴谋,但是邓宁和约翰·哈灵顿的弟弟识破了他的阴谋,最后趁他不被又将那张魔咒的纸条放进了卡尔维尔的卡片夹里,“必须有一种方法,由他将纸条送出去,而且对方接受了才行。”这是一个从恶到恶的循环,当指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被魔咒束缚的不是邓宁,而是他自己,“二十三日下午,一个英国游客在查看阿布维尔的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正面时,被一块从教堂西北塔楼周围竖起的脚手架上滚落的石块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如尼魔咒和《失去心脏》里的那把刀一样,成为一个报应的工具,但是阿布内先生为什么会死,谁握着那把刀挖走了他的心脏?“伤口可能是一头凶残的野猫造成的。”不是复仇的人,是更神秘的动物,就像《白蜡树》里一样,是那一只野兔还是那一只蜘蛛?而这些无非都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命名的鬼,那些几乎都长着长长的毛发的东西,构成了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比较单一的鬼形象。而其实,对于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来说,鬼的神秘、可怕并不是要承担道德的力量,他们惩处恶人只是更可以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古老的大宅和教堂、寂静而黑色的夜晚,一个人的房间,都为鬼的出现和复活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想要达到的效果,“依我看来,另一个必要元素是,其中的鬼怪必须是可怕而充满恶意的:可爱的或者助人为乐的鬼怪很适合童话以及民间传说,但对于一个虚构的鬼故事而言却毫无用处。”可怕而充满恶意,是为了更好地在故事里进行虚构,而这种效果并不是为了道德、宗教意义,“这些故事本身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如果其中任何一篇让读者夜晚走在孤寂的路上时,或者后半夜坐在行将熄灭的炉火边时,感受到一丝愉悦的不舒适,那我写作它们的目的便已达到了。”
“一丝愉悦的不舒适”,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而这种悖论或者就是鬼故事的一种巨大魅力,这是人对于神秘的超现实力量的一种虚构,他越是害怕越是要走进,“我认为每个人对超自然话题都有种天生的热爱。”所以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鬼故事里,这种感官的愉悦和不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那只“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的手,《铜版画》里那个“只有一个惨白的、如穹顶般的额头,以及几根散乱的头发”的人,《白蜡树》里“通身长满灰色的毛发”的无数蜘蛛残骸,《第十三号房间》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的手臂,都给人“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那个《“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里那个在圣殿骑士分堂的遗址上发现的哨子其实和宗教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它被发现而复活,复活而带来恐惧,“他看到原以为是空床的地方坐起了一个人形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跳出了自己的床,奔到了窗户前,那里躺着他唯一的武器——那根这是他采取的最糟糕的行动,因为床上的那东西,突然以柔滑的动作,从床上滑了下来,伸张着双臂,占据了两张床之间的位置,正好对着门。”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没有宗教里的亵渎,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哨子,却变幻出一个恐怖的形象,而当上校将哨子扔进大海深处,旅馆里只不过升起了一股浓烟而已。
“来的到底是谁?”这是在哨子上刻着的字,在封尘的历史中,在被记载的文本里,在传说的故事里,复活意味着闯入,闯入就是到来,但是“来的到底是谁”的疑问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未知,无论是恶人还是后人,无论是见证者还是发现者,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揭开埋藏的谜团,不是为了抵达真相,只是为了带来“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这种“愉悦的不舒适”甚至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看来,不是在一次性的揭秘和阅读中体验到的,他期待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得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些剪贴册,那些铜版画就像自己的这些鬼故事文本一样,被保存起来,无论是送到博物馆,还是拍摄成照片,似乎就是为了重复阅读,为了永恒保存,因为不管来的是谁,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打开,看见,就是复活,就能获得“一丝愉悦的不舒适”,就能在超自然话题里找到“天生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