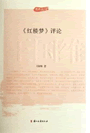|
|
编号:C91·2130320·0966 |
| 作者:王国维 著 | |
|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亚马逊6.90元 | |
| ISBN:9787807158257 | |
| 页数:83页 |
评《红楼梦》,王国维认为考证之学下的评述是不科学的,也是无解的,“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自然会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从个体窥见人类的整体,或中或西,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在书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本书为“博库丛刊”之一种,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人间词话、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人间词补编。
《红楼梦评论》:”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解脱
庞大和简略,梦境与评论,只有那一抹红,还粘在《红楼梦》的百二十回中,也粘在这《〈红楼梦〉评论》中,或如王国维书中所说的那样,这红色也是欲望的一种呈现,是欲望发现的人生存在,“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所以王国维只以这小小的五章来论述“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的《红楼梦》,或者也是在文化和知识的保留中,不让欲望过多,不让苦痛过多。
欲在何处?王国维在《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直接运用叔本华的观点提出了:“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这欲是关于身体的,是关于性爱的,也是所有生命的本真状态。有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为证明,人生的“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也就是说随着人的降生,欲望便伴随其中了,这种欲望连接的生活从此也是贯穿人生:“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而不仅是人生的常态,欲望也是和知识有关,知识越丰富,欲望就愈强,而欲望不能满足,也必须通过知识加以排遣,使之“趋利而避害者”。所以不管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的欲望蔓延,还是“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的知识正比,或者“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实际上都是同一种东西:“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所以人生的有关,不管是知识还是实践,都是欲望和苦痛相关,而这种欲望与苦痛的人生,注定让《红楼梦》成为一部以不能解脱的悲剧。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的庞大世界也是由欲望构筑,“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就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最直接叙述,主人公为什么叫宝玉?那么所谓的“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也就是说,贾宝玉身上带着最原始的人生欲望,而这种欲望的表现形式即是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一个是有限的欲望,另一个则是无尽的欲望;一个是形而下的满足,另一个则是形而上的解脱,所以说,以“玉”为隐喻的欲望,在《红楼梦》里则成为一种想要摆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在王国维看来并不是用最直接的自死来满足来解脱,而是不死。“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王国维认为,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都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因为欲望无法满足的无奈,而真正的解脱只有三个人:贾宝玉、惜春、紫鹃。在王国维看来,对于苦痛并不是都需要解脱,解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存于世,而对他人对整体的社会有着意义。所以解脱又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存于观他人之苦痛的解脱是超自然的,神明的,比如惜春、紫鹃;而后者之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当然也是美术意义上的,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代表人物便是贾宝玉,因为在贾宝玉身上,有着人生欲望的标本,有着人生苦痛的普遍性,“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从个体到整体,贾宝玉的标本意义也就是构筑了一个能够在美术意义上的欲望和解脱之道。
为什么解脱?在王国维看来,解脱的意义也就在与能找到“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也就是说将我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忘记我和世界的那种关系,那么独立于世界和欲望,就是一个如理想国的状态,“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美术是最好的办法:“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忘记物我的关系,也就忘记了那种人生的欲望和苦痛,也就忘记了生与死,在“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的美术世界里寻找观者的状态:或者“吾心宁静之状态”,或者“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都是寻找最纯真的那个远离欲望的自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从欲望的世界里解脱出来,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美术之务”:“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术之目的也。”所以在《红楼梦》中,王国维发现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就是和“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王国维看来,“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是“悲天之色彩”,而《红楼梦》开启的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悲剧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则是“盲目的运命者”,而第三种悲剧是“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非客观原因造成的悲,是一种“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无法改变的自我深渊,与生活有关,与苦痛有关。
悲剧之美学意义,对于《红楼梦》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王国维也指出了《红楼梦》在人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之上的:“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不仅是伦理学支撑着悲剧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学的“误谬”是《红楼梦》具有世界意义的基础,解脱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解脱,而是从解脱中感知存在的价值,“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宝玉之死如果只是个体意义上的,那么《红楼梦》也只是具备了悲剧美学,而无任何时代意义,““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融入世界,融入人生,运用叔本华的观点,将美学融入社会伦理学,从而找到“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里的“意志”。而伦理学的最高理想,也便是得到解脱:“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梦想而来,对于《红楼梦》的批评建构便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群体意义,从考证之学上升到了批评之学,“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谁是作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红楼梦》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也正是美术的特质之一,那就是从索引和考据中解脱出来,从美学的悲剧意义和伦理学中发现人类的意志,而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角度去批评《红楼梦》,那么“《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也就从个体性中解脱出来,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的批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这篇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批评,在重新出版时被这样定义,但其实这一册小册子对当时的蔡元培索引派和胡适的考据派之外,新建了王国维的批评派,有开创价值,但是这样的标本意义并不足以用这5篇文论来涵盖,而这一抹红色的“丛刊”其实带入的是一个“跳房子”的游戏中:22页之后应为23页的《第五章 余论》,而其实23页已经被替换成了第55页的《人间词甲稿》,下一页却仍然是24页,而25页的背面却是58页,之后是59页,再翻过去则是28页《人间词话(上)》和正常的29页,而再过去则是第62页、63页,32页、33页,66页、67页,再下去才是正常的36页、37页……也就是最后装订成书的页码是:22-55-24-25-58-59-28-29-62-63-32-33-66-67-36-37……混乱和无序,或者也不是那个“跳房子”的游戏了,数字里的谶语看起来就像是《红楼梦》里的“眩惑”:“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
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
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
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
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
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
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故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悲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
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
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
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
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怎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贮则大不可解脱者也。
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
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由此观之,则谓《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