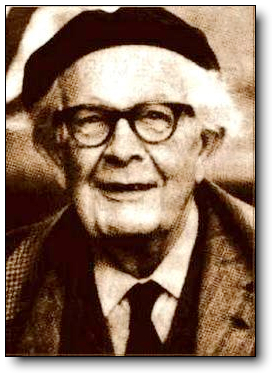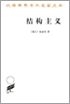 |
编号:B88·1970704·0387 |
| 作者:(瑞士)皮亚杰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6.60元 | |
| 页数:120页 |
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结构主义”对20世纪的心理学、语言学、认知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皮亚杰的这本著作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结构”的意义。皮亚杰对“结构”的定义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主要特点是整体性、转换型和自足性。”皮亚杰从数学、逻辑、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诸方面对“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结构”没有消灭人,也没有消灭主体的活动。真的,应该懂得,在关于人们所应叫做“主体”的东西上面,已经被某些哲学传统积累起了许多的误解了。
——《结论》
“结论”里已经把人解放出来,把主体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非要把人当成是结构的自我中心,而是要通过持续不断地“除中心作用”,形成一个“认识论上的主体”,或者很明确地说,主体之存在必须使结构成为方法论上的结构,必须以人的认识来建造互反性和再构造的结构,认识论而有方法论,方法论而有运算,而有转换,而有协调,而有功能——当撇开结构主义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那种去中心化的主体才能在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成为起功能作用的中心。
去中心而成为中心,去哲学化而具有认识论,这或者是皮亚杰把结构主义称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普遍结构主义、真正的结构主义的主旨所在,而在他的对面赫然站着福柯《词与物》中的理性“考古学”。这似乎是关于结构认识在哲学体系上的不同建构,当皮亚杰称福柯的结构主义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就是认为他是以怀疑论和消极论点来阐述结构主义,从而使得结构与构造论分开来。福柯把人文科学看成是一些“突变”,只是“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者“认识阶”的暂时性产物,“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所以福柯认为人文科学都是伪科学,只是在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并且使他扎根在现代的“认识阶”里成为一种形式,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
“认识阶”是福柯所起的一个名词,它具有某种历时性的意义,在结构的形成中,它是先验的,是无法预见的,“它们不是从简单的心智活动习惯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关系的体系,它们也不是在科学史上某个时刻能够推广的带有限制性的思想方式的体系。”所以当它以先验的形式决定了知识,它只能延续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最终它会在历史的知识转变中让位给别的“认识阶”。所以以“认识阶”的历时性为特征,福柯的理性“考古学”在皮亚杰看来就是没有理由的“理性变换”:“理性的结构是通过偶然的突变或暂时的涌现而出现和消失的”。
突变的,先验的,历史性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显然不符合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当然也背离了他对于结构主义的科学认识论的观点,“这位作者的具有革命意图的著述能给我们提出对人文科学的有益的批判”——把“人文”和“科学”结合在一起,似乎是皮亚杰期望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在哲学上寻找到它的科学论断,而其最主要的突破就是在福柯怀疑论和消极主义中对于主体活动进行有益地界定,而不消灭人的主体活动之存在,就必须使得结构主义在哲学上恢复其辩证思维:“在各种科学本身的领域,结构主义总是同构造论紧密联系的,而且就构造论而言,因为有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矛盾解决’等特有的标记,人们是不能不承认它有辩证性质的,更不用说辩证倾向与结构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了。”辩证是能动的,是发展的,是对立而解决矛盾的,皮亚杰认为,辩证所要求的的构造,就必须在我们无知的深渊之上“建造一座座便桥”,从而使得无知的深渊向知识的彼岸延伸出来,延伸便成为构造本身,无知而有知,有知而无知,就如在肯定之中产生种种否定,从而在共同的“矛盾解决”中得到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
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都在这样的辩证思维中为结构主义的构造建立了联系,而皮亚杰甚至认为,“必须把辩证过程所占的地位,恢复到比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希望赋予它的还要重要的位置。”这样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摆脱哲学传统中对于主体的误解,摆脱“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束缚,因为在他看来,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实在论,而是一种方法论,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科学的辩证理性,当然最主要的是它具有除中心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意义,使得它“把主体从自发的自我中心现象中解放出来,以得到协调,建立起有互反性的构造,再构造的历程中产生的结构。”所以在皮亚杰看来,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不存在和功能主义分开的结构主义,只要它是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是普遍的结构主义,只要它存在着“认识论上的主体”,结构主义就是开放性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趋向于把所有这些研究整合进来,而且整合的方式是和科学思维中任何整合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在互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进行整合。”
从批判到探寻,从否定到肯定,皮亚杰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可理解性的共同理想”,他认为,结构主义具有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也就是说,一个结构本身具有自足性,“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面则是,结构虽然是多样的,但是它却是普遍的、必然的:“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概括出来,一个结构具有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当然是它本身具有自足意义;而转换性是结构内部存在着一个或若干个转换的体系;自我调整性具有某种守恒意义,作用于它的主要是三个程序: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从这些程序中发现这些结构‘真实’构造过程的各个阶段,也可把在没有时间性的形式下、几乎是柏拉图主义式的那些运算机制放在基础上,从而引出其余的一切,把次序颠倒过来。”
很明显,结构的这三个特性显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整体性是在打破结构的“原子论式”的研究,以一种整体观构建一个自足的结构;转换性则是否定结构静止的“形式”,建立起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自身调整性则在运算、构造中实现结构的守恒性,守恒性也就意味着结构的封闭性。展开而来,皮亚杰分析了数学结构、逻辑结构、物理学结构、生物学结构、心理学结构和语言学结构,在这些结构里,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成为所有结构的普遍特征。比如数学结构,最简单的是群结构,通过组合运算汇合成某个集合,通过这个集合的运算法则应用到某些成分上去,也会得出这个集合的一个成分来。所以群具有普遍协调的作用:“在转换关系的可逆性中体现了不矛盾原理;中性成分的恒定性保证了同一性原理;最后一个原理人们较少强调,但它同样是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到达点不受所经途径不同的影响而保持不变的原理。”在群上还有母结构,母结构分为群的代数结构、以“网”为原型的结构以及拓扑学性质的结构,不管何种结构,皮亚杰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课题上的“那些动作”,这些动作反应了抽象法的本质不是来自于客体,而是从动作中产生的结果,这也是结构主义构造论的一个基础。
逻辑结构其实是不封闭的,它是建立在“上升形式-内容阶梯上的任意一点”,逻辑体系的上方是开放着的,下方也是开放着的,“作为出发点的概念和公理,包含着一个有许多未加说明的成分的世界。”虽然在一个点的不同方向上是开放的,但是在公理和概念的整体意义上,则是封闭的,“每一个成分对于比它高级的成分来说是内容,而对于比它低级的成分来说是形式。”内容和形式的结合而产生的体系同样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三个性质。物理学的结构,虽然不依赖于人,但是却符合我们的运算结构,而生物学研究的有机体是一个“能自身调节的有若干转换作用的整体性体系”,而作为人的生物学意义,就是人既作为复杂物理的客体,又是行为的原动力,这双重性质使得人有可能精确地了解自身结构,而这种能力“给我们提供一把结构主义理论的钥匙了”。在皮亚杰看来,这个结构的图书意义在于找到了主体的根源,按照福柯的看法,人只是“历史发展上的各个事物的次序中的某个裂口”,相当于“我们知识里的一个简单的褶皱”,而皮亚杰却认为:“这个裂口和这个褶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但组织得很好的爆裂声中产生的,这个爆裂声就是整个生命界所构造成的。”
心理学结构上,格式塔式结构主义已经阐释了存在整体性的知觉系统,而在知觉意义上就有了构造论的可能,结构通过反映抽象提供的材料,以平衡作用提供的可逆性,“逐步构造成逻辑结构的”,这样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密不可分,也就使得主体成为功能作用的中心。而在语言学结构中,索绪尔建立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符号和意义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使得语言结构形成一个整体,而言语方面的创造力,根植在理性中的语法和派生的语句组成的生成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这也发挥了结构主义具有的三个特性,特别是语言转换模式的建立,是对于索绪尔静态语言结构主义的一种积极的补充。
数学结构、逻辑结构、物理学结构、生物学解构、心理学结构以及语言学结构,种种结构都纳入到皮亚杰方法论的结构主义之中,它是和整体性结构主义有着区别:整体性概念是涌现出来的,是起作用的原始概念,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是有转换性质的相互作用;整体性结构主义只是把观察的联系或相互作用的体系,看作是自身满足的,而方法论结构主义是“要到一个深层结构里去找出对这个经验性体系的解释”,所以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时,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就具有了优势,它通过推演的重建,使得结构不再是意识,而是行动,使得体系具有结构和功能不可分的特征,也正是这种方法论,使得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实现了运算的可能:“这种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要到‘具体’社会关系的背后,去寻找出只能通过对抽象模式作有演绎作用的构造才能得到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来。”当物质和形式剥掉了独立的存在,通过某些图式的“运算”结合在一起组成结构,它们就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形式,也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内容,“在现实世界里也和在数学里一样,任何形式,对于包含这个形式的那些更高级的形式而言,就是内容;任何内容,对于这个内容所包含的那些内容来说,就是形式。”
同样在哲学研究上结构主义在注入了辩证思维之后,也从“先验的历史性”的“突变”中找到了它积极的功能主义,所以皮亚杰说,结构主义的关键“在于运算的第一性”,运算是把主体当成功能的中心,在不消灭人、不消灭主体活动的前提下,区别开个别主体和认识论上的主体,然后把支离破碎的意识和主体“在其智慧活动里所能努力做到的这两方面分开来看”,主体的运算,就是“从主体自己动作的普遍协调里通过反映抽象得来的”,所以主体的运算是一种发生认识论,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形成过渡”,是“一个从最弱导向最强的形成过渡”——“结构只代表这些运算的组成规律或平衡形式;结构并不是先于它们或高于它们的、为它们所依靠的实体。”
结构主义是方法论的结构主义,是运算为第一性的结构主义,是具有科学性和主体功能中心的结构主义,当然也是把多种学科协调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主义,是在开放性中实现转换的结构主义:“在把种种结构同它们的来源切断时,人们才可以把结构当做是形式化的本质;当结构不是停留在字面上,也就是把结构重新放进它们的来源中去时,人们才能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