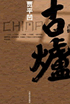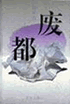|
编号:E29·2170516·1391 |
| 作者:贾平凹 著 | |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35488473 | |
| 页数:320页 |
从“孤独地走向未来”到“默默看世界”,从“独自走一走”到“独处的安宁”,再到最后“自在的禅意”,一个人的看,一个人的走,一个人的安宁,一个人的自在,一个人的默默,一个人的孤独,《自在独行》分明是退回到“诗意的栖居”里,不管是行走于西北的大地,还是隐居在自己的书房,对于贾平凹来说,内心的安宁与独行的自在是一种境界,“真正的孤独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但是长啸的兽又为何打破寂静?而这一声长啸是不是也是一种强者的态度?而其实,独行不是为了让人追崇,它只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为,“走向孤独的人难以接受怜悯和同情。”
《自在独行》:我的荒园里再不荒了
既然死是人的最后归宿,既然寿的长短是闻道的迟早,既然闻道而死去的时候是一种解脱和幸福,对于死应该坦然。
——《说死》
《礼拜二午睡时刻》合拢,便是“千克读品”的完结,就如一种死,是把30年个人阅读史放进了密封的时间里,作为一种整体,刻在了某个碑石上。即使以后重新翻开,重新阅读,当时间和整体都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也应该是另一种开始,新的开始,宛如死之后的新生。于是1000本阅读完的图书之后,便一定是第1001本,翻开新的那一页,是贾平凹的《自在独行》,而这1001个文本似乎正以一种“自”在和“独行”的方式出现在我“千克读品”之外。
中国当代作家,散文,这是贴在上面的最基本的标签,而在我近几年的阅读世界里,这样的标签基本上是被我鄙视甚至废弃的,除了诗歌之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已经自动过滤在我的阅读之外,但是《自在独行》却闯了进来。只是某次学习活动的读书资料,带着明显的功利性,所以是赠品。赠品而来,只是手上拿着,眼睛看见,翻过一页,而已,这样的忽视甚至忽略不是刻意为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去除所谓写作和思考的功利性,而“自在独行”的书名,是不是反而构成了阅读标准和个人实践之间的矛盾,一如1000之后的这1001,是真的自在独行,还是与不纯粹的他者同行?
敏感于作为新起点的1001这个数字,符码一般,契合着数字化时代的书写,所以很直观地认定,1001就是一个质数,孤独的质数,除了1和它本身作为因数的质数,当然,它就是“自在独行”的世界。可是,这是一个直观带来的错误,1001根本不是质数,当可以分解为7,11,13的时候,1001并不是孤独的,它是另外数字的合体,也是伴随它们走在并不孤独的路上,于是,直观和本质,在这个数字,这本书面前,就被区别为两种状态。
从直观开始,除了1001的阅读序列之外,是那白色的封面,似乎一尘不染,似乎纯粹无杂,似乎也是喜欢的,可是那黑色的注解却总是粘在着白色的封面上,“贾平凹的独行世界,写给每一个孤独的行路人”,是在书名的下面,“贾平凹四十年散文精选”是在书脊的旁边,“从容是真,宽识是福,有敬无畏,乐以忘忧”放在封底的正中,还有那句摘录:“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不虚此行。”当然还有图书条形码之外关于新媒体阅读平台的二维码,还有“亚洲好书榜——粉丝力量”的圆形LOGO……它们分布在白色世界里,以点缀而错落的方式进入直观世界里,那么在这样的注视下,白色还能表达“自在独行”的境界?
而且,还有那个独行者的设计符号,就在封面的左下角,沿着一条灰色的道路前进,似乎背着包,似乎戴着遮挡的帽子,似乎低着头,一种符号,其实是具象的人,独行客,也是阐释着“自在独行”的境界,可是他是谁?贾平凹?你?还是我?当一种独行的状态被设计成一个具象的符号,无论如何都是以画蛇添足的方式让人进入到独行的世界里,可是,如此,却反而让人看见了纷杂,看见了喧闹,看见了目的,看见了自在之外的他者。
而一本免费的书,一个不是质数的阅读序列,一种可以忽视的阅读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倒变成了他者,而在贾平凹四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中,自在独行真的是一种欲求的状态?四章的分类,第一章 孤独地走向未来,注解为“生命的睿智——从容是真”,既然要让孤独带着自己走向未来,那么在回首的时候,一定会看见自己内心不断生长出来的孤独。这孤独是母亲纺车里发出的声音?“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音带了,唱着低低賊的、无穷无尽的乡曲……”是父亲在遭受社会的不公和身体的摧残之后的死亡?“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或者是自己小学生活力用坟地里的白纸条儿钉成写字的本子?还是在西大三年偷偷吸烟,偷偷给留辫子的女生写了一首自己都吃惊的情诗?亲情有关,以及有关,那些成长中的故事是纯粹的,但是这种纯粹看上去更像是失去之后的遗憾和寂寥,就像在父亲逝世的葬礼上看到的那棵梨树:“满院的泥泞里人来往不断,响器班在吹吹打打,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还是父之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
独独一个,不是孤独,是无奈的单独,而当这种单独的状态变成怀念,对于贾平凹来说,也是在拥有了名气之后被打扰的无奈,明代的陈继儒说过,闭户即是深山,而贾平凹的疑问是:“闭户哪里又能是深山呢?”有过冲击,受过诽谤,渴望着灵魂的安静,实践着闭户的生活,却最终还是被声声的敲门声惊动,熟悉的来访者,陌生的打扰者,深山不再,单独不再,“我的命就是永远被人敲门,我的门就是被人敲的命吧。有一日我要死了,墓碑上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人终于被敲死了!”
于是在敲门声里返身而归,重新审视孤独的状态,什么是孤独,贾平凹的理解,孤独是一种过程,起先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是无知己,是不被理解——就是没有他者在身边,亲情之失去,记忆之淡忘,都是把自己推向了单独状态,这是第一重孤独。但这是一种被客观世界推入进入的孤独,而贾平凹心目中真正的孤独是“不孤独”:“真正的孤独者不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长啸的意义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当尘世不轻易让人孤独,让群居变成一种平衡,作为自己就需要勇往直前,还要把那些众生撇在身后,当众生无法赶超,当众生开始向你欢呼和崇拜,当众生尊你的神圣,“神圣是真正的孤独。”所以这第二重的孤独才是真的孤独,但是这种被众生尊神的膜拜是不是真的让你享受孤独?
敲门声声,门外的他们是不是众生?你不开门,是不是就可以不被他们赶超?所以对于贾平凹来说,他的努力是为了摆脱众生,却需要众生的崇拜,这就构成了一种自我神化的悖论,贾平凹说自己喝点小盅的酒,浅醉而悟;贾平凹说自己读些闲书,“不必规矩,坐也可,站也可,卧也可。”贾平凹说可以与人交,“淡,淡至无味,而观知极味人。”贾平凹说,养生不养猫,出门挂旧锁,如此,就是远离众生的烦扰,远离俗世的侵害,这就是他所说的舍得:“舍舍得得、得得舍舍就充满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演绎着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啊,舍得实在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艺术。”
但是这和众生保持着距离,留下自己高度的孤独,从来不是一个人,它把众生作为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时时刻刻回过头去看看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于是在贾平凹那里又延伸出了另一个词:“默默”,第二章:默默看世界,说的是“人世的悲凉——宽释是福”,闭户看不见深山,敲门变成了宿命,这个世界到底存在怎样的敲门者?到底会有怎样的众生?他们是那些在街头上露出不同神情的人脸,他们是总说自己是忙人的闲人,他们是偷得一闲厮杀在棋盘上的弈人,他们是醉茶醉饭最酒以及醉人的饮者,他们是“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的朋友……他们在贾平凹看见的世界里,他们是复数,而似乎只有贾平凹一个人“默默看世界”,于是一个人坐下来吃烟,“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于是看透了房子,“房子是囚人的,人寻房子,自己把自己囚起来,这有点像投案自首。”于是看透了奉承,“奉承换句话说是献媚,献媚就是送上女之色,是妓的行为,那么,既然有了妓,妓使许多人变成了嫖客,嫖客得性病就让他自受去吧。”于是看透了生死,对于死应该坦然,而真正的死就是闻道而死,不留遗憾。
从社会的芸芸众生看见世界,从人世的悲心寻找“道”,无论如何,当众生成为陪衬,那个孤独的人是不想孤独的,但要保持孤独,唯有寻找寄托物,在贾平凹那里,寄托物是一方的山水风情,是那书房里的玩物,是玩物里的禅趣。一种是目光向外寻找自然之道,所谓“独自走一走”,强调的是自己触摸“大地的魂灵”,从得到有敬无畏的快乐。那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听了秦腔,肉酒不香”:“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的使他们获得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那黄土高原,是“归复于黄土的颜色”的一生,“深深的犁沟,像绳索一般,一圈一圈地往紧里套,他们似乎要冲出这个愈来愈小的圈,但留给他们活动的地方愈末了,就停驻在山峁顶上。他们该休息了。只有小儿们,停止了在地边玩耍,一步步爬过来,扑进娘的怀里,眨着眼,吃着奶……”那五味巷,是“借得巷头巷尾酸辣苦咸甜”:“这巷子,离大街是最远的了,车从未从这里路过,或许就最保守着古老,也因保守的成分最多,便一直未被人注意过、改造过。”那“小极小极”的白浪街,是三省人和谐地统一在这条街上。还有贫瘠的山沟却是爱情的乐土的米脂,还有神秘却有逗人情丝的三边,还有活泼泼地叫人爱怜着青的石层的清涧县……
行走是为了触摸大地的魂灵,所以独自走一走是看见,是发现,是一个人的品味,但是在这孤独的状态中,那种原始,那种神秘,那种和谐,是不是会因为走的人多了反而被破坏,或者说,这些大地上的魂灵本身就是一个神话?观者是无法自观的,大地也无法在自己的世界里安详如昔,于是那种矛盾就在孤独中变成了注目,在敬畏中变成了亵渎,《商州又录》中那两则对话似乎就是凸显着这种矛盾,当山里的女人生了孩子,接生婆喊着男人进门,在烧水,打鸡蛋,泡馈馍之后,男人说的一句话是:“又一个山里人。”而另一户人家,当孙子听说县里要修一条柏油马路到山里来,就高兴得喝醉了酒,那家里的老婆子听到孙子喝醉,说了一句话:“越来越不像山里人了!”男人说“又一个山里人”是对于命运的不安,自己的命运和下代的命运还会困在这山里,而老婆子“越来越不像山里人了”的感慨是对于大山的坚守,她拒绝一条公路进入山里。
如此的矛盾,或者也是自在独行还是他者为背景的独行之间的矛盾,在贾平凹独处时也是如此,家里书房放满了那些玩物,汉罐、绥州拓片、老子讲经石,是对于那些所谓“或迷醉得变态异化;或营营逐利,以聚钱财;或装饰门面,以显高雅”的收藏者的一种讥讽,而对于自己来说,“旨在创造一个心绪愉快的环境,而让我少一点俗气,多一点艺术灵感。”把他们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把自己抬高到艺术的境界,但是当独处时,那心却也并非是释然而淡然的。从三生石里看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又看山不是山,又看水不是水,再看山还是山,再看水还是水”的境界;从丑石中看到了“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的哲学;从埙里读到了海明威冰山理论,读到了“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感悟,似乎都在进入那难得的自我状态,都在接近心灵的纯净,可是“群居守口,独坐防心”,看见而看不见,看不见却又看见,朋友送来的狐石竟然想到了先前在乡下看见的梅花印,想到了梅花印有关的红狐,于是在夜梦里竟见了红狐变出来的美人,“艳而不妖,丽而不媚,足风标,多态度,能观音,能听看,轻骨柔姿,清约独韵。”这通体灵性的人终于使得独坐的人生出了新想法,甚至新欲望,“终有一天,我想,我会将狐石系在了她的脖颈上,说:这个人儿,你已经幻化了与我同形,就做我的新妻吧。”
狐石而想起梅花印,梅花印想起狐女,狐女想起新妻,这转化大抵也是自己的孤独是留着一个位置的,坐在位置上的不管是想象,还是梦境,不管是灵性还是欲望,总归是一种想要的东西,就是一种不舍得的东西,如此,孤独便是有所求,当众生不再,唯有在物的世界里想象一种满足,所以在“心最难受住”的感叹里,贾平凹说:“脑子里有一群惊乍的野马,想功名,想利禄,想一些奸佞人如何对我欺诈和诋毀,也想一些女人是怎样的妩媚。”而拿了书看,多少也只是一种掩饰,关键在书中,那些东西不是被过滤了,反而更长出了新的欲望,“夜半三更的时候,总企盼举头一看,其实是已经感觉到了,窗的玻璃上有一张很俏的脸,仅仅是一张脸,在向我妩媚。我看她,她也看我;我招之,她便含笑。”
那个她,总是难以从自己的头脑中挥去,总是难以在孤独中沉思,而她是什么?是忘不掉的俗世,是走不出的寂寞,是少不了的烦扰,是众生,是他们,当那一面被命名为“红狐”的琴放在了自己家里,于是空着的位置也终于有了主人,在写给Z的信里,贾平凹说:“Z,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一件大事,真的,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也就是我有了红狐琴,我的荒园里再不荒了,我开始过得极平静而又富有,这你应该为我祝福和羨慕吧!”荒园不再荒,是有了另外的世界,所以对于贾平凹来说,重要的不是无人打扰的荒园,而是有人坐着的世界。
自在孤独像是一个寓言,他独行,却需要回望,他自在,却需要众生,他是白色的封面,却需要一堆的注释,它看起来像是孤独的质数,却是伴随着因数的合数,就像那只曾经关在鸟笼里的云雀,大自然或者是它最自由的天地,可是当从鸟笼里飞走,它不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反而以回来的方式让自己再次囚禁,“老头说,笑得更得意了,‘我已经喂它两年了,这笼里多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