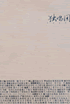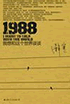 |
编号:C28·2110116·0791 |
| 作者:韩寒 | |
|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215页 |
《独唱团》死了,2010年岁末,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韩寒只能在1988和世界谈论一些东西了,他现在是一个爸爸,他亲自关闭了那个世界的大门,1988字符的后面是一个青年的无奈,走在路上,却没有喝彩。对这本书的注解,出版社用煽情的句子概括:首印量达到空前的70万册,韩寒称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也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的新概念。但其实,这里面有着韩寒一直以来的不安和困惑,他说:这部小说完成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我从2009年的夏天就开始落笔,多事之夏,最终停滞。到2010年初的冬天继续开始,再停滞。一直到2010年的夏天,一样多事之夏,但完成了1988。书的第一句是:“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和《独唱团》里的句子一模一样,不知道命运是不是也一样。
书的秩序原来是这样的:《1988》在下面,《1Q84》第三季在上面,终极版的《1Q84》压着韩寒据说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我翻了个把《1988》抽出来,秩序颠倒了,我说的是那个书名,韩寒说,正是因为《1988》和《1Q84》有着冲突,所以几经周折,在“内心已经无法更改”的尴尬中,他最后把书名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读起来有那种小孩叫板大人式的自信,但其实,这里没有瓜葛,我把书的秩序翻过来,看起来只是完成了一场行为艺术。
和《1Q84》或者只是时间概念上的冲突,但其实他们都不涉及真正的时间,1Q84是个规则变化的世界,虚拟和现实难以分辨,而《1988》只是一辆自我命名的越野车,在物理时间里,我倒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对称是阅者和作者之间的不平衡,恕我对于《1988》的简单处理,这本韩寒从2009年夏天至2010夏天完成的小说,我只是用急促的1个半小时便阅读完毕,那中不能体会作者创作艰辛的感受让我一直找不到很愉悦的快感,它呈现给我的只是一个故事的简单文字,属于有限的夜晚。我抚摸套在外面的塑料,有一种很柔软干净的感觉,然后撕破,扔进垃圾箱,翻开,里面是韩寒很酷形象的一枚书签和他的签名海报,作为图书的附属物,我只会在阅读完之后再把它们收录进去,完完整整地合拢,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它早就发生了故事,我说的是《1988》的那段开头,在《独唱团》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去年的那个秋天午后,我用心阅读了韩寒的那段青春记忆,但只是这部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新概念的小说在杂志上显得那么孤独,也充分说明了独立刊物的无奈,在这样的绝唱面前,“我和世界谈谈”显得很有必要,但其实只是大人设的一个圈套,世界才不会理睬你。
我想我也必须在撕破图书那层宛如处女膜一般的塑料之后,阅读一段公路奇缘。这是一个激发回忆的故事,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但绝没有经典,它像一段自由流动的空气,你没法阻止它,但是你却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抽根烟,或者在夜色中住宿下来,前方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目的地。但我们必须在某一个时段前进,因为有人在等着我们,等着生活继续前进,等着“要跟他们,跟这个世界谈谈”。“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这样一个凯鲁亚克式的开头使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东西都可能没有终点,我们在路上,而我们的行走像极了行为艺术,“因为我坚信,世界就像一堵墙,我们就像一只猫,我必须要在这个墙上留下我的抓痕……”那道抓痕说明我们曾经来过,至于那抓痕会在墙上留下多深,谁也无法知道。
抓痕是成长的必要仪式,在这里,一个青春的故事被安排进了我们需要跟随的目标后面,看起来那个目标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的朋友和丁丁哥哥。朋友给我留下一辆车,就是那辆带着死亡气息的1988,曾经只有壳子和车架的报废车,但是朋友让它成为一辆车,一辆可以在公路上开,可以遇见妓女,也可以运载回朋友的骨灰;丁丁哥哥,帮我摆平来自小地痞的刁难,带我兜风,为我唱歌,教我踢球的时候要做假动作,但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地方——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紧紧跟随的精神寄托,“我总是发现,当我在发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思考了,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已经行动了,当我行动的时候,他们已经翘了,然后我又不敢行动了。翘了的他们就成为我生命中至高的仰望。我天生佩服他们,希望他们身上的血能够温热我的身体。”在我身上,似乎有着那种瞻仰的感觉,生活在下,必须仰起头,高于自己的理想就是我们精神的全部,尽管现实中有着种种的磨难和不平,有着那个吞弹子的10号,但毕竟我们都是需要那些精神支撑的孩子,“只爱一个人,刘胡兰”式的英雄高度是我们对现实的一次超越,于是我们用卡通的圣斗士来武装自己,保持着“生命中最重要的台词”。
“我也是被他们笼罩着的人,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
继续前行是一次青春的仪式,无可避免会有那些爱着或不爱着的人,那些记忆中的爱情或者爱之外的遇见,这是年少的必须经历,而我的故事在一段有形的路上展开,那里没有刻骨铭心,却有着无法摆脱的情结。于是便有了出卖肉体的娜娜,或者叫姗姗,或者还可以叫田芳。她是一个乐观的人,对生活的希望是延续自己肚子里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要给他教育,要不让他走自己这条路,这个把台灯当成红外线照射仪器,把嫖客当成医生的妓女,似乎一直在自己默默承受的轨道上行进,对于她来说,对于爱或者喜欢只有10元钱的一个标准——只要喜欢的人她只收10元钱,仅仅是一种象征而已,但是对她来说,剩下的身体也已经不能成为资本了,在底层的生活中,她其实是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尊严,她甚至只为了孩子去赚钱,而当面对我作为一个真实的听众,她会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告诉我,而我,似乎一直就是一个不和她发生意思感情,却愿意听她故事的人,自然,那些回忆中触动了我的青春记忆,关于女孩,或者关于那些爱,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子”,还有那个想着出名的演员孟孟,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心里刻骨铭心的东西,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后来却把我叫做“反革命”,而且和10号一起在路上成为牺牲品,而那个孟孟,只是一个爱出名爱赚钱的不入流演员,娜娜,或者孟孟,对于我来说,都是那段青春里的抓痕而已,“我们一生很难对婊子动情,很难对戏子动心,纵然我对婊子动情,婊子也很少赠我真情,纵然我对戏子动心,戏子也未必还我真心。”那种哀怨似乎正是青春难以摆脱的宿命,“似乎只有违背现在的生活,才真正懂得了生活。”
违背生活其实就是走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朋友死了,只留下一堆的骨灰,娜娜死了,只剩下那个孩子,“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在路上,生活是看不见尽头的旅行,我们有时候自己把握着方向盘,有时却是被搭载在自己以外的车上,韩寒在《1988》序言中写道,“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你,不带‘们’。” 青春的记忆里,有些纪念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