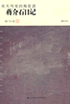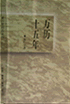|
编号:Z51·2130825·1008 |
| 作者:黄仁宇 著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07年02月第2版 | |
| 定价:19.00元亚马逊14.10元 | |
| ISBN:9787108010360 | |
| 页数:350页 |
“纵是新意,也泛创意”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概念在《中国大历史》中成为打开边缘政治学的一扇窗户,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作者说:“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在浩如烟海中国历史典籍中寻找一条脉络,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便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梳理的方法。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他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所以,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
《中国大历史》:走兽如何蜕化为飞禽
中国就像—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走兽要蜕化成为飞禽,是靠道德的力量,还是靠人为的区分设计,或者是插上翅膀的技术性改造?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型社会并没有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没有符合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相反却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在官僚阶级和农民的双层夹心中,无可避免的形成了牢固的地缘政治,不论是秦汉的第一帝国,唐宋的第二帝国,还是明清的第三帝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原始积累资本阶段”,都始终无法完成商业革命,无法形成货币管理模式,从而使走兽变为飞禽只能成为一个“摸石头过河”的历史寓言。
“macro-history”,这个被黄仁宇自称为“系模仿而非发明”的历史方法是一种技术的关照,区别于微观,也只是“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而已,而体现在宏观上,也就从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发现技术的困难和可能,所以,广泛的归纳法在黄仁宇的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一种俯视状态,特别是在时间轴里寻找现代意义,从秦汉的第一帝国,到唐宋的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的第三帝国,黄仁宇以压缩史料的方式,再建了历史的“路线图”,但是这种“路线图”也只是在回顾宏观视界。
对于历史进展当然用史料来分析,这种技术观是抛弃道德因素的,“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也就是说,道德支撑只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而已,特别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道德观念尺度一直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在司马光的时代,道德观念已经等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标准,但是也没有进入韦伯的“新教伦理”之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恒古不变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主导中国能否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决定因素,而唐宋帝国的扩展性和明清帝国的收敛性,也只是用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一种背景而已。
而这个背景必不是被虚化的,而是在逐渐演变中,以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成了国家的制度。如果从确切的证明来看,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但是商代除了青铜器和甲骨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之外,并无在制度上形成农业社会的扩张形态,而武王伐纣建立的周朝,则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在制度建设上,黄仁宇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开始出现,其代表当然是最具创造性的人物周公,作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始创者,周公用“间架性的设计”弥补了当时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上的技术难题,从人为的政治区分上为国家进行了组织设计,封分制、宗法制以及井田制都成为“间架性的设计”的一个部分,从而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而周代政治上的早熟,直接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最明显的标志便是秦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发展有自然灾害的威胁,有气候上的变化因素,也有和塞外游牧人的斗争记录,但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来看,只有将官僚机构置身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才能抵挡这诸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威胁,而在秦朝,也种使境内的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极权主义”,在秦始皇即位前约一百年,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等政策已经付诸实施,而经过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度量衡统一,甚至是焚书坑儒等极端政策的实施,而到了汉代初期,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公布了地址意识形态的立场,不论是儒术的统一,不论是太学开启的教育体制,还是李悝向农户抽税的补救之策,“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而在汉朝后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使第一帝国建立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再统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形象和百姓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隋唐的统一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唐宋的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所以不管是带着世界主义色彩的唐朝,还是大胆试验的北宋,或者是具有“商业革命”的南宋,在政治的“间架性设计”中,依然是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行走,在唐朝,“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而专制政府并非是专制者自身选择,在极权产物的唐朝帝制中,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在斗争中败坏,当然影响了极权的维持,这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悲剧:“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也就是历史的宿命往往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不管是统治者自身的需要还是百姓的愿望,都不能真正维持昌盛的局面。而在北宋,“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这些物质文化的发展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同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气象,比如在组织上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在经济上,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特别是王安石的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惊异之举”:“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由此,在宋朝的大胆试验中,财政上要实现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端倪,但是这或者也只是一种理想,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失败,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上的打压,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也使从唐开始的第二帝国实际上仍然无法突破这一瓶颈,即使有南宋物质生活领先世界的“商业革命”,但是,“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而从明朝开始的第三帝国,中央集权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虽然组织和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而且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也完全可以实施,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在集权者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阻碍:“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所以在最后,晚明变成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更多的是内省,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是数目极少,所以使农业的商品化缺乏继续经营的可能,而在清朝,尽管有初期帝王的励精图治,但是从世界整体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也依然在集权和极权的政治“间架性设计”中。
不管是唐宋的扩展还是明清的内敛,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这些史料的背景依然可以说明中国在传统农业型社会里无法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完成数目字管理的架构。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并不只是要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梳理脉络,而更要在横向的比较中,探讨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个比较是从1800年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开始的。
1800年的中国预示着将进入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那时,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死去不过一年;那时,从家中没收以亿万计财产的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那时,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时,皇帝下诏禁止鸦片入口、不许白银输出也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而从世界视野来看,“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泊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像已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睦的合并构成事实。”而这两个体系的碰撞,在这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变成了一种梦魇,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不平等条约,以及太平天国等已经完全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瓦解,这种瓦解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
对于这种停滞,黄仁宇提出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两千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是辉煌的帝制时代,还是西方入侵的现实,都源于地缘政治缺乏一体性,所有的战争开支到最后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条理和组织,只有官僚和农民,也就是这两种阶层导致的分化和利益对抗,使中国成为—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这也是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有洋务运动,有百日维新,甚至有民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要做的是“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渡过新世纪之难关。”
“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长久以来中国的组织形式就是间架性设计,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制度,所以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稳定期,还是分裂期,不论是游牧和外敌入侵,还是朝代自身的弊病,最后牵制出来的必定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从而在微妙的局面里保持表面的宁静,而现代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数目字上实行管理,以货币管理的方式改变一直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格局,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于目前现代的中国,黄仁宇以一种希望的目光看待改革:“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但或者只是一种希冀,对于这个“潜水艇夹心面包”的国家来说,黄仁宇并不想预言什么,他只是站在宏观历史的山头,俯视中国历史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而那只走兽或者永远是走兽,而不会成为飞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