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15 闯入的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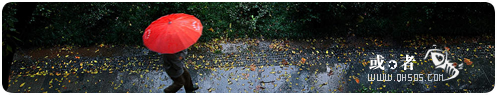
“我吹熄蜡烛,躺上床,伸展四肢,然后,在各种遥远、陌生、奇异的物品包围下,安然睡去。”闯入者的自白,只是小说里的一个句子,却突兀在可以夹放书签的地方。吹熄蜡烛迎来的是黑暗,伸展四肢带来的是舒适,安然睡去进入的是梦想,一切的故事似乎都不属于闯入者,他是自在的、合法的,甚至是永远的逗留,所以他自己成为一个房间的主人,成为一本书的主人。
但是闯入者永远要面对的是那一扇陌生的门,所以自白的前半句是:“接着,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仿佛闯入自己记忆中遗忘的角落,直到开启最后一个房间。”钥匙从哪里得到?房间为何没有真正的主人?所有可能设置的条件都被抽离了,空空荡荡而自由自在。所以允许前半句不在隐匿的状态下被引用,就必须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其实是一个允许被闯入的世界,允许自在而合法地度过一个有梦境的夜晚。所以在任何一种闯入的故事里,只有“我”才是被带进了房间的主语,而且也是唯一的主语,“我”的世界可以成全所有的动作,包括吹熄蜡烛,包括躺在床上,包括伸展四肢,包括被各种物品包围,包括安然睡去。
闯入是一种主动的行动,是用钥匙打开一扇一扇的门,然后成为主人,成为主语,成为叙事者,成为见证者。不设防而成为合法,这不是小说中的寓言,在每一个可能发生故事的现实里,也一样有着把自己当成主人的闯入者,一样有着可以打开每一扇门的闯入者。“我”在故事的明亮处,而“你”一定在看不清的黑暗里,所以允许,所以默然,所以被带进了闯入者的小说。一次点击也罢,一个同意也好,“我”和“你”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成为一体的人,所以非法而合法,拒绝而允许,是完全没有界限的,就连那一张书签,也完全从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的空隙处抽离出来。
一切合情合理,一切顺理成章,一切自由发展。但是巨大的危险却就在这时发生了,“当我在谈论自己时,也在谈论着你;当我对你讲述故事时,我也在重温自己的回忆。”那面镜子其实一直在“我”和“你”之间,在时间中分列开来,如果看见相似,那也只是一个镜像,所以闯入者所有的动作都在镜子里呈现出陌生的样子,“我对着镜子阅读自己的脸。”带着欺骗性,看见的我又何尝不是别人,甚至就是那个站在镜子后面的“你”,所以闯入者永远在一种镜像的故事里,在一种如梦的梦境里,合法而自在,甚至永远的逗留,只是进入了一个封闭的牢笼,那就仿佛是一个永远走不出的世界,带着自我满足而放弃了逃离。
故事被带入镜子之中,闯入者被带入自己的牢狱里,一个句子的突兀其实是在提防被改变的现实,那枚书签是必须插进去的,就在那一页和另一页之间,成为一道屏障,隔开了故事和镜子,隔开了“我”和“你”,隔开了虚设的场景和必须的现实。其实隔开亦是回归,闯入者摘掉自设的面具,退出打开的房间,就是从一个寓言离开,回归到没有记忆相关的世界里,“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的故事简化成一个闯入者的自白,而不管是“我”还是“你”,种种的隔离被拆除之后,其实只是同一个人,寻找遗失的另一个自己不是靠记忆,也不是靠想象,不是靠自我命名,也不是靠小说中的合法化,只有现实的喜怒哀乐,只有唯一的风雷雨雪。
放下一本书,从小说中退出,其实也是把我从闯入者的故事中解放出来,去除曾经的记忆寻找自己,是必须走进冷暖自知的世界。是的,夏天就这么恍惚地走过了,秋天也就不经意降临了,雨下在地上飘在空中,湿湿的,冷冷的。关了窗户,换了被褥,穿了长袖,不可复制的季节不是闯入者,也没有可以照见的镜子,它只走在不会重复的时间里,一天又一天,再无预演和折返的可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676]
顾后: 《生存哲学》:现实已经发了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