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5《异识》:你可以见证它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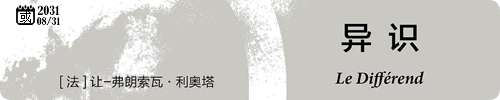
写作过程中,作者有一种感觉,他唯一的听众,就是“发生了吗?”,发生的语位(语用事件)求助于“发生了吗?”当然,作者永远不会知道,语位是否抵达终点。
——《本书说明》
这是一本作者书写的书,这是一本读者阅读的书,书和书是同一本书,但是书和书又是不同的:这是一本在诗学意义上呈现为观察、评论、随想、注解的“不连贯的散文形式”;这是一本和其他的书一起组成某个系列的丛书,但它是丛书的最后一部分;这是一本哲学性的、反思性的书,不预设自己的话语规则,它的要义是发现规则;这是一本“太累赘,太长,也太难了”的书……所有这些对“本书的说明”,都是从利奥塔作为作者的角度进行介绍的,而他所介绍的目标就是读者,于是作者和读者又在利奥塔的某种“预设”中完成了链接:“作者天真地希望,他的写作接近于零度风格,而读者随时可以有想法。”有想法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某种智慧的语气,然后忽略书中“不连贯的散文形式”;有想法可以让读者心血来潮在没有阅读此书的情况下“谈论这本书”;有想法甚至可以让读者完全放弃这本书,因为利奥塔寓言下一个世界“将不会有书籍存在”,因为读书太花时间,因为书只是“被打印出来的物体”,因为书的信息完全可以被传媒、电影、新闻访谈、电视节目和录像带取代。
在利奥塔看来,这本书已经不是“我们时代”的节奏,一边是作者进行着不预设话语的反思,另一边则是在零度风格中允许读者忽略、放弃这本书,作者和读者之间是不是也由此进入到“异识”之中?作者的文本和读者的文本是不是在零度中构建的异识?甚至作者的时代和读者的时代乃至整个时代都是异识的隐喻?在这里异识成为了利奥塔对于本书的一个反思内容:反思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发生”,它留下的开放性问题就是“发生了吗?”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预感到了唯一的读者也是“发生了吗?”但是在作者永远不知道的情况是:“发生”的语位到底有没有抵达终点?似乎在这个关于“发生学”的问题上,无论在语位表达上还是在语用事件上,利奥塔都认为作者不该知道,“他仅仅知道,他的无知是最后的抵抗,唯有如此,事件才可以对抗可计算的时间运用。”
对读者、对时代、对写作本身,利奥塔都进行了反思,反思指向了“发生”,指向了“发生”的此刻,但是当对“发生”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异识的反思也变成了一种意识,而这种异识却让作者在无知中进行了最后的抵抗,这抵抗又成为对异识的另一种反思,“这本书的标题意味着在异质的风格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为什么有异识?异识当然是对于共识而言的,利奥塔认为,异识表明的是至少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冲突状态,由于缺乏对双方都适用的判断标准,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方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合法。”如果对两者采用单一的判断标准试图消除异识,那么这就变成了一场缺少公共话语标准支撑的诉讼官司,至少会伤害到其中的一方,如果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标准,那就意味这两者都会受到伤害。异识是冲突状态,无法消除异识就会造成伤害,所以异识的存在不是“发生了吗”的问题,而是已经发生了的沉默。
那场诉讼发生在“奥斯维辛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当然发生了,但是“发生”的此刻却成为了一种异识。法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弗希松自1978年以来,对大屠杀灭绝的叙事提出质疑,他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不存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根本就是一个历史谎言,它的受益者是以色列国和犹太复古主义,之所以提出不存在的论断,他的逻辑是:要确认毒气室的存在,唯一能接受的目击证人就是它的受害者,“现在,据我的对手所言,不该有死了的受害者,不然毒气室就不是他所宣称的那样。因此没有毒气室。”利奥塔对弗希松逻辑的解读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部分当事人消失了,幸存者很少谈论它,即使有人说起它,怎么知道这一情况确实存在?是不是证人的一种臆想?如果大屠杀的确存在,那么证人的证词就是假的,因为要么他也应该消失,要么他应该保持沉默,即使能够讲话,也只能证明自己的独特经历,这一经历是否属于这一境遇还有待证实。按照弗希松的理解,“要么你是错误的受害者,要么你不是。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在证明自己是时,你就错了(或者你在撒谎)。如果你是受害者,但既然你还能证明这一伤害,那么这一伤害就不是伤害,你在证明自己是受害者时,还是错了(或者还是在撒谎)。”
这不是就是普罗塔格拉所说的悖论?“居然要受害者来举证他们所受的伤害!”当证人保持沉默,当法官充耳不闻,当证词变得矛盾,这就是“完美的罪行”,而“完美的罪行”之所以无法自证清白,就在于异识的存在:原告在法庭前提出控告,而被告则摆出论据证明指控无效,这也就意味着原告被剥夺了论辩的手段,由此沦为了一个受害者,“当调解冲突以一方的习语进行,而另一方所遭受的伤害并不用那一习语来表达时,双方的‘异识’就出现了。”大屠杀的确发生了,但是在庭审的时候,它却不再是一个被给予的事实,而是要求建构程序并根据主题得以实现的机会,正是这个建构的过程产生了异识。利奥塔认为,异识不是一个“诉讼问题”,而是一种“无法证明”的情况,控诉的人可以被听到,而受害者本人即使与控诉的人是同一个人,也被迫陷入沉默,“他们不说话,是因为他们在说话时会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即一般情况下,有人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他们说话的能力。”
| 编号:B83·2240611·2132 |
利奥塔将异识问题置于语言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之下,他认为异识关涉的是语位问题,语位不是一个从说话者到受话者且与两者不相干的信息,说话者、受话者、指称和含义构成了语位所表象的世界,推理、认知、描述、质疑、指示、命令构成了不同的语位体系,之所以语位之间不可转译,就在于它们是两个异质之间的语位,这种异质表现为语位被交谈、质问、论辩、心理分析的谈话、忏悔、批评性的评价、形而上的表述所替代;或者否认了四个语位项当中的一个而产生了否定的语位,继而取代了沉默——弗希松即使承认幸存者的沉默并不一定证明毒气室不存在,但是在否定语位中异识也不可避免存在,也就是说,异识是是语言的不稳定状态和瞬间,“在这种状态下,某样东西可以用语位来表达,却尚未被表达。”所以要消除异识的存在,就必须从语位上构建新的规则,利奥塔将这种规则称为“语位链接”。
一方面,利奥塔他承认异识不可避免,他也认为还没有普遍的话语风格来规范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异识反而打开了一扇门,“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关键,就是在创造语位的过程中,见证这一异识。”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好”的链接将判断合法化,至少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拯救思想的尊严”,而思想、认识、政治、历史、存在,都涉及语位链接。承认异识的存在,也发现语位链接的作用,当然就需要建立起新的受话者、说话者、含义和指称,“由此让错误得以找到表达的途径,让原告不再沦为受害者。”如何建立语位新的规则?利奥塔通过反驳高尔吉亚指出的四个沉默,提出了思想和语言之间存在的工具性关系,“这种关系遵从某种技术模式:思想有目的,而语言提供手段。”思和言之间的关系,利奥塔虽然是从技术工具的模式来考察,结合柏拉图的观点和实践,利奥塔将其变成了思和言的同一性问题,它所言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用嘴所说出的东西:指称也就是说话者,“存在与思考是一回事。”
柏拉图提出的改变、模仿、劝说,就是建立起了论证的规则,他预设了受话者容易被感动的能力,也预设了说话者掩饰、隐藏和伪装的能力,“我不是说话者,我只是神或英雄的传话者:我不过是化身为死去的英雄,化身为巴门尼德的女神而已。”通过把神看作是受话者,并以摹仿的方式将神放置在说话者的位置,由此完成了摹仿的诗学,建立起了语位的链接,虽然摹仿被看做是第二自然,是伪造和助长了不得体的东西,但是利奥塔认为,“摹仿是必要的,语言是在我们年幼之时,在保姆和母亲所讲的故事中就已经切近我们的东西。”只要在摹仿中不制造谎言就会是一种对话,它不是要彻底征服对方而是要达成一致。同时,利奥塔考察了发生异识的另一个可能,那就是指称问题,“当受害者语位的指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对象时,你又如何判断存在着异识呢?你又如何证明这一情况确实存在?”
在指称和实在之间是不是存在错误语位?产生这种错误语位的指称并非是虚无,而是指向了另一个对象,在这里利奥塔认为必须进行对象的命名,“每个指称都有一个名称,每个名称都有一个指称。”指称进入名称网络才使得实在的定位成为可能,“名称之所以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它是空的,是不变的。”而实在就是被放入由世界标明的场域,“实在可以同时被赋义,被实指,被命名。”如果指称把“此时”转换为一个日期,将“此地”转换成一个地点,将“我”“你”“他”转换为让、皮埃尔、路易,那么当下发生的语位表象出来的世界就被命名了,固定的意象也就变得独立了。另外,利奥塔也区分了表象和处境,语位在被表象出来的瞬间,它是捉摸不定的事件本身,说话者、受话者、指称和含义都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将一个世界呈现给人,也就是说,它只是语位事件的“发生”,发生了什么并不知道,但是当把语位放入到具体情景和关系之中,建立彼此的关联,它们的意义、内容、性质和价值就被确定了,就可以和“某个被给予的东西”打交道了,“与它打交道,就是把它放在某个处境之下,将它放置在某个语位世界之中。”
回到奥斯维辛问题,利奥塔认为,这个语位所表象的世界,根本没有受话者,因为纳粹制定法律不必向任何人请示,“受话者的缺席也是证人的缺席。”甚至利奥塔认为,在党卫军和犹太人之间,连异识都不存在,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表达式,“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进行审判,连拙劣的摹仿都没有必要。”所以根本没有“发生了吗?”的此处和此刻的处境,存在的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语位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犹太人的话语被漠视,被推入了遗忘的河流。在这里利奥特认为,受话者必须被赋予义务,语位也必须是义务句,“在新的语位中,他不再是受话者,而是说话者,而新语位的关键不再是服从,而是说服,让第三方相信他自己有要服从的理由。”这是道义所在,信仰所在,自由所在。
利奥塔对于异识问题的阐述,并非是要解决奥斯维辛以及“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问题,而是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真正赋予哲学新的意义,在关于进步、社会主义、富足、知识等叙事的现代形而上学教义陷于衰微之时,当“新的这个,新的那个,后这个,后那个”成为理论批评标新立异的存在而带来懈怠的时候,哲学家反而更应该关注异识、发现异识,并在语位链接中寻找新的规则和表达方式,因为哲学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忘记异识,在所谓的共识中建立既定的风格,“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治霸权。”所谓知识分子制造了神话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又变成了关于人类的宏大历史,而历史意味着对名字的消灭,真正的哲学家需要通过异质的叙事完成自我救赎,这种叙事就是卡西纳瓦的“小故事”。
“在卡西纳瓦模式中,每一个miyoi(神话、故事、传奇、传统叙事)的解释都是以固定的格式开始:“下面是……故事,和我历来听到的一样。现在轮到我来给你们讲故事了,听着!”而结尾通常是一个不变的公式:“关于……的故事就讲完了。给你们讲故事的人是……(卡西纳瓦人的姓名),白人叫他……(西班牙和葡萄牙姓名)。”在这一故事中,叙述着从来不把自己定义为叙述的第一作者,他首先是受话者,然后才是说话者,在被前一个叙述者提及的时候,他还处在指称的位置上,所以这种叙事模式构建起了叙事者的说话能力,受话者的倾听能力和指称的处事能力,更重要的是,叙事不需要特定的程序为自己的合法化奠基,它的合法性源于自身,源于自身不断被讲述的事实,所以利奥塔认为,“权威不再来自起源的神话,而是来自一个理念,它把自身的目的加于语位之上,允许消除话语风格之间的异识。”
正在链接和将要链接的语位存在着充满异识的区域,理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异质性,所以在“发生了什么”和将要发生之间也是一个异识的世界,所以“此刻”必须进行链接,而链接不是为了制造异识本身,而是在“发生”中看见历史的征兆,甚至预判“发生”:“我们不能制订关于发生的政治计划,但是你可以见证它的发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