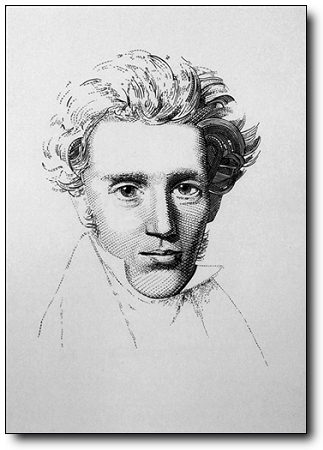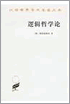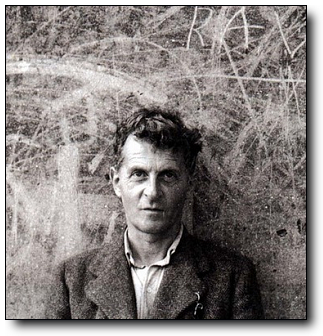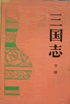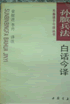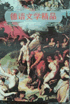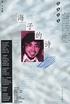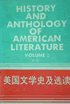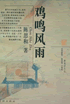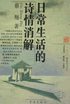|
编号:C92·1960421·0278 |
| 作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92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5.80元 | |
| 页数:163页 |
米兰·昆德拉就是听到了犹太人的那句谚语而开始思考的:“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只不过米兰·昆德拉不害怕那种欧洲传统的小说观被自己亵渎,他只是表明自己的立场、风格。这位东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将政治与戏谑、寓言与诗歌、死亡与玩笑之间对立的东西化解得一丝不挂,余下的就只有你精疲力竭的思考。这是一部笔记体的对小说发表个人看法的集子,有对欧洲小说发展的见解,小说创作的心得,对小说未来的一些假设,共分七章。
这样,欧洲的认同的形象正在远遁到过去。欧洲人,是对欧洲怀着乡愁的人。
—《第六章 七十一个词》
七十一个词,是碎片的词,是单一的词,是在翻译过程中消失的词,是用自己的态度检阅的词,当一个时代因一九一四年的大战让世界变成陷阱,当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道德使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当科学的片面性使存在变成简单的技术和算术,当卡夫卡研究学者在猜想卡夫卡中杀死了“卡夫卡”,那个站在欧洲小说精神最初地平线的人,如何才能怀着最后一丝乡愁?如何才能转身望见最后的影子?如何才能在词语的精神中抵抗“存在的被遗忘”?
欧洲,是理性主义开启的欧洲,是具有“认识的激情”的欧洲,却也是被“或者,或者”带向无力的欧洲,是被技术缩小而走远的欧洲,在远遁而去和转身缅怀的夹缝中,米兰·昆德拉希望看见一个重新发现的欧洲,一个在小说里重生的欧洲,“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是欧洲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是在不同的语言里进行的,但它属于整个欧洲。发现的连续不断(并非写出的作品的增加)造就了欧洲小说的历史。”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欧洲,那个发现连续不断精神的人,米兰·昆德拉说,他叫塞万提斯。
“随着塞万提斯而形成的一个欧洲的伟大艺术不是别的,正是对这个被人遗忘的存在所进行的勘探。”为什么塞万提斯发现了被人遗忘的存在,并对它进行勘探?被人遗忘,是存在的被遗忘,海德格尔说,存在是in-der-wrelt-sein,即,存在在世界中,存在在世界中,存在就是本体,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人与世界的关联犹如蜗牛和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它是他的维度,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也变化。”当笛卡尔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地位,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其实就已经将这种“存在的被遗忘”种下了危机的根,人成为一种主体,他开始统治世界,开始占有世界,这是理性的人,也是简单的人,当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世界其实被缩小成“一个简单的技术与算术勘探的对象”,当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力量超越了人本身的力量,他原本的具体生活和“生活的世界”被排除在视线之外,也就说,存在的被遗忘,因为强大的理性创造了发达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反过来占有和超越了人,使人的“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利益–“它预先早已被黯淡,被遗忘。”
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爆发使世界变成陷阱,这是一个被缩减为事件因果连续的世界,这是一个“认识的激情”作为欧洲精神的本质而消失殆尽的时代,这是人被科学的片面性统治而在没有存在可能性的现实,而在米兰·昆德拉看来,这种被胡塞尔定义的危机在小说中也暴露无遗,人的理性需要一个善恶泾渭分明的世界,它以某种命运的“或者,或者”状态显现出来,而这种“或者”正是包含了对人类事物的基本相对性无力承受,使得小说的智慧难以把握和理解;而理性意义的一个悖论是:当理性获得全胜,它必然会在夺取世界中把自己的意愿变成一种纯粹的非理性,“因为不再有任何可被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成为它的障碍”。
当上帝死了的时候,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唯一的神性真理解体,于是出现了不同的相对真理,而那个唐吉坷德也终于在欧洲的理性世界中走出了自己的家,他不认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对着风车作战,这是一种可怕的模糊,这种模糊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恰恰就是现代世界和小说诞生的序曲,因为它取消了唯一性,取消了统治的力量,取消了神性真理,开始发现人存在的诸多可能性。当米兰·昆德拉在塞万提斯那里发现了小说的伟大意义,欧洲却以另一种方式远遁而去,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有用一种怀乡病来重建小说,重新寻找被遗忘的“存在”,重新走进“生活的世界”。
“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与模糊性基础上的这一世界的样板,它与专制的世界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的是相对性,排除的是怀疑,排除的是疑问,当然也排除存在的可能性,所以站在专制的对立面,米兰·昆德拉需要对欧洲小说的精神重新进行定义。在他看来,人的意义在于存在,存在就是世界的本体,所以小说必须关注、唯一关注的就是自我:我是什么?通过什么我才能被捉住?
自我在米兰·昆德拉看来,首先就是一个行动的本体,因为行动,他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因为行动,他成为个体的人, 引用但丁的那句话就是:“在任何行动中,人第一个意图都是揭开自己的面貌。”所以,行动是行动者的自画像,但是行动在过去的小说世界里,却遇到了一种悖论,那就是人最后还是变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被塑造,他被虚构,他从属于情节和结局,甚至他成为作者忏悔的工具,在外界的规定性里人最终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所以米兰·昆德拉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人的可能性是什么?他自己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给出的答案是:“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在世界变成的陷阱中对人类生活的勘探。”
对人类生活的勘探,使他本身就成为一个可能的人,托马斯到底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并不重要,特丽莎的“生活只是她母亲生活的延续”到底指的是什么?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对人物的外表似乎只字不提,对人物的过去也是吝啬笔墨,因为,“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他是一个想像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当取消了具体性、确定性、描写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把小说中的人物只当成是一种客体。所以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在米兰·昆德拉那里,其实变成人:人是实验性的自我。特丽莎就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当她在镜子前看自己的时候,她想象自己的鼻子每天长出一毫米,在这种想象中,她其实进入到了一种可能状态中,一种实验性的自我里,特丽莎是不是还是那个特丽莎,他者的特丽莎是镜子中的特丽莎,还是鼻子每天都在长的特丽莎?
可能是一种模糊,模糊是一种存在,所以在特丽莎的实验性的自我里,米兰·昆德拉就是给了她一个捉住存在的编码,它就是词语: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每一个词语都是一种可能,每一个词语也对应着一种自我,就如“晕眩”:“……晕眩,就是沉醉在自己的软弱中。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但又不想反抗它,而是任其下去。人因自己的软弱而沉迷,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所有人面前瘫倒在大街上,希望脚踏在地上,在比地还要低的地方。”理解特丽莎的可能,就是理解晕眩,理解软弱,理解田园诗,理解灵魂,理解天堂。
所以为了不使人处在世界的那个正在缩减的漩涡中,为了使个体不被宿命般的暗淡,为了使存在不堕入遗忘的深渊,米兰·昆德拉提出了小说的“四个召唤”: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和时间的召唤。游戏的召唤是建立一种可能性,梦的召唤是达到梦与真实的混合,思想的召唤使得小说能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而时间的召唤就是把历史放进小说的空间里–小说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也不是小说必须遵守的时间线索,所以米兰·昆德拉处理历史背景提出了四个原则:尽可能简练;只抓住有揭示意义的背景;历史只写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写人;“历史背景不仅应当为小说的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况,而且历史本身应当你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
当然是对于线性时间的否定和颠覆,包括历史,包括现实,其实都不是被时间标注的具体事件,而是关于存在的可能场所,“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不是在写一个具体的人,不是在具体的历史中,这是米兰·昆德拉建立可能性小说的两种方法论,所以在这些方法论之上,他阐释了关于小说结构的艺术,在他看来,这些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在小说中寻找那个“未完成的部分”:它必须有一个彻底剥离式的新艺术,永远走向事情的中心;必须有一个小说对位式的新艺术,在创造对位法中,“把哲学、叙事与梦连接为一支音乐”;必须有一个专具小说特点的论文式的新艺术,它是假设的、游戏的,讽刺的,它以假定和疑问的方式制造可能。无论是彻底剥离,还是对位法,或者是论文,其实就是要模糊小说结构的清晰性,就是要取消小说叙事的确定性。
但是主题的统一却不可抛弃,这是小说连贯的保证。当小说中的人物变成实验性的自我,当小说的历史变成对于线性时间的颠覆,当小说的结构中出现了未完成的部分,那么作者又会在哪里?他的可能性体现在何处?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就像詹·斯卡塞尔写的诗人一样,不是发明诗,而是在诗后面某个地方“已经很久很久”了。小说家不是写小说的个人,不是一个名字背后具体的人,他实际上也是一种可能–他不发明,他只发现,“作为人的可能性,它存在’已经很久很久’。”米兰·昆德拉从卡夫卡身上发现了这个在后面某个地方的作者,他认为卡夫卡制造了“卡夫卡现象”,而这个现象不是指向社会学或政治学,在他的小说中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商业,没有产业和产业朱,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政治,没有警察,没有军队,卡夫卡现象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逐渐集中的权力趋向于神圣化;社会活动官僚化;它们把所有的机关改变成使人一眼望不尽的迷宫;由此而引起个人个性的丧失。”所以米兰·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现象更象是代表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不确定的,它几乎永远伴随着人。”
它是一种存在,一种可能,一种现实,作为小说家,卡夫卡提供了一个样本,它让作者消失在作品之中,也成为一个可能的人,成为未完成的那部分,或者说,小说家本身就是一个文本。但是当塞万提斯远去,当卡夫卡远去,当穆奇尔远去,当K、帅克、帕斯诺、艾斯克、于格诺这些镶嵌在可能性版图中的人物远去,甚至“卡夫卡研究学者们正是在试图猜想卡夫卡时,将卡夫卡杀死的”的悲剧发生之后,小说家其实也在这场危机中取消了可能性,而站在了作品之前,甚至成为一个公共人物。这是大众传媒时代的危机,“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它们作品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
说出这段话的时候,米兰·昆德拉正站在耶路撒冷奖的领奖台上,正成为一个公共人,正被大众传媒报道,这像是一个悖论。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在这样的悖论中,那个欧洲到底是远去了还是回来了?塞万提斯的遗产是被继承了还是被诋毁了?或者说,他代表着确定的、那个叫做米兰·昆德拉的自我,还是永远想在作品后面消失的人?或许,欧洲只能成为一个可能的欧洲,一个怀想的欧洲,一个不是地理概念在存在意义上的欧洲,永远锁进了现实的“未完成部分”里:
如果说在我看来,欧洲文化在它的外部和内部,在它最珍贵的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的特殊思想的尊重,对个人享有的私生活不被侵犯的权利的尊重上受到威胁,那么我认为欧洲精神的这一珍贵本质象被放进一个银盒子一样,被放进了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