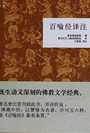 |
编号:B52·2171210·1435 |
| 作者: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33.00元 | |
| ISBN:9787101086362 | |
| 页数:447页 |
《百喻经》 ,全称《百句譬喻经》,是古天竺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天竺三藏法师求那毗地译。《百喻经》称 “百喻”,就是指有一百篇譬喻故事,但现存的譬喻故事只有九十八篇;之所以称之为 “百”,有两种说法,一就整数而言,二是加上卷首引言和卷尾侮颂共为百则。《百喻经》全文两万余字,结构形式单一,每篇都采用两步式,第一步是讲故事,是引子,第二步是比喻,阐述一个佛学义理。它从梵文译成汉文,距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百喻经译注》以日本《大正藏》本为底本,采用《金藏》(仅存卷二、卷三)、《高丽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藏》及金陵刻经处本对校,并以他书辅校。
《百喻经译注》:云何得知泥洹常乐?
贫人见已,心大欢喜,即便发之,见镜中人,便生惊怖,叉手语言: “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
——《宝箧镜喻》
隆隆作响,从早上七点就开始了,一直要到日落时分,甚至有时延长至晚间七点——十二小时,完全变成了 “时间的噪音”,它覆盖了称作白天的时间段。大约也是有了些意见,在小区的楼下竟然贴出了 “安民告示”,解释说这是特殊项目,希望大家谅解。想必是有人提了意见,或者还去投诉了,但在这样一种打着民生工程旗号的项目建设中,用白纸黑字的安民告示,不是为自己制造的噪音寻找到了理由,相反,完全会愈演愈烈。
一个引子。周末在家,是切切实实听到了,闻而起身,推窗而见,那些挖掘机、推土机忙得不亦乐乎,隔着那一道墙,以为是隔绝了声音,以为避于一处而不见,但是声音是具有穿透性的,而在高楼之上俯视,亦是收入眼底。但是当收回目光,关闭窗户,是不是可以关闭耳朵?当打开图书,进入阅读,是不是可以忘记噪音?隔绝的不是底下的围栏,或者就是当我打开一个世界的时候,其余一切都如云烟,不闻也不见。
一种境界。是阅读之境界,还是无他之境界?翻开书页,从封面到腰封,从目录到正文,又如何进入其中? “譬如外道,僻取其理,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致使将来无得道分,流转生死。”第五则,名为 “渴见水喻”,有人口渴,找到了一条河,但是看着河水却不去饮水,当有人问他,口渴了才追逐求水,既然有谁为何不喝?那人的回答是: “君可饮尽,我当饮之。此水极多,俱不可尽,是故不饮。”因为水太多了,不可能被喝光,所以才不去喝它,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 “愚人”是对这人的一个称呼,站在河边看见河水,本可以解渴,但是担心河水太多而无法饮尽,便放弃了,在说理中,对这个故事的说法是: “譬如外道,僻取其理,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致使将来无得道分,流转生死。” “见水不饮”便是非佛的外道,对于佛的教理断章取义,由于自己无法受持戒律,于是一条也不受,这一种放弃便是再无得到的机会,故而 “流转生死”,在俗世的轮回之中被取笑。
外道便如 “他者”,总是在听闻中使自己成为 “愚人”,比如 “食盐喻”,有人开始吃的菜没有放盐,于是感觉淡而无味,待主人放了盐,觉得味美,于是就想: “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一勺盐成全了美味的食物,但食盐本身并不美味,而愚人 “便空食盐”,最终是 “食已口爽”,当口舌受刺激而失去味道,反而把盐看成了一种 “恶者”,从 “美者”到 “恶者”,便是外道所致, “譬彼外道,闻节饮食可以得道,即便断食,或经七日,或十五日,徒自困饿,无益于道。”有愚人认为甘蔗很甜,如果把甘蔗的汁水浇灌甘蔗,那不是更甜吗?而最后的结果是: “返败种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说理: “欲求善福,恃己豪贵,专形挟势,迫胁下民,陵夺财物,以用作福,本期善果,不知将来反获其患殃。”无非也是让 “美者”变成了恶果。
他者之存在,总是遮蔽智慧,也便是自己成为了 “愚人”,《乘船失釪喻》就如中国的寓言 “刻舟求剑”, “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所以, “如外道,不修正行,相似善中,横计苦困,以求解脱。”反而将自己困于其中不得解脱。外道而来,使自己 “迷失津济,终致困死”,《杀商主祀天喻》里那一行商人为了渡过大海,找到了导师,不想到旷野之中竟遇到了天祠,要让他们进行 “人祀”, “我等伴党,尽是亲属,如何可杀?唯此导师,中用祀天。”于是他们将导师用作祭祀,但是祭祀完成,却又陷入了迷途,因为再无人能够教 “入大海之法”。《婆罗门杀子喻》中说有一个婆罗门自称见多识广而且自持才高,通晓各种占星技艺,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竟抱着小二哭泣,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说: “今此小儿,七日当死,愍其天伤,以是哭耳。”别人劝他命运难料,预计可能会出错,而婆罗门竟然给他说道理: “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记终无违失。”为了不 “违失”,竟在第七日 “自杀其子,以证己说”,而那些人知道他的儿子死去,都感叹说: “真是智者,所言不错。”为了自己的预言,甚至为了让自己成为 “多知”的人,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牺牲品, “犹如佛之四辈弟子,为利养故,自称得道;有愚人法,杀善男子,诈现慈德,故使将采,受苦无穷。”
此为愚人法,就是自己在他者的世界里进入了迷途,《以梨打头破喻》里愚人让梨打自己的头,甚至被打破,他却说: “如彼人者,侨慢恃力,痴无智慧。见我头上,无有发毛,谓为是石。以梨打我,头破乃尔。”笑的是梨的愚笨,竟然以为自己的头是石头,而别人却笑他: “汝自愚痴,云何名彼以为痴也?汝若不痴,为他所打,乃至头破,不知逃避。”所以在说理中说: “不能具修信、戒、闻、慧,但整威仪,以招利养。”《愚人集牛乳喻》的愚人本来天天挤牛奶,后来觉得不如 “就牛腹盛之,待临会时,当顿轂取”。把牛奶盛装在牛腹中,等到宾客来了,牵来了牛,不想哪里还有牛乳?说理: “愚人亦尔,欲修布施,方言: “待我大有之时,然后顿施。”有愚人记得乘船之法,结果却不解其意, “虽诵其文,不解其义,种种方法,实无所晓。”《伎儿作乐喻》中,艺人在国王面前演奏,国王说会赏给他一千钱,等到他向过往索要,国王对他说: “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乐汝耳。”你给我听的音乐是愉悦我的耳朵,而我给你钱的承诺也只是娱乐你的耳朵而已。
为祭天而杀导师致使迷途,为彰显自己才能而杀儿子,为笑话梨头不识自己的头而忍受被打破的痛,把牛奶盛装在牛腹中,承诺只是娱乐耳朵,凡此种种,都只是在那个 “外道”里,而在外道中求道,则是邪见,不管是搆驴乳喻、田夫思王女喻、驼瓮俱失喻,说理为: “外道凡夫亦复如是,闻说于道不应求处,妄生想念,起种种邪见,裸形、自饿、投岩、赴火;以是邪见,堕于恶道。”闻于外道而生妄念,最终是在邪见中 “堕于恶道”,那些裸形者,那些自饿者,那些投岩者,那些赴火者,都被邪见所劫持, “以为得果之因”,却不想 “反致毁呰”。
而其实,只在外道中求道,本就是因为贪利而求方便,《人海取沉水喻》中说有人入海去搜集沉水香,沉睡香因其色黑芳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得名。当几年才搜得一车,于是去市场上交易,不想因为价格昂贵无人问津,他看到有人在卖炭,买者络绎,于是学卖炭 “速售”,最后 “不得半车炭之价直”。沉水当然不同于木炭,但是为了 “速售”,把沉水当成了木炭, “世间愚人亦复如是,无量方便,勤行精进,仰求佛果,以其难得,便生退心”。正是在求佛果中遇到了困难,便生退心,也便有了贪求方便之法:有人生食胡麻子味道不好, “熬而食之为美”,于是 “不如熬而种之,后得美者。”最后是熬而种, “永无生理”。有人认为自己妻子的鼻子不美,看到有人有美鼻,竟 “割其鼻,寻以他鼻著妇面上”,结果反而受到损伤, “虚自假称,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复伤其行,如截他鼻,徒自伤损。”有贼人为了贪利,用偷来的锦绣裹破旧衣服;有父亲为了不让盗贼将儿子的耳珰拿走,自己又无法拿下来,竟然 “斩儿头”;有愚人认为木工可以造就三重楼,竟然懊悔: “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外道中求道,为方便,为贪利,其实是 “迷乱上下,不知法相”,就如《山羌偷官库喻》中所说, “借以为譬,王者如佛,宝藏如法,愚痴羌者犹如外道。”所以如要不颠倒,不迷乱,就是要有次第,有在家次第、出家行住次第、还灭次第、流转次第、入僧次第、增长次第、入定次第等, “于各别行相续中,前后次第,一一随转,是谓次第。”次第不见,秩序以乱,或者是为外道所迷,或者为我见所执。《宝箧镜喻》中的那个人为贫困所扰,贫穷困苦便是一种 “他者”世界,所以他需要一种自救,当他发现放有珠宝的宝箧时,便想到可以偿还那些欠债,可以结束穷苦生活,但是却看到了珍宝之上的那面镜子,而且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于是生气地说: “我谓空箧,都无所有,不知有君在此箧中,莫见瞋也。”以为箧子里只装了珍宝,不想还有一个 “你”。此 “镜中人”本是我之镜像,是虚像,但是却当成了实体,于是执着于镜中的我,此为 “我见”: “为身见镜之所惑乱,妄见有我,即便封著,谓是真实。于是堕落,失诸功德、禅定、道品,无漏诸善、三乘道果一切都失。”
执着我见,还有《见水底金影喻》儿子和父亲看见水底有真金,儿子便下水捞取,不想一无所获,后来父看见水底真金的影子,才知到真正的金子在树上,父亲说: “必飞鸟衔金,著于树上。”于是不执著于水中之影, “即随父语,上树求得。”说理曰: “于无我阴中,横生有我想。如彼见金影,勤苦而求觅,徒劳无所得。”还有《伎儿著戏罗刹服共相惊怖喻》有一帮伎人赶路,其中有一人患病,于是穿着戏本罗刹的服装,向火而坐,当时有同行者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火边坐着一个罗刹,于是惊慌而逃,其他人不知其故,悉皆逃奔。而那个穿着罗刹衣的病人为了找伙伴,也在后面奔跑,前面的人以为他要加害自己,越加害怕, “越度山河,投赴沟壑,身体伤破,疲极委顿,乃至天明方知非鬼。”《人谓故屋中有恶鬼喻》中有两个大胆的人都不怕故屋里有鬼,于是一个人先进去,反复推门,后来者以为有鬼,于是二人争论,一直到天亮, “既相睹已,方知非鬼。”镜子中看见和自己一样的人,是我见;水底看见金子影子,也是我见,把穿着罗刹衣的人当成鬼,无鬼的屋子里自己生鬼,或者都是执着于那个 “我见”: “以我见故,流驰生死,烦恼所逐,不得自在,坠堕三途恶趣沟壑。”
那么,什么是他,什么是我? “推析,谁是我者?”我见,就是执着于有真实自我存在之邪见, “我见者,谓我执,于非我法,妄计为我,故名我见。”而佛教一直强调此身为五蕴所成,虚假不实,如果 “恒执为我,是为我见”。不管是《宝箧镜喻》的身见,还是《观作瓶喻》的边见,不管是《搆驴乳喻》的邪见,还是《父取耳珰喻》的见取见、《愚人食盐喻》的戒禁取见,也都是 “于见道一时断之者”。所以佛教提倡的是 “非我”, “无我”,没有恒常不变的我,也没有灵魂,一切都在那里不停的刹那的生灭着,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不生灭的东西,也找不到一个叫做 “我”的实体存在,世亲造、唐玄奘译《辩中边论》卷中《辩真实品》将 “无我”分成三类: “无我三者:一、无相无我,谓遍计所执,此相本无,故名无相,即此无相说为无我;二、异相无我,谓依他起,此相虽有,而不如彼遍计所执,故名异相,即此异相说为无我;三、自相无我,谓圆实成,无我所显以为自相,即此自相说为无我。”
无相无我,异相无我,自相无我,便是无我的三重境界,便是水底无影,镜中无我。只是这 “我见”如何能超越?成为无我见?《序品》中,在鹊封竹园讲法的时候,梵志问佛 “天下为有为无?”佛说: “亦有亦无。”有和无从人道谷,从五谷到四大风火,从四大风火到空,从空到无,从无到自然,从自然到泥洹的涅槃,于是梵志问: “佛泥洹未?”佛的回答是: “我未泥洹。”所以梵志的问题便是 “若未泥洹,云何得知泥洹常乐?”这颇有 “子非鱼”的那种诘问,而佛说: “汝今不死,亦知死苦。我见十方诸佛,不生不死,故知泥洹常乐。”
我见十万诸佛,是 “我见”却并非 “我见”,而是一种 “离断、常二边,处于中道”的方法,如此,在这通往 “中道”之路上,与诸大比丘、菩萨摩诃萨及诸八部三万六千人俱,以及那些梵志,是需要从我见中解脱而出,在无我中非镜非影非外道,于是静坐下来, “如是我闻”——即使外面隆隆作响,即使开窗而见, “无我者非我、非我所,非我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