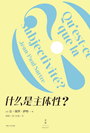|
编号:S32·2200514·1652 |
| 作者:【英】佚名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48.00元当当26.00元 | |
| ISBN:9787544773652 | |
| 页数:132页 |
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宴乐厅,遭到魔怪格兰道尔的袭击,高特武士贝奥武甫率十四勇士前往救援,经过激烈的搏斗,力大无穷的贝奥武甫扯断了魔怪的一只胳膊,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个魔怪前来骚扰宴乐厅,此魔乃格兰道尔之母,是为他的儿子报仇来的,贝奥武甫与她在水潭下的洞穴中展开殊死搏斗,最后用魔剑将她杀死。贝奥武甫凯旋回国后不久,国王海格拉克父子先后死于非命,贝奥武甫继承王位。他成功地统治高特国达五十年之久。就在壮士暮年,国内出了一条毒龙。该毒龙因自己守护的财宝被盗,开始向高特人进行报复。它口吐烈焰,毁灭一切,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贝奥武甫毅然进入龙窟,最后在威格拉夫的援助下,毒龙被除,但老英雄也因受伤过重而献出了生命。史诗《贝奥武甫》早在第六七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全诗共3182行,是英国古代一首长叙事诗,约占现存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
《贝奥武甫》: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抗拒
我要么创建一件英雄的业绩,
要么让这座宴乐厅见证我的末日。
——《三 鹿厅盛宴》
他一只手的力量与三十个勇士的力量相当,他曾俘获五个巨人,捣毁了巨人家族,他曾在“大海探险”中用宝剑杀死了九个海怪……他是出身高贵、用力过人的英雄,他在同时代人中堪称卓越超凡。而这这不过是贝奥武甫这个英雄过去的传说,当那个恶魔格兰道尔在丹麦国里制造血腥,当格兰道尔的母亲在神秘的疆土建造“黑暗的深渊”,甚至当贝奥武甫成为高特国王出现了“毁灭一切活着的生灵”的火龙,作为英雄和国王的贝奥武甫如何再次创造奇迹?
口头形式流传于六世纪、完成于八世纪的《贝奥武甫》,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古老、最长的一部较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欧洲最早的方言史诗,3128行诗占了现存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文学的三大英雄史诗。“英雄史诗”的归类其实就已经将诗歌所叙述的题材进行了限制,那就是“史诗”——史诗必然是对于历史的书写,但是当作为英雄的贝奥武甫遭遇到了恶魔及其母亲,遭遇了守卫财宝的火龙,它是不是反而溢出了历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传说?或许这里有一种历史传说化的特点,甚至恶魔和毒龙解构了所谓的历史,但是让英雄在这样的一种对抗中显示起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技能,也体现了其传奇性,在这传奇性背后隐含着一段亦真亦幻的历史虚构。
在《贝奥武甫》中,有一个特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历史的书写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英雄在场的情况下进入到“历史”的里面,使其真实发生:贝奥武甫来到丹麦,帮助丹麦国王赫罗斯加打败了困扰这个国家十二年的恶魔格兰道尔,杀死了格兰道尔母亲建立的黑暗王国;当他回到高特之后被拥戴为国王,统治这个王国达五十年之久,之后在垂垂老矣时又遇到了一条喷火的巨龙,于是只身进入水底,并和勇士威格拉夫一起杀死了火龙,消除了国家隐患,但自己也身受重创最后死去。在这两部分中,贝奥武甫有着不同的身份:勇士和国王,但是无论是身为高特国的勇士到丹麦国降妖除魔,还是后来成为高特国王之后为了本国的安宁而杀死火龙,都体现了一种大局观,而这种大局观正是为了构建一种和平主义的历史。
和平主义体现在贝奥武甫为了丹麦国的安慰,跨越国界完成壮举。他听闻丹麦国王赫罗斯加被恶魔所困,于是精心挑选了一批最勇敢的武士,十五人一起渡海而来,只是为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国际主义风范,所以赫罗斯加说:“这个人童年时我就认识;他的父亲名叫艾克塞奥,高特王雷塞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如今他勇敢的儿子为了友谊来到了我们的国家。”这是一种友谊,而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王后维瑟欧也彬彬有礼地上前与众人见面,这位高贵的夫人把酒敬给贝奥武甫,祝愿他“欢欢喜喜享用美酒,永远受人民的爱戴”,并感谢他“帮助他们铲除祸害”。当贝奥武甫杀死了格兰道尔,赫罗斯加认为贝奥武甫“完成了我们原先千方百计无法完成的伟业”,赠送给他描金的战旗,一个头盔和一副护胸甲,一把珍贵的宝剑,还将最好的马及其马鞍送给了英雄。而当格兰道尔的母亲前来复仇,贝奥武甫再次击败了恶魔,甚至捣毁了整个黑暗王国,赫罗斯加在鹿厅祝捷,当贝奥武甫和勇士们准备返回故国时,他对赫罗斯加说:“只要你需要,我一定能为你搬来救兵,用手中的长矛为你增援效劳。还有,如果赫里斯雷克王子乐意光临高特人的宫廷,他一定能交上许多朋友;伟大的远方客人永远受欢迎。”赫罗斯加非常高兴贝奥武甫的承诺和邀请,他对贝奥武甫说:“你的品行真让我无比欢喜。你给所有的高特人和丹麦人带来了和平,争斗与敌意,先前那么猖獗,都将因你而消弭。只要我一直治理着这个国家,会让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财富,不管是谁来自大洋彼岸,我都要让他得到丰厚的奖赏。”
而在高特国,由于国王海格拉克阵亡在疆场,海格拉克制止赫德莱德也被杀死,瑞典人还杀死了赫莱里克,高特国从此就归贝奥武甫一人管辖,他成为国王之后,积极治理国家达五十年成为一位明主。而其实在海格拉克时候,他并不愿取代赫德莱德的王位,而是极力辅佐王子,“友善地佐他,尊敬他,直到他成年,有能力自己治理这个国家。”表现了一个英雄谦让的风格,但是当战争又让王子死去,贝奥武甫无奈才登上王位,但是他的职责仍是为了高特国的和平,“于是贝奥武甫登上宝座,开始治理高特王国。他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国王!”而当那条火龙肆虐时,年事已高的贝奥武甫又挺身而出,他发出的豪言壮语是:““我年轻时就曾身经百战;如今年事已高,但作为人民的庇护者,只要作恶者 敢从地洞里爬出,我就一定 向他挑战,让我的英名千古流传。”面对火龙,他毫不畏惧,体现了一个英雄国王的担当,而与他一样具有这种担当精神的则是另一个武士威格拉夫,他在众人躲避之时挺身而出,与贝奥武甫并肩作战,但他们最后杀死了火龙,当贝奥武甫深受重伤不治而亡,在最后他说的是:“你是我们威格蒙丁族最后一位武土。命运席卷了我的全部宗亲,身强力壮的人都得告别人生,我现在就将步他们的后尘。”这一番肺腑之言,其实让贝奥武甫有所寄托,那就是新的英雄的诞生,威格拉夫无疑成为一个继承者,而那些所谓的贵族在火龙面前退缩到树林里保全自己的姓名,则变成了一种耻辱。
贝奥武甫时候,百姓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海岬上修建了高大的陵墓,它成为了英雄的纪念碑,而贝奥武甫也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符号,“他们都说世上所有的国王 数他最仁慈、最温和、最善良, 最渴望为自己争取荣光。”这是英雄的一生,贝奥武甫构成了英雄史诗最耀眼的一部分,当他站在人类共同利益上,当他为维护百姓而牺牲自己,英雄的塑造就必须设立恶魔,从这个意义上讲,恶魔格兰道尔将象征着和平的破坏者,象征着战争和暴力,所以在鹿厅宴会上,出征之前的贝奥武甫说:“我要么创建一件英雄的业绩,要么让这座宴乐厅见证我的末日。”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勇气,这是只有英雄才能配的上。而英雄的反面则是恶魔,格兰道尔是“是塞外的漫游者”,它占据着荒野与沼泽,它统治着一片鬼魅出没的土地,而它就是该隐的后代,“那里是该隐子孙的庇护所,自从该隐残杀了亚伯,自己的兄弟,永恒的主就严惩了他的后裔。”而格兰道尔死去之后前来复仇的母亲,则更是邪恶的象征,它是妖妇,它“居住在可怕的水府,寒冷的水乡”,那是一个神秘的疆土,是“野狼的山坡”,是迎风的山岬,是险恶的沼泽,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深渊里,有着无数的恶魔,它们破坏着人类的安宁,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高特国的那条火龙,因为自己的宝藏被偷而报复人类,“可恶的火龙到处寻找他的洞穴,喷吐着火焰在夜间飞行;当地的居民见了无不胆战心惊。”它的可怕是因为“存心要毁灭一切活着的生灵”。
恶魔和火龙,代表着邪恶,所以英雄必须站出来,必须放弃一切的安慰,必须置生命于不顾,也只有英雄的大无畏,才能成就英雄的历史。这是书写历史的第一种方式,英雄是在场的,而在这种在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书写,那就是通过插入的方式,以回忆、吟唱来再现历史,而在这些历史中,也充满了仇恨,充满了邪恶,充满了对立。史诗的引子部分就介绍了“丹麦早期的历史”:从斯基夫之子希尔德,到希尔德之子贝奥,再到贝奥之子哈夫丹,他们都是丹麦可敬的国王,都是为了庇护希尔德的子孙,所以这一种关于丹麦国王的谱系学传递着一种英雄主义,“在遥远的过去,丹麦的王公、首领,如何将英雄的业绩一一创建。”但是正因为怀念,才凸显了现在这个时代的纷乱,那些纷乱的历史一次次被插入进来,成为在场之外的被叙述的历史。
在《格兰道尔袭击鹿厅》中,插入了一段话:“如今还不到时候,翁婿间那场血仇尚未爆发,血腥的屠杀只是后话。”这后话其实是这样的历史:为了避免仇杀,赫罗斯加将女儿嫁给敌国,但战争仍未能幸免,象征王权的鹿厅后来被火烧毁。当贝奥武甫来到鹿厅,丹麦人的庇护者赫罗斯加也说起了一段历史:“你父亲曾经惹过一桩大血仇,他亲手杀死了威尔芬人希塞拉夫。高特国当时因为害怕战争,没有敢把他留在国内。因此,他只好越过汹涌的波涛 来投奔光荣的希尔德子孙。”这是和贝奥武甫有关的家族历史,因为战争贝奥武甫的父亲流落他乡;在贝奥武甫扯下了恶魔的一条胳膊,大家在鹿厅里欢聚时,人群中的一位国王侍从开始吟唱,他背诵了许多古代的历险故事,也把贝奥武甫的故事变成了易于传诵的歌词,后来他也说到了威尔斯之子、英雄西格蒙德杀死毒龙的传奇,这段传奇也有着相互争斗而复仇的影子,丹麦国王海勒摩德是武士的保护者,但是他被朱特人出卖给了他的仇敌丢了性命,而当时最著名的英雄西格蒙德历经千辛万苦,最终也遭遇不测,当时的追随者“始终牵挂着他,许多智者曾经为他痛哭流涕,为这位勇土的离去而悲伤”。
在这次的祝捷中,插入的还有这样一句话:“当时的希尔德子孙预料不到 以后叛逆的阴谋尚能得逞。”这指的是在赫罗斯加死后,赫罗索夫曾发动叛乱,篡夺王位。当贝奥武甫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赫罗斯加赠送礼物,此时吟游诗人又开始讲述故事,他叙述的是芬恩部落的故事,当时有盟约朱特人和芬恩部落各占宫廷的一半,但是这并没有换来和平,芬恩的妻子、丹麦国王之女希德贝尔亲眼看见自己的主人被杀,芬恩部属的人死亡过半,“宫廷于是被鲜血染红,芬恩及其部下被杀,王后被掳。丹麦人的武士把国王的财富,包括项链和各种宝石珍玩——凡是在芬恩家里能找到的——全部装船运走。”在贝奥武甫杀死了格兰道尔的母亲之后,赫罗斯加再次祝捷,他讲起了丹麦早期国王艾克瓦拉的故事:海勒摩德建功立业,给人民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屠杀与痛苦。在贝奥武甫回国之前,宴席上还有人说到了故事,是关于高特的莫德莱丝王后,她年轻时做过很多可怕的坏事,但是后来听从了父亲的教诲,于是嫁给了年轻的武士奥法,“从此以后,她就很少伤害无辜,作弄他人。在皇后的宝座上,她后来还以慷慨闻名于世,她的有生之年,她深深爱着那位武士的首领。”真正的武士让她改邪归正,因为“她的夫君是人间的大伟人,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谁也不能 与他相提并论。”当然,在贝奥武甫准备讨伐火龙时,他想起了赫德莱德的经历,在海格拉克时候,欧塞尔的两个儿子来到了高特,他们背叛了瑞典人的保护,来到高特王国寻求庇护终于招致了赫德莱德的死亡,“由于殷勤好客,海格拉克的儿子 被利剑刺中,受了致命伤。”
因为贝奥武甫成为了国王,瑞典人才不敢冒犯,所以当最后贝奥武甫身受重伤而死去,对于高特人来说,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因为瑞典人可以肆无忌惮前来进攻了,正如威格拉夫所说:“我可以预料瑞典人一定会进攻我们,一旦他们得知我们的国王已经仙逝。”英雄逝去,在埋葬了贝奥武甫之后,高特国陷入了危机,“既然英雄的主公已经弃绝人间的幸福与欢乐,他的子民别想再活得快活,他们将一个个离乡背井。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他们一大早就得把长矛紧紧地握在手上。唤醒武士的声音不再是清越的竖琴,而是乌鸦的聒噪, 它们在气数已尽的人身边低飞,向老鹰叙述它们的经历,夸耀自己如何与狼争食尸体。”于是这个在五十年里都国泰民安的王国因为英雄的离世,再次跌入到了战争的恐慌中,“一位束发老妇为贝奥武甫唱起凄凉的歌曲,一遍又一遍哭诉的忧虑,担心敌人的侵犯,无数的杀戮,战争的恐怖,百姓的凌辱和掳掠即将来临。滚滚的浓烟此时已消失在蓝天。”
这个国家需要英雄,这个时代需要英雄,而对于《贝奥武甫》来说,这一切却都成了幸运,因为主宰一切生死的都是上帝——这一部古代英雄史诗,在不同时代的改写中,它最后变成了一本传递宗教思想的史诗,上帝无处不在。诗人吟唱着上帝创造万物,“诗人在歌唱 遥远的过去,人类的起源,万能的主如何创造大地,让田野充满阳光,周围出现海洋,如何胜利地创造出太阳与月亮,让它们以明清的光辉照耀人寰,如何用树木和绿叶装点世界;如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生命,让他们能够生活,能够呼吸。”当格兰道尔开始在丹麦王国肆虐,于是它便成为了该隐的后代;当贝奥武甫出征,他把生死也交给了上帝,“我不屑于使用刀枪和盾牌,要跟恶魔来一番徒手交战,与他针锋相对,拼个你死我活。最后到底是谁被死神擒获,那只有让上帝来为我们判决。”“命中注定的事,你无法抗拒。”这是所有人都在传递的一个观念,上帝判决输赢,上帝决定生死,上帝主宰命运,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先前的英雄主义则慢慢变成了宿命论,战胜恶魔格兰道尔,战胜妖妇,都是上帝对恶的惩罚,当然最后杀死火龙也是上帝正义的体现,但是当贝奥武甫作为国王亲自去激战火龙,他正是在这种宿命论中渐渐丧失了英雄的气概:“智慧的武士以为自己冒犯了永恒的主,违背了上帝规定的戒律。他的胸中涌起阴郁的思绪,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如果没有威格拉夫的帮助,这位英雄国王将无法战胜火龙,因为他的命运早就注定了:“仁慈的国王总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尘世的生命乃租赁之物,拥有宝藏的毒龙与他一样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英雄只是英雄,他是尘世的生命,而这种生命只不过是向上帝租赁而已,所以最后都要归还上帝。但是英雄之死,最后对于命运的扼腕悲叹,反倒是在削弱这种宿命论,贝奥武甫说:“身强力壮的人都得告别人生,我现在就将步他们的后尘。”老国王说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这是对于命运的无奈,但是在大火燃起的葬礼中,那火焰便成了“可恨的火焰”,即使灵魂脱离肉体,“踏上正直的归宿者的旅程”,那死去之后弥漫的哀伤气息也绝不是对于命运的顺从,从这个意义上,那个讲述者的“我”反倒是一种反宗教式的存在,因为最后他依然把历史还给了英雄,“我们人类 应该用语言尊崇自己的明主,应该用全心挚爱自己的首领,一旦他抛弃肉体,离开人间。高特国的百姓、国王的亲信也就这样悼念自己的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