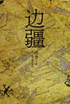 |
编号:C28·2081027·0758 |
| 作者:残雪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 | |
| 页数:336页 |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独树一帜的女作家,也是中国唯一位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 本书讲述边疆某小石城里几个异乡客的诡异生活。多年以前、主人公六瑾的父母为了追求爱情来到边疆的小石城;在那里,他们发现小石城是一个一切事物都处于无形胜有形状态的地方。六瑾成人后,决心重走父母在小石城走过的道路。通过与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觉功能的形形色色边疆人物的交往,她对边疆的事物也产生了荒诞不经的认识和想象。边疆小石城成了一方让人进入异常事物内部的净土。
悦·读:《边疆》:一部残废的先锋
我承认,我对残雪一直没有过份关注,我以前对她的阅读也仅限90年代的《黄泥街》,而用两个月读完她所谓最高峰的小说《边疆》,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冲动,文字,还是那个习惯用文字装点精神虚无的残雪。
边疆地区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屋外的景色总是对人的情绪有巨大的压迫。虽然有这些受难之处,整体上来说她还是喜欢这里的风景。
《边疆》从头至尾都给人设置了这样的阅读障碍,我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一章,然后安然入睡,那些障碍在睡梦中自然消解,我甚至第二天记不起昨天阅读的内容,但是晚上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阅读,那种断层又会重新构建,而我仍然不再依靠思考和回忆来消解。这种阅读的方式一直带给我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阅读残雪的作品,首先要抛弃情节,走进去可能是危险的,我曾这样告诫自己,所以,她在文字内部独自舞蹈,而我在文字外部独自休憩,两个世界是平等的,互不侵犯。
“我潜意识里就是一个边缘人,既不能脱离人群,又对人群厌恶。我不写外部,只关心人的内心和精神的规律。”这是残雪对《边疆》精神内核的自我评价,所以你不能指望用理性的阅读来阐释这个怪异而自负女人的内心,她是孤独的,你不能破坏她的孤独和她共鸣。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的文字,“一定要找到一个混沌的暗示性的东西,向语言的原始性靠近。”任何言说都不能还原混沌和原始,所以残雪的呓语是只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她不会影响一个深夜瞌睡者的状态,更不应该用这样的逃避方式把小说上升到人类精神的内核。
还是要有限谈谈这部小说。
《边疆》和90年代的《黄泥街》一样,都是以某一个地理作为小说的自足封闭的空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城堡。在人性、自然诡异现象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时间的迷宫里走失,六瑾、蕊、阿依似乎都是时间安排的替代品,他们找不到归宿,在每一个可能面前找不到出路。小石城存在他们的恐惧中,存在于时间的建构和破坏之中。残雪在怪异、琐碎、深入、渗透的讲述中,让人在荒诞面前不认识自己,脆弱地生和死。
可以说,残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言说方式没什么创意,现代派的典型手法——分裂贯穿始终,梦魇、自语、神异、死亡,这些手法一一呈现,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拥有惟一的解释权,并将他人隔绝在外,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
尽管作品贴上标签去阐释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但我还是想把她叫作中国先锋文学最后一个舞者,尽管她自己不承认“先锋”这个词。中国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有过冷清的开场和热闹的纷争,但是到了21世纪,许多曾经坚守的作家都消失了,格非、北村、马原、余华 ,这些曾经建筑起中国先锋文学大厦的作家,仿佛都在转身蜕变:北村开始接触影视,马原离开了西藏就只能上台演讲,余华在《兄弟》的回归中抛弃了诗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探索姿态,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他们或长时间搁笔,或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叙述风格,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而似乎只剩下残雪这个西方现代派的“传教士”,在中国文学舞台上独自起舞。
残雪是孤独的,更是寂寞的。她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在自我实践中把西方“后什么现代,还主义”的东西,以君王的方式统治她的读者,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自负,甚至用身体的坚持来贩卖这样的信仰:“我觉得我任重道远啊。在这个国家推行我的文学理念,还要有很长时间,所以我拼命锻炼身体啊,搞到底啊……我锻炼了有25年了,每天长跑,现在半个小时,年轻的时候一个小时。”“我创造性的东西已得到世界的公认了。”
在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更多创造性的残雪,过去西方试验过的一切叙事样式都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就像她最初的职业一样,只能拼凑、粘贴布料,她不是设计师,她只是一个裁缝。
其实,我无意亵渎这样一个被所谓的西方承认的作家,我应该像对这本书的阅读一样,和她的文字互不侵犯,所以我更愿意把残雪还原为一个叫邓小华的裁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