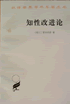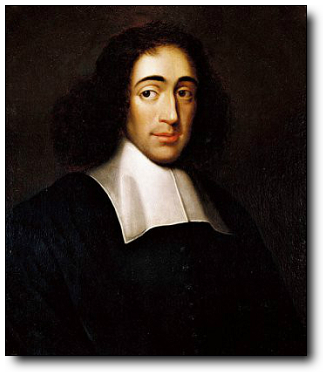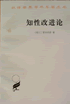 |
编号:B34·1961005·0334 |
| 作者:(荷兰)斯宾诺莎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版本:1960年2月第一版 |
| 定价:3.80元 |
| 页数:60页 |
作为对培根《新工具》和笛卡尔《方法论》进行批评的论著,斯宾诺莎带着理性主义的光环,重新提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像题目所言,“知性”一词在斯宾诺莎眼里成为“制造理智的工具”,从而“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本书共五章110节。
《知性改进论》: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完善
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导言:论哲学的目的》
当讨论了哲学的目的,当言说了知识的种类,当定义了知性的本质,当区别了虚构的危害,当分析了界说的条件,第60页,却是“余缺”。放在括号里的“余缺”,是注释的词语,是最后的终点,两个字,却似乎制造了关于文本的最后事件,余缺是没有完成的论述,是再无继续的断裂,是悬置在那里的阙失,在“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它是不是在走向一条路径的断裂处,留下了关于知识的最后命运?
《论界说》的部分,在明晰了知性的性质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斯宾诺莎摊开更大的一张纸,思考了更为明确的观念、本质,甚至天赋的力量,准备走向一种更为宽阔的哲学大道,却戛然而止于一个悬念众生的“余缺”,那么在这个断裂和阙失之后,知识会去往哪里?知性会在哪里被认识?真理会在哪里显现?甚至,是不是这一个“余缺”的事件会将所有关于真知识的论述都变成无功而返的遗憾?被写在括号的“余缺”之前,斯宾诺莎说出的那句话是:“我们已经充分说明,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并不是由于具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因而被称为错误或虚构。其所以被认为错误与虚构,完全由于知识的缺陷。”知识的缺陷,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就如这论述的缺陷,在最后余缺的结果面前,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个“错误与虚构”的原因?当面对第60页的余缺,我们的错误与虚构又从而何产生?
错误或者是对于文本戛然而止而导致论述最终走向终结的错误,虚构或者是对于知性被悬置而有一种否定式存在的虚构,那么这最后一句的“知识的缺陷”当成为文本的一部分的时候,斯宾诺莎似乎设置了一个隐喻:就是因为对于知识的缺陷,才使得我们产生了对于知性的“错误和虚构”,才使得我们认为“余缺”断裂了以前的一切论述,才使得我们在通往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茫然无措。这是一种感官的体验,这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这是一种可疑的观念,而在《论想象》里,斯宾诺莎早就以预言的方式说过:“我们可以看出,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因为余缺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从虚构的观念出发,所以我们内心有了某种想象,而其实,不管是放在括号里的“余缺”,还是第60页的断裂,都无关于真知识、真观念,无关于知性,甚至无关于天赋的力量,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知性改进论》已经指明了那一条通向事物真知识的途径。
因为知性是必然性,是永恒性,是确定性,是无限性,是本质性,“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斯宾诺莎已经在否定的“余缺”之前,形成了一个肯定的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知性是自然之光,本身没有带有被否定、可能性的病症,只要被真正的认识,那就一直通向真理的终点。所以不如从“余缺”的现象返回,重新回到从“导言”开始的肯定状态:“论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斯宾诺莎说是善,是一种单独支配心灵的善,它是唯一的,它是肯定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但是,在斯宾诺莎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当做幸福的东西,却并不都是善,人们把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当成终极目标,这些东西的确能够让拥有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美好,但是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却容易让人产生贪欲,而在贪欲支配下,所谓的快乐就会变成痛苦,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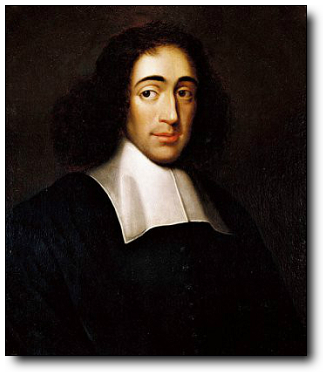 |
| 斯宾诺莎:“余缺”不影响知性的确定性 |
这是一种俗世中的目的论,而如果避开这些恶,或者将恶转化成善,是不是就是一种幸福,是不是可以支配心灵?斯宾诺莎却说,恶转化成善,即使是一种善,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善,善同样可以变成恶,同样可以被否定,所以真正的善是持久的善,是没有可能性的善,也就是说,是必然的善,是唯一的善,是肯定的善,是永恒的善,而这种善,斯宾诺莎把它命名为“真善”、“至善”,“它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
善是知识,是唯一的知识,是永恒的知识,是“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的知识。斯宾诺莎认为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途径造成了不同的知识,一种是由传闻而得来的知识,一种是由“泛泛的经验”获得的知识,一种是从并不必然正确的推论推出的知识,在他看来,这三种知识因为不确定、偶然性和非本质性,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而他所设想的真正的知识是“纯从认识到一件事物的本质,或者纯从认识到它的最近因而得来的知识。”只有它“才可直接认识一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于错误”,所以要获得这种知识,斯宾诺莎认为要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去行动,否定就是要去除不正确的方法,所谓“医治知性”就是要区别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虚构和错误的知识,然后才能用肯定的方式“纯化知性”,从而“可以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这种认识事物本性的能力就是“知性”,知性是为哲学的目的论而准备的,在他看来,这种追求哲学目的地过程是这样的:人由于自己“天赋的力量”,可以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当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后,可以获得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用来制造更新、更全、更完善的理智作品,而新的理智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新的工具又产生新的力量,“如此一步一步地进展,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在这个过程链条里,其起点是人的天赋力量,终点则是智慧,天赋力量是“指非由外因所支配的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天赋力量是自我本性的一部分,也就是有这种来自本性的力量,才会有产生“真观念”的知性,才会在工具的制造、力量的产生中一步步前行,最终走向“我爱智慧”的哲学终点。
所以很明确,要确定一种真正的知性,就必须界定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在真观念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对象的东西,这两种观念指向两种本质,一种是形式本质,一种是客观本质,观念可以拥有他的本质,但是也可以拥有它的对象,而真观念只是真理的确定性符号,也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指向本质的观念,“要达到真理的确定性,除了我们具有真观念外,更无须别的标记。”只有在这个真观念之下,才能找到抵达心灵的方法,才能在“最完善的方法”中达到至善。
这是一种肯定式的认识,“所以真的方法不在于寻求真理的标记于真观念既已获得之后,而真的方法乃是教人依适当次序去寻求真理本身、事物的客观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的一种途径。”而在肯定的过程中,一定要相辅相成一种否定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在于认识什么是真观念,将真观念从其余的表象中区别出来,又在于研究真观念的性质使人知道自己的知性的力量,从而指导心灵,使依一定的规范来认识一切必须认识的东西,并且在于建立一些规则以作求知的补助,以免枉费心思于无益的东西。”不管是否定和肯定,在论述完哲学的目的这个目的论之后,斯宾诺莎就站在了方法论的上面,他指出要达到目的,必须用正确的手段来认识,要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本性”;要正确推究出事物相异、相同和相反的地方;要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事物做得到的,什么是事物做不到的。”要将对事物本性的知识和人的本性与能力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从事物到人,才能达到最高的完善。
否定就是去除表象的迷惑,就是医治,就是纯化,“真观念与别的表象加以区别或分开,保持心灵使不致将错误的、虚构的、和可疑的观念与真观念混淆起来。”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灵不受真观念控制,就是因为我们虚构了一些事物,“虚构”当然是远离本质,远离真理,他给虚构的定义是:“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事物还有不知道的原因,我们才会使它成为可能的事物,才会用一种虚构的方式认识他,所以从本质上说,虚构不涉及永恒的真理,它只是在头脑中或想象中把记忆中的东西回想起来,然后当成是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所以虚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就会产生错误的知识。
“凡涉及存在的错误观念,可用与改正虚构观念相同的方法去加以改正。”对错误观念的否定,就是对虚构的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意义不仅仅是远离错误,而是要确定一物的存在并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要在本质意义上成为一个“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需要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真观念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它能表示一物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或产生;它的客观效果在心灵中,与其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
那么,如何获得寻求纯粹出于心灵的真观念,如何单纯从事物的本质去认识它?斯宾诺莎提出了“界说论”:“所以研究的正当途径即在于依一定的界说而形成思想。对于一物的界说愈好,则思想的进展愈容易有成果。”界说的方式和步骤当然也是方法论的,它的建立基础则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则是必然性,“一个界说要可以称为完善,必须解释一物的最内在的本质(essentia),而且必须注意,不要拿一物的某种特质(propria)去代替那物的本身。”内在的本质不是某种特质,他举例说,圆形的界说可以说成是“一个由中心到周边所作的一切直线都是等长的图形”,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圆形的一个特质,而非本质,本质的圆形应该是“任何一根一端固定的另一端转动的直线所作成的图形”。圆形是被创造之物,他认为被创造之物的界说必须包含的是“最近因”,最近因就是只有唯一原因而产生的特定结果,也就是说,后一个事实的发生,必须要基于前一个事实,若无前事实,则无后事实,则没有最近因果关系。
最近因具有的是创造的唯一性,而对于非创造之物,斯宾诺莎认为它的界说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是排除任何原因的,也就是说,非创造之物是独立存在的;它既然已经存在,就不会再有不存在的疑问;而对于心灵来说,“界说必不可包含可以转变成虚字的实字”,也就是说,不可用抽象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特质都能够“从它的界说推出”。如果心灵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去考察产生的思想,并能够依照次序推出结论,那么由于它是确定的、唯一的、本质的,所以自然而然不会有错误的思想。
否定是为了肯定,肯定是为了至善,在这样一种正反方法论之后,斯宾诺莎就指出了知性的特质:
一、知性自身具有确定性,换言之,它知道事物形式地存在于实在界中,正如事物客观地包含在知性中。
二、知性认识许多东西或绝对地构成某些观念,而又从别的观念以形成另外一些观念,譬如,知性无需别的观念即绝对地形成量的观念;反之,知性形成运动的观念时,必须先思考到量的观念。
三、知性绝对地形成的观念表示无限性;而有限的观念则是知性从别的东西推论出来的。
四、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
五、知性观察事物并不怎样从时间的观点,而是在某种限度内从永恒的和无限数量的观点。
六、我们所形成的明晰清楚的观念,好象只是从我们本性的必然性里推出来似的,所以这些观念,似乎只是绝对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混淆的观念,则恰好与此相反;混淆的观念的形成,每每违反我们的意志。
七、知性从别的观念所形成的事物的观念,可以在许多方式下为心灵所规定。
八、那些愈能表示一物的完善性的观念就愈为完善。
知性具有确定性、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本质性和完善性,去除了传闻、泛泛的经验、感觉来推断出的知识,去除了错误和虚构的观念,在“知性改进”中,凭借着求知的天赋工具,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达到至善的哲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