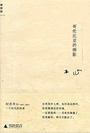 |
编号:E29·2161030·1339 |
| 作者:木心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原价25.00元现价15.00元 | |
| ISBN:9787563358243 | |
| 页数:192页 |
“本篇原定九章,既就六,尚欠三。此三者为‘黑眚乾坤’、‘全盘西化之梦’、‘论海派’——写完第六章,因故搁笔数日,就此兴意阑珊,再回头,懒从中来,只好这样不了了之了。”木心在《后记》中说,留下的“无尾之尾”或者也是木心的一种态度。作家陈丹青这样评价木心: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惟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哥伦比亚的倒影》是一本散文集,全书分为上、下辑。上辑收入了《九月初九》、《童年随之而去》、《竹秀》、《论美貌》、《同车人的啜泣》、《带根的流浪人》、《明天不散步了》等共十二篇作品,下辑是《上海赋》。
《哥伦比亚的倒影》:故见其一去不复返
所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乐了,为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忧了,试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大有人在,怎能不跫然心喜呢,就怕“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后下去,诚不知后之览者将如何有感于斯文——
——《九月初九》
忧而乐的不是天下,乐儿忧的也不在现在,在“一直后下去”之前,其实还是有着“跫然心喜”的快乐。听说木心在前,阅读木心在后,那些文本是《我纷纷的情欲》,是《诗经演》,是《伪所罗门书》,都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之后,而1986年刊印在“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上的文本仿佛真如“倒影”一般,在“转过身来,分开双腿,然后弯腰低头眺望河水”中被看见。
已经写进九品书库编号里的数字是2016年10月,这是一个和秋天有关的时间,而地点则在树叶泛黄的西湖边,浙江图书馆大门右侧接近小径的假日书市里,看见了那一册也同样泛黄了封面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外面的塑膜是泛着光的,像极了被命名的“倒影”——没有被拆封、被翻开、被阅读的新书,为何会出现在专卖各种旧书古书的假日书市上?想来也是销售专辟的一个渠道吧,那别于旧书古书的摊位上卖的全都是簇簇新的名著,而且打折力度超过一直网上购买、优惠不断的亚马逊。
这倒是一个异数的存在现象,索性将那些曾被时间湮没、留下太多陌生指纹和印章的古旧书抛掷一旁,专心挑选没有被拆封、被翻开、被阅读的新书。或者这样的一种购书行为也变成了忧而乐、乐儿忧的叙事,2016年10月的“此时此地”完全和1986年的专题讨论会无关,和之后被不断被熟知的木心名字无关,也和那些故纸堆里的古旧图书无关,泛着光的倒影里,无非是对于一本价廉物美图书的“跫然心喜”。
可是这“此时此地”的叙事也并非是关于时间的一种单一心情,当2017年8月的夏季和浙江图书馆右侧接近小径的地方成为新的“此时此地”的时候,泛黄的落叶不见了,泛着光的倒影不见了,连叫喊着的古旧书摊也不见了,那一纸上的告示是:假日书市已经关闭,如开放将另行通知。开放而关闭,关闭而开放,仿佛就如那“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乐”的反转,如“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忧”的变化一样,“诚不知后之览者将如何有感于斯文”。
斯文已在,那时站在炙热而空旷的地方,感觉到开放而关闭、关闭而开放实在是一个充满了无奈的地方,它仿佛隔绝了时间和空间,隔绝了过去和将来,隔绝了忧和乐,就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所在,前面的都已散去,后面的还未来到,不是闯入者,也不是奇遇者,生生地在“此时此地”的寂寥和茫然中。那情形在之后拆掉了塑膜,翻过了封面,读到了“哥伦比亚的倒影”的时候,才发现早就被木心的那句“不知如何是好”说到了。
“‘不知如何是好’是想知道如何才是好”,不知如何是好,最多也只是一次迷航,那也算作是没看见倒影时的迷失而已,迷失的意义在于寻找,在于知道如何才好——那假日书市是应该在的,古旧图书和簇新的图书也应该在的,即使不在,也会在别处依然存在。这便是一种不离的希望,可是“不知如何之好”终究是浅层次的无奈,更不安的是不慌不忙中的“目标之忘却方向之放弃”,是“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的结果是整个儿蒙住了”,是“‘他人’与‘自我’俱灭,‘过去’和‘未来’在观念上死去”的“管它呢”,再没有“恭恭敬敬地希望,正正堂堂地绝望,骄傲与谦逊都从骨髓中来,感恩和复仇皆不惜以死赴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悲哀?也像我一样只需要一册泛着光的书,知识的幽谷也罢,学术的地层宫殿也罢,什么名称,谁著作的也在其次,只是为了摆脱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迷航,但是这一册书,木心说的却是为了驳倒一个“不妙的,不景气的”论点:“还是二十世纪有味”。那是在怨怼自身所隶属的世纪,啜饮经历史蒸馏的酒而发出的叹言,可是那一本书又在何处?是旧货摊上富兰克林的靴子上印着的“生活再过一遍”的感悟?是酩酊归舍的王尔德“思想产生在阴影里,太阳是嫉妒思想的”的观点?是德国的铁血先知斯宾格勒在《西方之衰落》里的哀叹?是培根“人的天性是愚昧多于智慧,而做作的表情则常能打动听者的心”的解释?是举起一个手指的赫胥黎“他们一无所知”的不屑?
似乎这书已经不单单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图书馆,一个上流社会,“人类全都曾经像严谨的演员对待完整的剧场那样对待生活(世界),田野里有牧歌,宫廷内有商籁体,教堂中有管风琴的弥天大乐,市井的阳台下有懦怯而热狂的小夜曲,玫瑰花和月光每每代言了许多说不出的话,”而当这一册册的书被翻开,它们其实根本没有被读完的可能,引号里的句子,其实不是句子,只有逗号没有句号的引用,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像是时间被延伸到一个无穷尽的地方,像是空间被拓展到无限远的所在。
整整20页的《哥伦比亚的倒影》,没有分段,没有停顿,当然也没有封闭和隔开,看上去是把他人和自我、把过去和未来放在一起,是为“不知如何是好”寻找一种如何才是好的答案,继续,继续,再继续,向后,向后,再向后,还是二十几有味?那句子其实通向了二十一世纪,通向了2016年10月,通向了2017年8月。在这继续向前不停顿的句子里,仿佛就没有了“便是一手刚作奉献另一手即取报酬的倥偬百年”的二十世纪,没有了自作多情的被风吹动而飘飞的纸袋空罐,没有了“薄的学士,滑亮的硕士,人造纤维的博士”……
其实,这或者是木心所找寻的方法,“前人的文化与生命同在,与生命相渗透的文化已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我们仅是得到了它们的倒影,如果我转过身来,分开双腿,然后弯腰低头眺望河水,水中的映象便俨然是正相了——这又何能持久,我总得直起身来,满脸赧颜羞色地接受这宿命的倒影,我也并非全然悲观,如果不满怀希望,那么满怀什么呢……”把省略号也当成停顿的符号,把影子当成是正相,把未来当成是“此时此刻”的现在,甚至把那些书当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本,何尝不是一种“如何才是好”的方向。
正相之前,转身之前,分腿之前,弯腰之前,那宿命的倒影一定是存在的;也或者在“此时此刻”之前,“十五十六世纪上流社会”一定存在的,“还是二十世纪有味”一定存在的;而在一本书之前,甚至富兰克林的靴子,王尔德的酩酊之醉,赫胥黎的手指也一定存在的。那简直就是一副“遗狂”的风情画:在波斯,女才说:“贵国的思想语言的锦毯,也应像羊毛丝麻的锦毯那样倾销到各国去;彼欺君者,可免一死,遣去作思想语言的锦毯商,以富溢荣耀波斯帝国。”在罗马,尼禄竟也是世界上最蹩脚的诗人,在希腊,荣光被瓜分在各国的博物馆中,“若论参宰罗马,弼政希腊,训王波斯,则遥远而富且贵,于我更似浮云。”而那一部华夏文化史里写就的壮举却都变成了憾事:“滔滔泛泛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
风情画之外的小奏鸣曲呢?“朔拿梯那”的声音何止是一种花开花落的叹息?丹麦的美人鱼被锯走了右臂,巴西的驴子在送给教皇时成了“圣驴”,菲律宾的新古典主义春药只是那吞食的臭虫,希腊只剩下“比枯萎的珠子更难看”的枯萎的花,维罗那的剧场里没有欲仙欲死欲死欲仙的歌剧,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听众。而那只存放在英国苏佛克郡的老箱子竟然和外婆房里的皮箱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工场同一批手工业师傅的制品,我还是认为这两只大皮箱是我外婆家的。”相同的命运?还是相似的倒影?湮没在时间深处,还有谁能够“转过身来,分开双腿,然后弯腰低头眺望河水”,在倒影中看见变异的正相?在四十余年不去外婆家的“此时此刻”听到后来的故事:“片瓦砾场,周围也有野草,听说后来营建了炼钢厂,后来,就没有听说什么了。”
风情画的华夏文化史,小奏鸣曲里的老中国皮箱,也许这才是站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看见的那一个倒影,倒影在水里,它的根是否还在?“弃而不顾?唯其欲顾无术,毅然弃之,弃,才能顾,他算是弃而后顾吧,他。”木心说到的“他”是昆德拉,或者说是如昆德拉一样“带跟的流浪人”,当头也不回地离开蝙蝠形的故土,当坦克的碾压下只有地球以上的祖国,当没有年龄的极权主义支配了有年龄的东西,“流亡作家”的命运大约只剩下“一块蝙蝠型的斑迹”,但至少不是脱根而去,不是枯死异邦,不是“萎瘪瘪地咳嗽着回来”,因为还存在一种带根的流浪人,“带根流浪人,精神世界的飘泊者,在航程中前前后后总有所遇合。一个地球仪也够了。”
带根的流浪者是看得见那个倒影的,倒影里是“上海赋”:从前的从前,是半殖民地的罗曼蒂克;巅峰的四年“孤岛”,是炮火中糜烂颓唐烟云过眼;弄堂里的风光,是在“格算,不格算”中耗尽毕生聪明才智;亭子间姘居的窗格里,终究是看到双翼飞机飞向那一个战场的影子;而“只认衣衫不认人”的面子里,是“自己嫁不出去或所嫁非人,还得去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权术……当“既就六,尚欠三”的上海赋终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搁笔的时候,那无法完成的“九章”似乎也成了不完整的影子,这是不带根的上海?这是反讽的赋?“但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故在诱胁之下,嗒然面颜尽失,再回头,历史契机骏骏而过。”
九章之缺失,也是一个蝙蝠型地球仪的隐喻,就如在“九月初九”中的那个“自然”,早就在宠幸中,在吟咏中,在抒情中,成为人化的自然,成了催眠的自然,成了粉饰的自然,最终也成了“自然赋”:在儒家那里是一套君王术,在致格学派那里架空到实用主义中去,在释家那里成了诸般道具,道家近乎自然,却也在那个括号里反讽为一种艺术家的摆设,“一夕之后,走了。”走了的倒影里还有什么自然,还有什么根,还有什么哀伤和绝望,还有什么“不知如何是好”的迷航:“异邦的春风旁若无人地吹,芳草漫不经心地绿,猎犬未知何故地吠,枫叶大事挥霍地红,煎鱼的油一片汪洋,邻家的婴啼似同隔世,月饼的馅儿是百科全书派……就是不符,不符心坎里的古华夏今中国的观念、概念、私心杂念……愁,去国之离忧,是这样悄然中来、氤氲不散。”
“一夕之后,走了”的自然,“再会吧,再会吧”的从前的上海人,“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程度”的竹秀,还有那一只脱手而去的盌,“我的一生中,确实多的是这种事,比越窑的盌,珍贵百倍千倍万倍的物和人,都已一一脱手而去,有的甚至是碎了的。那时,那浮氽的盌,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走了,再会了,去了,即使敌不过“还是二十世纪有味”的遗憾,也终究要俯身,把那倒影颠倒过来,“如果不满怀希望,那么满怀什么呢……”或者,2017年8月消失的假日书市也是一个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