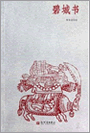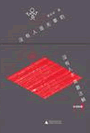 |
编号:C28·2140309·1063 |
| 作者:梦亦非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49543854 | |
| 页数:348页 |
还是那个叫碧城的小县城,还是鬼师和巫术,还是逃离和梦境,只不过比起《碧城书》,这次梦亦非在文本上的实验更为彻底。1本书=6本书:你读到的不只是一本小说,而是四部(或两部)小说加一部散文、一部政治哲学:现实主义小说、爱情小说、匪帮小说、奇幻小说、政治小说;包括几种文体:小说、散文、评论、民间传说等,每一章的第一部分为叙事部分,第二部分为细节性与解释性的散文部分,第三部分为评论部分,但以评论的方式呈现一部小说,本书实质上为四部(或两部)小说加一部散文、一部政治哲学,每一节标题连起来又是另一篇微小说,本书中暗藏无数结构上的机巧;没有任何一句比喻,没有任何一个形容词;颠覆性的阅读体验:或者是从文本的第一行开始阅读,读到最后一行结束,或者是将每一章的第一部分连接起来阅读,不要触及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如此等等,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间碧城的那段隐秘历史肢解开来。
《没有人是无辜的》:人人都是于同志
死亡是不可能的吗
他在街上行走时
变成—株树,立在街角
开花、结果、枯朽
三十年后又变成活人
拍拍身上的风尘
继续往家中走……
他找到的却是一片郊野,
树木与石头在说话,但是
他听不见,那是否
死去的人,灵魂并没有
消失。他在一池水边停下
看水中自己,仍然是
变成树木之前的模样
但城市已经改变,漂浮,
在水面,命运在水中
流转,永远在一个点上
消失者会再次出现,它们
互为实物与倒影……
他坐在窗台倒影上
天黑下来之前,他
变回童年模样,一株树
倒在地上,听到水声响起
——目录
是索引的目录,它跳跃在页码之间,像布满分岔的小径,而当那些数字被拆除,它也是一首二十三行的诗歌,一株二十三个枝节缠绕的树,一首诗开始的死亡,一首诗结束的死亡,不可能的死亡,水声响起的死亡。但是当“凶手是谁或者谁和谁或者谁谁谁谁”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倒影,一个在水中的倒影,在窗台上的倒影,以及写在扉页上的倒影。
是在目录之前,在一首诗歌展现之前,“小说作为世界的虚像”的题赠分明打开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连同没有见过面的“梦亦非”的签名,都是虚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2014”的标记分明要把我拉向一个已知的时间段落,它是现在,它也是过去,一个时间映照着过去的倒影,一个时间也折射着未来的倒影。过去是两年前,梦亦非出现在那本叫《碧城书》的小说中,我看见一个穿过水和火的梦:“梦成为了‘吞噬自己的蛇’,在那里变成梦中之梦,在时间的循环中,在空间的重复中,抵达终结。”书页是一个集合,梦也是一个集合,可是在两年之后,那团不见灰烬的火又开始在书页里燃烧,就像那枚废弃的铁钉,小心而准确地刺穿了一个人的脚掌,穿进“2014”的世界虚像里。
“这是解放初期,略铎与妹妹花散在碧城绒外的泥塘里摸螺蛳,被一枚生锈的铁钉扎透脚背而陷入昏迷”,如果这是一种文本的暗语,那么《碧城书》一定是那个有关死亡诗歌里的倒影,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就已经变成了一株立在街角的树,一株开花、结果、枯朽的书,一株三十年后又变成活人的树。当活着的时间变成死亡虚像的一个确定的存在,是不是只有那水声才是真实的?它荡漾在时间里,荡漾在《碧城书》和《没有人是无辜》的文本里,荡漾在2014年签名的梦亦非和鬼神的儿子梦亦非中,所以,当时间以一株树的样子倒在地上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了一个轮回:“死去作为终结,人之所以害怕死是因为害怕终结,尤其是时间的突然终结。但我看见,死去只是一种说法而死去的形态却不同,只有死亡的人才能看见别的死亡。”
老鬼师看见了死亡,在他眼里,“碧城只有几个人,剩下的都是禽兽与草木。”就像那一株树;我看见了死亡,看见李奇飞的死亡,“却看不清李奇飞是否即李其飞”,当然,我也看见了鬼师的死亡,“他的死在黑色之中不可辨认出轮廓”,看见了吴定景的死亡,“他竟然死在我之后而不是在剿匪战争中”,看见了胡云翼的死亡,在“文革”武斗中“我命令手下的红卫兵们将他打死在西大街一条巷口”,也看见了土匪王朝相的死,“在河沙坝上我一枪射穿了他的咽喉。”看见的死亡,虚构的死亡,却也是自我的死亡,“死是以死为原点的画面的旋转”,那么在没有终结,在被死亡的人看见的死亡面前,凶手是谁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也必定是看见了自己的死亡。“这一刻我睁着眼睛却看不清人影晃动,是一个人还是半群人或者一群人谋害了我?”脑后体液流溢而出,那一群人出现在我面前,是反动分子李奇飞,还是地方领袖王朝相,是为我用鬼净身的鬼师,还是攻打碧城失败的吴定景,是那个下午参观了冰块的卡朗,还是造反的韦绍基,或者是散发黄瓜气味的卫红?人影晃动,他们也都是世界的虚像,都是在时间的倒影里听到水声响起,而我在没有死之前,所做的事情不是看见死亡,而是让他们以“命运在水中流转”的方式烫金坟墓,躺进不能修改档案的历史中,“尽力不给被打倒的人站起来的机会”,就像一株树,在变回童年模样之前,永远倒在了地上。
“标语将时间的过去未来与此刻搅在一起让城市变成时间迷宫。”在时间里,城市变成迷宫,那么出现在《碧城书》的那个名叫碧城的迷宫又在哪里?在吴定景的攻打计划里?没有投诚,意味着在一种命运下摧毁一种存在,“卡在碧城的有与无之间”,对于吴定景来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确定碧城的存在,而那一次计划中的反攻像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语,它可能记录在于同志在《接管碧城与敌斗争》中,记录在碧城县委书记杨勤修的《接管碧城和剿匪噩战斗的回忆》里,也可能在军大五分校的陈将雪的《碧城激战》中,但是这样一些纪实的回忆录,对于吴定景来说却像是没有发生过的故事,或者他就在被看见的对面想象自己亲历的一场战争,然后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体内的另一个人。而对于我来说,碧城却是不断镇压不断修改不断打倒的统治中,在“真真假假种种拆除城墙的例子”里,反攻碧城和统治碧城组成了两套话语体系,一方面是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仪式里,另一面却是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时间记忆中,它们是有和无,它们是存在和覆灭,它们是各自人群里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卡朗来说,碧城却是一次书写,“我记录的是碧城,如果我不记录,碧城就不存在。”而被记录的碧城在一种无法解读的睢语里,就像迷宫,在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下午,变成了无法逃脱的咒语。
在记录与虚构,在反攻与统治,甚至在制造和消解过程中,碧城只留下了具体的味道,它是“解放军睁开眼时碧城是糙米饭既甜又霉的味道”,是“政府官员被阳光晒醒时碧城是猪肉与牛肉的味道”,是“码头挑夫午梦醒时碧城是酸汤菜的味道”,当然,也是为红身上散发的那种充满诱惑的黄瓜味,“这些味道组成碧城的城墙房屋与街道,组成碧城的楼梯下水道与阳台,组成碧城的时间回忆与对碧城的描述。”味道里的碧城只不过是一种与梦境有关的虚像,它也一样无法抵达真实,甚至是一种隔离。而这种隔离其实是那无处不在的缝隙,“缝隙构成碧城有一个人在碧城行走他不是行走在碧城而行走在缝隙里,街道是缝隙一条主街一条横街加一些巷子将碧城切割为碎片”,缝隙容纳着风,容纳着雨,容纳着梦,容纳着词语,只有捉影人才能发现缝隙里的秘密,“水面上的城市,人们千百年来都叫它做碧城,水面下的城市,也叫碧城,人们认为水面上的城市是岸上城市的倒影,所以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座。”也是倒影,一个是存在了数百年的城市,一个是悬在半空的城市,一个是本地人生活的城市,一个是外地人想要逃离却永远无法走出的城市,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他们,不同的梦境,把一个迷宫变成了时间记忆之外的倒影,但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看不见自己的倒影,就像于同志作为一个汉人,无法读懂那些睢文化,无法读懂他们的幻想,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树立一个敌人,在战争中重构自己的碧城:“我恨碧城是因为我恨碧城的文化是因为我将它们当作敌人,我未接受过这里的异族文化它们让我作呕它们与数学相比简直不配存在,在碧城中我一直保持着北方的生活习惯虽然因为恐惧死亡而离开北方”,甚至包括对女人的占有:“我恨这个民族所以潜意识里想占有它的女人们想弄它的女人们”。
但是这样的爱与恨对于碧城来说,一定是无法逃避的错误,是引向死亡的宿命,如梦幻一样的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攻城的子弹只是射在那词语里,射在找不到记录的时间里,而我看见的碧城没有灯火,我遇到的女人也不存在,“我现在看到在我的一生中并未有过线花也并未有过卫红,我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首长的女儿在离婚之后我独身到现在”,这是颠覆的开始,错误,不可避免的错误,引火上身的错误,让碧城仅仅成为了一个梦的仪式,一个死亡的仪式。
“碧城甚至也不叫碧城它的名字叫三合镇解放军进城之前它叫三脚屯”,水面之上的碧城,水面以下的碧城,本地人存在的碧城,外地人要离开的碧城,甚至计划中攻打的碧城,革命中被镇压的碧城,都变成了书写中一个幻影,而我呢,那个于同志的人呢,“材料显示,在碧城三十年来的公安局长与革委会主任中,从未有过姓于者,一个也没有”。没有碧城,没有于同志,那么时间呢?那个创造了迷宫的三十年呢?它或者是掀起全民整风运动李其飞自杀的一九五八年一月,或者是以反革命潜逃的罪名判处李家鬼师死刑的一九六六年九月,或者是成立碧城睢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时我是革委主任的一九六七年三月,而最重要的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呢,这个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叛军们对碧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的战斗,最终被击溃,而碧城政权得以延续,但是这场被称为镇压的战斗在王朝阳那里,却是一个通过法术把画像变成真人的虚拟战争。
没有战争,没有碧城,当时间把城市搅和成一个迷宫的时候,我作为于同志的三十年也在这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我明白了,五十岁也是二十岁,二十岁也是五十岁没有区别水波的扩散与回溯没有区别,二十岁的眺望,五十岁的回忆,没有区别因为本来就没有二十岁与五十岁”,在时间荡漾中,在万物交互中,我看见了二十岁的革命,看见了五十岁的回忆,而一切都只不过是找到了那个和死亡有关的倒影,那个自己看见自己死亡的倒影,“我明白,当时间在人弥留之际,荡来漾去,我也就是她,她也就是我,我整死那些人,原来也是整死我自己。”我的死是大家的死,大家的死也是我的死,三十年不是一个有着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段,不是从生到死的直线,也不是被记录在文本里的和“一加一等于二”有关的数学题,所以于同志出的那道题只能是一个无解的寓言:“一座城市,只住了480个人而1/3男人,女人中,1/6是瞎子,睢人中3/4是聋子,聋子加男人数,等于死人数,死人被烧成骨灾的数量比瞎子的数量少4/7,问题是,用这些骨灰,可以建造成多少座城市以决定城市中时间的多与少,并求出,时间与城市,在人性的公分上各自的比例是多少,可以用代数,可以用几何。”当时间和城市变成虚像,变成灰烬,变成文本的集合,卡朗在日记本封面上写下的《睢人三十年》这五个大字的时候,文本里的世界也变成了和数学有关的多义项:“数学有一个将世界从多重梳理为一重的功能,世界也一样,世界应该挑选一种方式而便于理解。”
当然,李其飞与李奇飞,是找不到证据的“不同”,欧阳复生是十个指头还是十一个指头也找不到证据,在睢人中,没有人取名叫略铎或者陆铎,当多重梳理为一重的时候,当城市、时间被历史叙事引向一个终点的时候,《睢人三十年》以另一种文本的方式在卡尔维诺的计划里生成,只是这一份“手稿没有完工”的写作计划,在卡尔维诺这个意大利人的眼中成为寻找历史裂缝的文本,是虚构改变了历史,还是历史把虚构变成了实有?“—个悖论是当我们试图在历史的乱线中走直线时它带来的却不是拯救而是奴役也许是因为直线是一种简化?”价值体系的简化,文本方式的简化,《睢人三十年》会不会就是一道引向无解的数学题?1/3的男人,1/6的瞎子,3/4的聋子,对于一个城市的族群来说,缺席的人注定在身体的戕害中找不到自身的意义,就像于同志,在卡尔维诺的世界里,他实际上就是一道数学题,一个文本,“卡尔维诺面对文本就有如面对一场有终点的革命。”所以,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在一条看似走向终点的直线中还会有暴发的可能,因为仇恨的种子“已种在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并且会遗传下去”。
人人都是于同志,人人都有三十年,人人都在自己死的时候看见死亡,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宿命,一个集合的文本的轮回,“于同志只是三十年间碧城的一个政治符号,符号不死,一个符号可以等于许多人,所以一个于同志也就是碧城所有人的政治状态与政治历史”,这样不死的符号就是不死的种子,“直到卡尔维诺逝世,也没有写完《睢人三十年》这部著作,于同志也并没有死”。没有死的符号,就像那场战争,在一个互害的时代里,在互文的文本里,“所有人敌对所有人”,所以没有人是无辜的,而人人都是于同志,也意味着人人都不是于同志。
当然,在互害互文的叙事里,《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成为一个误读的文本。标题与文本、负小说与故事、显文本与潜文本、干掉形容词、消除隐喻、消除集权、交互而产生的质换与置换、荡漾的时间和纷繁的空间,这一切都写在梦亦非《没有人不需要注解》的特别附赠里,文本解释文本,也是互害,在“人人都是于同志”的繁复世界里,我按照※*¤的三种体系成为一个注解者,没有绝望,也没有穷尽,在页码编织的分叉小径上,先是从一个有关碧城的历史叙事实验文本出发;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九阡酒、木匠、睢族人办酒、出嫁银饰、鬼师薅介、保寨树的文化仪式和砍树烧炭、大炼钢铁、红卫兵串联的政治仪式有关的的随笔集;再从最后一页回到有关地方异文化、经济管制的正面效应、身体监禁和语言监禁、语言改变世界、立场是语言的表演、权力改变历史、政治语境对思考的抹杀、被掩饰的我本人、语言作为世界的全部的文学思想录,从开始到结束,又从开始到结束,仿佛是J.M.库切《凶年纪事》里的那条“分割线”,生生划出那个被虚构的迷宫。其实按照梦亦非的“虚像”世界的构筑,这些文本还可以变成悬疑凶杀小说、英雄小说、家族小说、以及“请打电话13533207600告诉梦亦非”的通讯录,而这种故意划分出的文本分割线并非是一种割裂,而是对于简化、单选、单一、极权的历史进程的颠覆,对于“人人是施害者,人人又都是受害者”这种同一性下多元性的阐释。
一章的标题就是该章起始的那个词,散文部分中最后一个词或字是接下来一章的散文部分的起始之词,这是文本的粘连,这是文本的循环,只是当第30章的“走”对应于“李奇飞走着走着便迷途于从盘石到碧城的过程中”的起始句,明显是一个例外,或者是站在文本之外也站在文本迷宫里面的“梦亦非”的疏漏,但是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文本的寓言,在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中,是需要这样一个出口,像一个钩子,扣住那一座城市,那一个时间,那一种死亡,“历史走不出一条直线,历史不走直线”,所以历史是一个有着出口的环,在那条“吞噬自己的蛇”的梦里逃逸,从文本集合的世界里逃逸,是的,在“去见识冰山的那个下午”,我的的确确看到了《睢人三十年》之外的那个醒目的“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