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2 《碧城书》:梦中之梦是永无止境

所有人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存在,于是所有的火是同一个火的梦,以及想象。
如果没有想象,那梦是不是会陷入灰烬般的结局,只在那一堆的火里燃烧,看不见那些欲望,那些爱,那些身体和灵魂,以及战争造就的对手,它独自燃烧着,连死都只是一个想象的一部分。而跌入最后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梦,是梦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梦的开始,“它只是一种比喻”,当打开所有的入口,也就打开了所有的出口,在入口里呼吸,在出口里张望,横穿过那些水和火,而最后像蛇一样,梦成为了“吞噬自己的蛇”,在那里变成梦中之梦,在时间的循环中,在空间的重复中,抵达终结。“我不再害怕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作为一个亡魂,没有人再会死第二次……”一个240页的梦到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而等合上书的那一刻,熊熊的大火正在里面燃烧,甚至没有纸张会变成灰烬,它完好的保存着,封面、书名、以及封底,作者,出版,字数,和条形码压着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一些图景,没有想象,它便只在看不见的内页里沧桑、杀戮和死去。
书页只是一个集合,关于文字的集合,关于故事的集合,关于从光绪二十六年,春天的集合,那团在书页里独自燃烧却不见灰烬的火,就像那枚废弃的铁钉,它是破坏者的集合,只是那么小心而准确地刺穿了一个人的脚掌。右脚脚掌,作为叙述的一部分,铁钉可以还原成以下的一种:方形,尖锐,“似乎从未用过”,那么这枚铁钉解构了那些集合,仅仅一枚,而且从未用过,它是孤独的想象,和梦无关,和所有人无关,也和里面的那团火无关——十年了它只是在那里燃烧,而由此被“送人陌生命运”的略铎也便消灭了集合,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露出骨头的个体,一个被铁钉带向另外生活的个体,而这个个体甚至成为与一切想象无关,“铎只是一个音节,在睢语中有第一的意思,也有别的含混不清的意思。”他的名字成为最后一道咒语里的词:铎。独立的铎,是个体的复活,他甚至抛却了所有永无止境的梦,作为一种意义,他用自己的身体的伤痛完成了集体意义的解构。
在鬼师这个集合来看,略铎的“陌生命运”就是没有灵魂,“都江城最灵验的过阴花尼经过上天入地的脱魂追查,也找不出略铎得罪了哪些鬼魂。”他不在梦境之中,不在想象之内,也不在鬼师的秩序里,灵魂是一种梦的结构,而在集合的书页、梦境和文字里,略铎不被火燃烧着,在昏迷十年之后,终于恢复了话语:“略铎眼睛盯着天花板,他说,鱼掉进锅里了。”这是另一个梦境?这是另一种想象?还是这只是一种个体的叙事?从光绪二十六年春天被废弃的铁钉刺穿右掌到宣统二年开口说话,他的个体里有着时间的序列,有着历史的纪元,所有的叙述似乎都开始抛弃梦、想象和那团火,而变成一种存在于真实中的历史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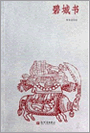 | 编号:C28·2120822·0907 |
所以,历史就需要解构需要篡改,甚至需要颠覆,需要从迷宫中走出来,而鬼师大院的存在,就是走向历史的反面,走向一个终点。没有对应物的历史是不是一定会变成想象?为了寻找最后的意义,就需要所有的对应物,在对应中获得意义,而所有关于存在,关于时间,关于灵魂,无非都是在缺席的状态下。略铎的失语一定是个标记,从此开始的寻找贯穿在整个家族的变迁中。比如都江城,“都江城却是历代朝廷通往南方的主要关隘,也成为南方那些嗜酒与血的睢族人对抗北方治者的必经之隘。”南方与北方,野蛮与更野蛮,在都江城的结合点上,有着天生的对抗,而这种地理意义上的对抗也为整个城市、整个时代的变迁找到了源头,民族和宗教,统治者和反抗者,他们一一对应在这个城市里,继而成为历史叙述的一部分。九阡城的铁匠潘新简在法术之下拉起了起义的大旗,打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军享太平”的口号,他是鬼师法术的膜拜者,也是牺牲者,那蛇一样的鬼师大院的土院墙,都是想象,都是轮回,“高达两丈的院墙无始无终有限无界:潘新简把它筑成了无数条循环地吞着尾巴的石头蛇,每一条蛇都存在吞前一条蛇的尾巴,而自己的尾巴又被后来的蛇吞着。”或者统治者就是反抗者,“起义者与压制者是手掌手背的关系,谁都一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战争中,所谓胜利者也最终只是失败者,知府李宗保没有用“火的欲望”烧掉鬼师大院,却在撤退行军中死于非命:“一个士兵走火的枪支打碎了他的睾丸,他在痛苦了一夜之后挥刀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从火回归火,由死降临死,这种循环像是那些被咬住的蛇,挣脱不了的宿命,这里没有非此即彼的规律,也没有所谓的正义和邪恶,而没有对应的世界就如一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咬着的蛇,没有终点没有起点,没有入口当然也没有出口。就像对应于历史的虚幻,对应于身体的则是灵魂,略铎只是一个例外,或者说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在集合外寻找一点个体的意义,而在更大的意义上,灵魂就是以非逻辑的方式存在,它糅合了梦、想象、隐喻,甚至它就长在照出对应物的镜子上,“镜子被避开的原因还有另一个:镜子暴露人们的魂魄。”镜子的存在,就是一种天生的对应,而与镜子具有相同意义的便是水,所以很明显,不管是有螺蛳的城外池塘,还是那条锅里的鱼生活过的都柳江,水之为水,是映照,是对称,是反射,是轮回。这水,是“潘新简在十六水的迷津中落入了蒙古特与欧阳静泊的手中”;这水,是我在寻找合作者的梦里出现的水;这水,也是便喜与四姨太躲在三脚屯关帝庙里的欲望之水……似梦非梦似雾非雾的迷离,是水的寓言,就像“平缓到我看见另一个都江城:以码头为对称线,另一个都江城在水里”。水上的城和水下的城,现实的城和想象的城,压抑的城和自由的城,就如“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但我们做梦时在另一座城市”,就是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对应,彼此成为镜中的虚幻之影。
而其实,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想象,不是对应的缺席,是身体的存在而应有的爱的迷离,张之藩的四姨太和便喜的偷情可以看做是欲望的发泄,是爱的一种归宿,但是这种爱并没有恒久的对应,关帝庙的所有释放其实是一种纵欲,或者说在伤害自己的身体,而那间“隐秘而废弃的厢房”完全成为了欲望罪孽的发泄地,到最后,他们的爱变成了一种害怕:“他们丧失了相爱的力量,也丧失了对其他异性的爱情”。爱的沉寂和毁灭,而便喜最后提出“想做鬼师”的要求,看起来是自我救赎,但是根本就不会有希望。而作为后代的其荡,更深地陷入了符号化的爱之中,他用银饰刻画的那个女人,像是梦的一次圆满,但其实那是轮回,那是报应,爱恨情仇最后变成了悲剧,“其荡失魂落魄地站在火堆旁,他最失败的事就是娶了自己所爱的那个人。”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无爱之中完成意义的命名,这种对应之爱一定只是一个符号,一种隐喻,甚至逐渐在这样迷离的世界里,逐渐丧失了人的本性,变成鬼师的救赎并不是真正的解救之道,而在象征的意义上,他们成了没有灵魂的动物,就如鬼师韦明德在梦里看见了自己的形象:“披着一身浓密的棕褐色兽毛,脚趾上长出尖利的爪子,双手的指甲像笋子一样拔出来,然后弯曲、变粗、变细,变得尖利,他就看见自己的手脚在一点点地变化,就连耳朵也变尖,有力地竖着……”
人的动物化,就是在告别灵魂的归宿,而梦中的“金黄的老虎”从博尔赫斯的世界里走出来,而成为都江城的一个新隐喻,“虎只食魂魄已变为畜生者”,或许这是一面真正走进都江城内部的真正入口,而那些变成动物的鬼师也在自己编织的梦里走不出来,“我们修建了一个把自己围起来的迷宫”。这是鬼师的使命,那迷宫就是梦,就是想象,看起来是在解构现实在逃离现实,实际上也是自我的封闭,三个迷宫的建造最后成为死亡的象征:“现在三个迷宫的中心都叠加到了一起,作为空间的水宫(月宫)、作为时间的水宫、作为象征意义上的玄宫,合而为一。”
所有的人都成为同一个人,所有的火都成为同一种火,是酒是炭是闪电,是历史是死亡是公正,不同的形态和意义,都是火的想象,在那里燃烧。而最后那些人呢,宗教有关信仰有关爱情有关,都变成了一种集合,对应之死,是无法再回到起点,也无法走到终点,在这个单一方向构筑的梦境里,必须有人醒来有人站在高处观望都江城。那团火在240页的故事里一直燃烧,而在合上那书的最后一刻,我发现有一个人从那书页里逃了出来,“梦亦非”写在封面之上,他曾作为都江城里著名的魔药师而走进书页的梦里,他在那里变幻着梦境,而他终于逃离出来,成为一个非文本的符号,或许就如书中早就定义的那样,“于是梦亦非来到了都江城,传闻里,他认为他遇到的那个对手正是他自己。”他对应在自己身上,他是自己的对手也是自己的叙述者,他是镜子是梦境,是想象是真实,是永无止境的蛇。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345]
思前: 被阉割的“芙蓉姐姐”
顾后: 那季节只剩下不说话的魔鬼(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