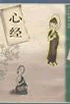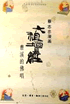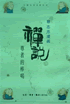|
编号:Y74·2120429·0881 |
| 作者:(台)蔡志忠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2009年1月 | |
| 定价:28.00元 | |
| ISBN:9787100064842 | |
| 页数:146页 |
从犬科时代到猫科时代,在蔡志忠看来,是团队合作向个人独立的转变,用这两动物来代表两个时代,或许是纯个人的理解,但是我们看到蔡志忠笔下的猫科时代的种种挑战和“未来社会的新丛林法则”:一切以个人的真正能力为优先,除非我们的能力能高人一等,否则不能确保一生能过得平顺。所以,蔡志忠的提出的“猫科宣言”说:“在数字时代里,一个人必须真正做到冷静、专注、精准、全力以赴,以及有效率地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英雄般的“猫”主宰着自己的未来,在书中的25个标签里,蔡志忠勾勒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猫未来”:“犬科动物与猫科动物最大的不同是:犬科动物依附群体,猫科依靠自己。”“多才多艺常会变成‘一无是处’!”“只有我们的能力成为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才会成为我们的资源。”“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失败却有一百万种借口!”,一个晴朗的早晨。”
《猫科宣言》:还是做自己最“妙”
一种状态仿佛就是凝固在那里,指向我,比如午睡之后的慵懒,比如在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时代的癫狂,比如自在者享受的孤独,但并不是要成全自己的转身,新的物种的到来和更换,仿佛那一只猫在天堂里和上帝相遇,却不要转世成人类的孩子,也不要是勇猛有力的老虎、比自己神气的狗,只要自己,只要如一个人的猫,“个人精英独领风骚”却已成为一个世纪的转身。
但唯独我不会叫“妙”,那一声清脆而暧昧的“妙”其实多少是在它自己的王国里告诉自己,离我们那么远,所以“妙!妙!妙!”才是“处世的万妙绝招”,“妙言妙语总是无往不利。”那么这一声的“妙”便脱离我的象征,脱离着午后的慵懒和数字时代的瘾病,以及更像寂寞的孤独,甚至还有看不见红色的视觉障碍。猫的复活,猫科时代的来临,原来也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梦境。
“梦具有一种荒诞的真实性,而真实有一种真实的荒诞性。”这是村上春树在《猫城》里的那句话,荒诞指出了与真实的距离,也指出了在现实中的合理性,作为寓言之一种,猫城是对人类的一次侵略,是一个荒诞的梦,所以在那里,人对于猫城的惊恐必须使他离开:“黄昏开始降临。很快就要到猫儿们来临的时刻了。他明白他丧失了自己。他终于醒悟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这里是他注定该消失的地方。并且,火车永远不会再在这个小站停车,把他带回原来的世界了。”
离不开是不是一种荒诞的梦?村上春树只是在人类和自己之外的世界寻找一种和解的方式,或许逃离也是其中之一,灵性的猫总是扮演人类的朋友,也总是缩聚在人类世界最恐怖的那里,闪着不可捉摸的眼神。与猫相比,狗确实和善得多,或者并没有那种荒诞的感觉,那种置人于恐怖地带的感觉,也从来没有使人要迅疾逃离——除非对人的身体构成威胁,但那也仅仅是有关身体的,没有触及心灵,也就没有进入那个荒诞的梦。
任性、我行我素,猫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象征,不是建立在人类的对面,而是成了人类的关照自我的一种折射,重新寻找物种的特性,是“去村上春树化”,或者说“去文学化”的一次实践了,那么很显然,也在脱离指向我的那种显示状态,这个过程其实在蔡志忠的书里变成了另一种启示录:《猫科宣言》,或者说是关于自我,关于适应,关于未来的职场宣言,完全没有象征和隐喻,没有猫城的恐怖,没有“摇滚的猫遇到了家居猫 带着它离开了那平凡的巢”的浪漫,也没有“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宣言。
从动物出发构筑一个物种的未来,关于猫,关于猫科,蔡志忠用一种轻松的漫画体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猫科时代,这种轻松来自于文字的生活哲理,来自于对猫科动物习性的熟稔,也来自于笔下简单线条勾勒与传神——红色和蓝色的两种猫科形象,以及左右三根胡须,夸张的粗壮尾巴,等等,这便是如蔡志忠一般的符号。符号之于符号,也完全契合着一种个性,想起签名的那些场景,蔡志忠从简单的名字还原为一个睿智的师者,对面,认真地在签名的书上画上有关的漫画,写上个性的签名。
不妨看作是蔡志忠传统一面的放大,签名这种仪式本身就是完全现实化的传统行为,一笔一划写在那里,可以触摸可以涂改当然也可以保留到很久远的未来——甚至纸张泛黄,那种记忆还在,这或许也就是在村上春树所谓的“荒诞的真实性”之外。这种传统做法恰好是和数字化的未来有些间隔,或者说也是和蔡志忠所建设和阐述的“猫科时代”的间隔。猫科时代就是新技术的21世纪,“是个人的时代,是创意的时代”,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网络,可以这样理解,网络实现了很多传统时代不能做的事情,因为“用很少的钱,便能完成自己的梦想。”同时,“也能通过互联网,将自己的创意扩展到广大的区域。”所以,在那些数字化生存中,猫科时代只是一种标签而已,而以数字化的网络为工具,脱离于团队合作的传统,脱离于真实现实而架构成的虚拟技术时代,完全是一种技术的制胜法则,或者说,是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成全了猫科时代,成全了个人主义建立功勋,而21世纪将群体分散开来完成自己的理想,其实就是建立一种技术时代的切割模式,借此走向“冷静、专注、请准、全力以赴以及有效率地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的猫科时代。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时间刻度在21世纪的猫科时代,是蔡志忠强调个人至上的时代,也是技术主宰的时代,所以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假命题,个人至上并不一定需要技术的切割和支撑,或者说,个人和创意的猫科时代是一种“我扮演自己,走自己的路”以及“做自己最乐意也最拿手的事”的本性回归,而并不一定需要数字化作为技术支撑,或者说,从他个性般的签名这一行为也可以推翻猫科的技术寓言。作为一个文化精英,与出版合作的团队性仍是关于蔡志忠的一个文化符号。
那么,既然猫科时代是一种构想着的技术时代,那么必定要建立一个参照物,那就是传统的20世纪,这就是“犬科时代”,所以在蔡志忠的构筑中,猫科时代完全将犬科作为对应,犬科时代是团队通力合作的时代,而猫科时代则是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犬科动物在叫是因为别人也在叫,猫科动物在叫是因为有话要说;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最大的不同点是:犬科动物依附群体,猫科依靠自己;做一只猫,无论物质条件多么匮乏,活得依然自由自在,当一只狗,无论生活得多么富裕,永远都活得很卑微;犬科动物的神情总是呆呆地等待着上级领导,猫科动物的神情总是紧紧咬住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如此等等,而在突出猫科的个性代表着未来方向的同时,必须要把犬科踩在脚下,似乎所有曾经的传统都有着致命的弱点,这种非此即彼的说理方式当然略显单一,甚至有一种为说理而说理的形式主义,虽然在“天堂之旅”中,好猫对于上帝所提供的不同转世物种进行了对比,也涵盖了人类、老虎和狗,突破了单一性,但是在之后所有需要建立的论证中,都将犬科时代作为一个远去而且必须抛弃的时代而加以否定和鞭策。
那么,蔡志忠所要建立的猫科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然是美丽、不凡、慈悲,以及不顾一切的自我。“要想成为猫科物种的方法有很多,首先要戒除无谓的犬叫。”也就是要去除陈旧的东西,革新成完全不一样的自我,从这里出发才可以不受以前时代的影响。当全新开始的时候,猫科就成为一种完全自我驾驭的超人,“天堂地狱皆因为自己!: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能乐在其中……就算置身地狱也会化为天堂。被迫从事自己没有能力胜任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算置身天堂,也会化为地狱。”而所谓和领导之间取得的“双赢策略”也就是:“如果你置身于地狱而无法逃离,那么就尽心尽力帮助撒旦,使他升到天堂。”猫科宣言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包含着膨胀的自我欲望和不可一世的超人理念,无论地狱还是天堂,无论失败还是成功,都可以驾驭,都可以实现。尽管,在蔡志忠所阐述的猫科时代的特征中,也还有谦卑,还有慈悲,还有自我的正确定位,但是过分强调的自我倒是使这样的猫科时代充满了虚无主义,高于理想主义而实际上多少成为了一种口号,“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肯当自己,那么,要请谁来当你?”这种自我主义看起来是贴近个性的张扬,肯定自己,但是却往往陷入鄙视对手的尴尬境地,“只有我们的能力可以成为别人的资源,别人的资源才会成为我们的资源。”这种利用也无非是为了自己更为成功,“以自己的‘无’去钓他人的‘有’,光用尾巴钓鱼,很难获得成功。”所有的行为和理想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个性疯狂渴望的成功,“想要达成不平凡的成就之前,是使自己跃升为超凡之人。”这种畸形的“成功学”实际上的一种权谋术和厚黑学:“我们乐于与愚者共事,是因为潜意识里自知能力不行。我们无惧与智者共事,是能力很行的证明。”
“将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猫科时代的“猫科宣言”,极致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这便是个体上的制高点,便是自我的全部意义,“要当猫科时代的最佳动物”,而21世纪早就来了,那些猫在数字时代里不停地叫着,是“妙!妙!妙!”,是处世的万妙绝招,妙言妙语的背后是无往不利,也是真实的荒诞,不如像村上春树的那个青年一般的醒悟:“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这里是他注定该消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