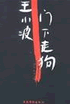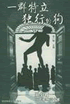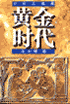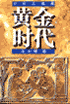 |
编号:C28·2040130·0691 |
| 作者:王小波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
| 定价:7.00元 |
| 页数:375页 |
王小波在1982年开始写作、经历十年,《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里,那个叫“王二”的人是一个青年的象征,总是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中,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他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王二是一个活得下去的无知者,“我记得那些日子里……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王二明白:“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王小波以梦为马,自由驰骋在男人与女人的梦中。《黄金时代》呈现了种种观点差别。
《黄金时代》: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革命时期的爱情》
不动声色地开始阅读,读到一个地方,便感觉不对,好像早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625页的《青铜时代》,里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都似曾相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确定:我的确已经读过了,而且认认真真地读过了。读过是一种过去时,发生了的过去时,为什么在现在时的阅读状态里,会形成一种暂时性遗忘?是记忆会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把《青铜时代》当成未读书目的时候,却把《黄金时代》标记了未读。遗忘之后是找回记忆,找回记忆之后是重新调整,把《青铜时代》放进了书柜,开始阅读《黄金时代》——过去时还留在过去的记忆中,现在时一定要进入现在的状态。
小小的插曲,从过去调整到现在时态,一切看起来变得正常,疑惑的是,“时代三部曲”为什么会首先看《青铜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最后才是《黄金时代》?是不是一种逆反?三个时代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序列,是作为读者自我的设定罢了,而当从遗忘中把时间纠正了过来,仿佛一部小说真正开始了叙述,但是叙述在无形之中,像时间一样不动声色地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第一人称是“我”:“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或者,“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也或者,“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既不是画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做豆的工人,而是一个工程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前几年,甚至“已经四十岁”,都是把“我”置于现在的状态中,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之于我,才不会越过边界,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
但是,小说第一句却一下子把世界拉向了一种客观的存在,“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甚至到了1993年夏天,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时间里,那个四十二岁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的人还是叫王二。王二是王二,不是王一,也不是王三,所以在王二被命名开始进入叙事展开情节的时候,王二是一个人,他活着的意义和其他第三人称的人一样,是被叙述的,但是在还没有真正展开情节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干涉了王二的存在方式:“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王二是王二,王二不是王二,因为很多人都叫做王二,而作者在不是王二的时候,没有插过队,身材结实,毛发很重——作者是作者,而作者就是“我”?
把王二称作是同名兄弟,其实是“王二们”的存在,当然不是作者,也不是我,但是那个叫王小波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同名兄弟都叫做“王二”,有时也把自己叫做王二?《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第一句是:“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似水流年”的第一句是“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在“三十而立”里,第一句是“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一方面把王二从作者的世界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把我叫做王二,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在我和他之间,叙事的主体和角度发生了改变,过去和现在交汇在一起,很多人和一个人混杂在一起,于是,在符号的解构和建构中,小说进入到了关于虚拟和真实的世界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小时候我跑到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天空”,当胳膊被划破,比必须要“我”出场,“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的成分,而我臂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一条疤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因为一条疤代表着疼痛,代表着伤害,代表着真切的感受,“讲到了划破了胳臂,虚拟就结束了。”
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王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都在一种被叙述的层面上,都具有同名兄弟的虚拟性,也都没有那条疤的真切感受,只有返回到第一人称,才是真实的,才是现在时的,才是面对自己的,所以在虚拟结束之后,我才进入到真实世界,正是因为虚拟和真实之间存在的隔阂关系,王小波才会在这样的文本叙述中才能找到一种混杂的并置,“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在隔阂和并置中,才会有一种脱离而进入、客观而主观、规范而叛逆、无性而有性、阴和阳的体验刺激,才会在牵强附会、最不可信以及处处受阻中拥有性爱的快感,“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就像“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三人称的牺牲品和第一人称的体验者,在分离和交融中,在取消主体和恢复主体中“自发地做一件事”。
革命时期里有作为厂长的老鲁,有“帮教”者的X海鹰,有帮助会,有强化治安运动,它们构成了第三人称“王二”的存在维度,“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的就会成了牺牲品。”革命时期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王二,他们都是“王二们”,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已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看起来是某种逃避,但是在从第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时,我想要的安宁变成了另一种革命:我会用父亲五八年的宣传材料擦屁股,我会在X海鹰对我进行教育时磨屁股,我会在作画、写程序中成为一个诗人,我会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创造的句式,“我喜欢的是他创造的句式,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简直妙到极处。仿此我们有:革命时期的发明,革命时期的爱情,等等。”从第三人称的王二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的过程中,最真切地体验是,“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
吊在树上,亲吻之后是爱抚,爱抚之后是强奸,这是爱情还是暴力?或者说,当爱情变成爱欲,当爱欲变成性欲,当性欲变成暴力,“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完全变成了“爱情意义上的革命”,革命的政治性、思想性、运动性完全被解构了,它在一种反政治、反思想和反运动中变成了另一种暴力,而对于我来说,“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货真价实才是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从革命到暴力的转变,从虚拟到真切的改写,既是对所谓革命的一种悖逆,也是对革命的顺从,而这便成为了奇异的辩证法,“有一句古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革命时期,就是X海鹰治人,王二治于人。X海鹰中正彩,王二中负彩。她能弄懂革命不革命,还能弄懂唯物辩证法,而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不是虚构,因为站在X海鹰面前的只有一个我,不是想像,因为在这种对革命的消解和悖逆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行动,甚至用最极端的死亡方式体验暴力的快感,“我在X海鹰家里,双手擒住X海鹰的手腕,一股杀气已经布满了全身,就是殴打毡巴,电死,蹲在投石机背后瞄准别人胸口时感到的那种杀气。”最后作为我,在这样的行动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完整性体验的男人:“它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使我勃起,头发也立了起来。”当X海鹰终于从“帮教”房间里出来,当她脱去了鲜红色针织内裤,当她赤条条地躺在棕绷大床上的时候,我的革命也就完成了,而从革命开始,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它不是一种逻辑,在反逻辑意义上它甚至具有了普遍性,“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暴力快感、革命激情和性爱欲望,在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中获得了真切的感受,而在《黄金时代》里,这种悖逆式的解构更成为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不无辜”。“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已经结了婚的陈清扬找我要证明她不是别人口中的破鞋,这个要讨论的事情有两点疑问:一是陈清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二是她为什么找我证明?这两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让大家信服变成了让自己信服,因为关涉到的陈清扬和我都无法完成证明,甚至于证明本身就是从无辜走向不无辜:无辜意味着要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意味着人是合理合法合规地生活着,或者说,“无辜”本身就是一个讨好别人的态度,而推翻“无辜”的观念,走向一种“不无辜”,就是走向自我,走向本性,走向自由。
陈清扬来找我,是因为大家都说她是破鞋,破鞋意味着结过婚的女人偷过汉,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领导,在不知道陈清扬私生活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无辜也变成了伪命题,而我提出的证明方式则直接指向了身体叙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大家设想的破鞋指向陈清扬的道德问题,而道德所直接反映的便是作风,便是和身体有关的行为,所以我以身体叙事回击别人的身体误读,也正是从虚构的身体回到真实的身体,无辜也便成为了对于不无辜的证明——用返回人性的不无辜推翻别人口中的无辜,解构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这种否定式的肯定,或者肯定式的否定就是在本能意义上的消解,所以我对于不无辜的证明方法便是:陈清扬是处女;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一方面是这两点在别人那里都是难以证明的私事,所以不再是无辜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些私事又和我与陈清扬两个人有关,所以揭开了不无辜的生活:我在21岁生日那天在放牛的荒僻地方有了一次雄浑有力的勃起;我开始关于自己的欲望,想爱想吃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成为了我的真实想法;甚至我想和陈清扬性交,想研究她的身体结构——走向真实身体,走向私有生活,走向本能欲望,这种不无辜便是让我们进入到了“黄金时代”:“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在山上的小屋里,我和陈清扬好上了,我的小和尚开始直挺起来,陈清扬脱光了衣服乳房坚挺,在不无辜的生活里,我们走向了那个时代的反面,或者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便是真实,便是赤裸,便是面对面的身体,“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但是两个人要证明自己的不无辜,显然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无辜依然充满了荒诞的力量,党代表、队长、人保组、团长,都拥有集体话语权,批斗、斗争差,都构成了对于私生活的剿灭方式,“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写交待材料,他还说,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如果我不交待,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而我们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对抗,而最后的胜利其实证明的无非是不无辜的可能意义,“但是谁也没权力打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即使之后和陈清扬分开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在两个人的黄金时代,不无辜成为维护自身的实践,成为真实的身体叙事,反倒变成了真正的证明。《黄金时代》之后是《三十而立》,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已经和二妞子结婚,已经在大学任教,“三十而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社会人?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规范体系里?
其实依然是不无辜,依然是身体叙事的再展开——我邂逅了曾经交好过的小转铃,一种重逢揭开了身体的记忆,而记忆之中的那首诗就直接指向了身体的敏感部位:“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倒挂的性器官,性器官入诗,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人的颠覆。除了性意义上对于婚姻的颠覆,我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虚伪》,首先证明的是作者王二的不存在,“我那篇论文是这么开头的:假若笛卡尔是王二,他不会思辨。假若堂吉诃德是王二,他不会与风车搏斗。王二就算到了罗得岛,也不会跳跃。”这种不存在具有一种普遍性,“不但王二不存在,大多数的人也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大多数人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在虚伪的社会中不会写和阴茎相关的诗歌,而在虚伪的规则和不存在的“王二们”之外,我作为第一人称便成为了存在本身:“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是赤裸的身体,是倒挂的阴茎,是不无辜的生活,甚至是生命本身——在那个父母使用避孕套的夜晚,因为是旧货,后来破了,我便漏了出来,有了生命——从性生活本身开始,在一种社会性的束缚中漏出来,这种生命的诞生既回归到了欲望本身,也突破了规则,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和身体有关的真实欲望和存在本身。而在《似水流年》中,离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又遇到了旧情人线条,而线条是李先生的妻子,这种关系又遭遇到了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不无辜一样,正如性器官倒挂一样,在“似水流年”中我的回忆变成了另一种身体叙事。回到那个年代,是李先生从香港赶回来贴大字报,最后被人蹿了一脚导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是贺先生无法忍受批斗从楼上跳下,死去时那个东西却直挺挺在那里——一种是和政治有关的受伤,却最后成了留在身体里的符号,一个是和政治有关的死亡,却最后变成欲望的不死,“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
打击和死亡,是那个时代在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常事,它们最后都回归到了和身体本身,所以对于我来说,和线条“似水流年”的生活,便也成了对于自我本能的一种展现,“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甚至暴力、死亡本身也是生命力的体现,“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社会性的革命,时代性的暴力,最后变成了私有的、欲望层面和革命和暴力,即使似水流年,也不是矫饰,也是一种真实,“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的能量。”
死和活,政治和欲望,规则和生活,权力和身体,无辜和不无辜,都构成了一种对立,但是从云南插队时的陈清扬,到回忆中的小转铃,以及旧情人线条,在和女人的关系里,作为王二的我充分展现了性意识和性仪式,回到存在本身,创造黄金时代,这是一种对道德意义的颠覆,这是一种对荒诞时代的改写,这是对社会规则的涂抹,但是个体力量真的可以在不犯矫饰之罪中让阴茎挂下来,真的可以在不无辜中让生活具有最原始的冲动?《我的阴阳两界》似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患了阳痿——与其说我是身体上的阳痿,不如说我是政治上的阳痿,“阳痿根本就是一种思想病。换言之,上面的思想端正了,下面也会端正。”就像我干不正经事写小说,被退稿到党委办公室,退稿信里不是关于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建议对投稿人加强思想教育”,所以当阳痿成为一种社会症候,其实折射的是阴阳两界存在的对立。
“这叫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生活,它也有阴阳两界。在硬的时期我生活在灯光中,软了以后生活在阴影里。”光明和阴影割裂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一个是思想端正的,一个是道德低下的,一个是文明社会,一个是野蛮社会,就像李先生所拥有的汤恩比的历史哲学,其中说到,“人类的历史分作阴阳两个时期,阴时期的人类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吃了就睡,睡足了再吃,浑浑噩噩的生活。后来人类又到一些河谷平原聚群居住,有了文明,一切烦恼就由此而起。”当文明意味着正常、规范、有思想,它必然造成另一个世界的阳痿。而我的医生却是女人小孙,在性接触开始的治疗中,身体却被激活了,“后来她把身体俯得更低了,这时我能感到她呼出的热气。等到事情完了,她在我身边躺下时说道:咱们俩同时达到了性高潮。”但是这却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在阴的同时阳存在着,在硬的同时软存在着,我们达到了性高潮,然后是结婚,然后是分到了房子,然后我知道小孙是个女权主义者——在重新回到社会层面,回到正常、规范、有思想的世界之后,我的阳痿便成为一种过去式,但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阳痿的开始?我开始参加学校会议,我开始成为中年骨干,我开始准备去美国进修,“院长对我说,咱们医院懂电子的人少了,你的病好了,就得多干点。”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又成为普遍主义的“王二们”,我又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但是在讥讽中,在戏谑中,“不免就要改变口吻”地成为我自己,在不无辜的证明中,在存在本身的黄金时代里,在阴茎倒挂的似水流年中,我就在反熵过程中回到了只属于自己的身体本身,“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已,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反熵过程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