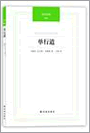|
编号:B82·2201215·1717 |
| 作者:【德】本雅明 著 汉娜·阿伦特 编 |
| 出版:三联书店 |
|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
| 定价:38.00元当当14.00元 |
| ISBN:9787108051011 |
| 页数:294页 |
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他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和希望、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因此就获得了某种暖昧的伦理学态度。本雅明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蒸蒸日上,在一小群杰出人物之中,本雅明属于更稀有、更卓尔不群的一类。对此,早在六十年代末,当“本雅明热”横跨大西洋在北美登陆之际,汉娜·阿伦特就在她为英文版《启迪》所作的长篇导言中详加阐述。而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当时她在美国默默无闻,通过引介本雅明和著述逐渐获得了声望,在她看来,本雅明是与尼采和海德格尔可以交手的人物,尽管本雅明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逃兵,一个集市中的流浪艺术家。本书收录了《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张旭东》《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汉娜阿伦特》《论尼古拉·列斯克夫》《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等文章。
《启迪》:借“自然之声”发言
“迷失在这个卑鄙的世界里,被人群推搡着,我像个筋疲力尽的人。我的眼睛朝后看,耳朵的深处,只看见幻灭和苦难,而前面,只有一场骚动。没有任何新东西,既无启示,也无痛苦。”
——波德莱尔
不是在“卑鄙的世界”里迷失,是在复数的阅读中迷失:撕开封闭着的塑封,打开三联版的《启迪》,看到的副标题是:“本雅明文选”,而编著者是汉娜·阿伦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本编号为E38·1990712·0495的《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是不是就是《启迪》的一种复制?《启迪》里有《打开我的藏书》,有《译作者的任务》,有《弗兰茨·卡夫卡》,有《什么是史诗剧?》,有《普鲁斯特的形象》——《本雅明:作品与画像》的七部作品有四部重新出现在《启迪》中,是不是阅读将会变成“没有任何新东西”的迷失?
一本是1999年第一版的图书,另一本是2014年10月第一版的图书,一本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一本则有三联书店出版,一本是关于本雅明的“作品与画像”,一本则是本雅明的“文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书名,当然形成了不同的藏书编号,更重要的在《启迪》中作为编者的汉娜·阿伦特在《作品与画像》中则变成了对本雅明作品的一般解读,它被放置于文本的最后面,当然,“导言”也成为了“附录”——《启迪》应该是以汉娜·阿伦特为阅读视角编辑的一本图书,当在《作品与画像》中成为七篇文选中的一篇,是不是湮没了作为编者的引领地位?而面对大部分篇章相同的两本书,在翻译异曲的风格下,到底该如何阅读?
偷懒如我,直接跳过了那四篇文章,也抽调了阿伦特的《导言》,于是“启迪”变成了残缺的文本,就像那篇关于藏书的文章不再阅读,是不是一切都进入了本雅明对藏书者的讽刺,“藏书一旦离开了私人藏家也就失去了意义。”不是藏书作为物品本身的意义,而是在却是了“私人藏家”之后,记忆中展现的经验、被复活的“继承人”将在离开之后失去了意义——作为编者的汉娜·阿伦特当然就是那个复活“继承人”的催化剂,当放在最前面像是开启本雅明文本进口的钥匙被抽离,“活生生地再现”就变成了彻底的缺失,以致“不是说书因他而活,而是他活在书中”也变成了一种传说,或许阿伦特的眼睛像波德莱尔一样“朝后看”,于是在一场骚动中看不见任何新的东西,“既无启示,也无痛苦。”
一种阅读,因迷失而抽离?还是因抽离而迷失?仿佛阅读也变成了“既无启示,也无痛苦”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更在行为艺术中在解构着本雅明所定义的“机械复制时代”——复数并非是单纯的复制,但是复制却一定是形成了重新收录其中的四篇的复数。如果只是回到藏书层面,回到私人藏家的意义,回到“继承人”的视角,其实作为编者的汉娜·阿伦特和作为阅读者的我,都站在同一位置,重要的是打开凝聚记忆展现的经验,重要的是让文本“活生生地再现”,重要的是“活在书中”——如果按照本雅明沿着波德莱尔抒情诗的道路前行,那些耳朵深处的幻灭和苦难,那些向前看见的骚动,那种“既无启示,也无痛苦”的体验,一定会在游荡者离开之后黯淡下来,从而发出自己的光辉,找到属于自己的灵魂。
“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是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定义,一个时代和一个诗人,本雅明并非是让两者处在包含与被包含之中,而是将其并置在一个时代的体系里,它们构成了对立之下的突围姿势,而这种突围便是波德莱尔代表的“抒情时代”。在本雅明看来,那个时代不是以抒情作为特色,而是抒情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首先,抒情诗人已不再表现诗人自己,其次,波德莱尔依赖抒情诗从未获得大规模的成功,再次,则是公众对抒情诗更加冷淡。抒情诗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代,是感官快乐越来越被偏爱的时代,是意愿的力量和集中精力的本领越来越淡化的时代——本雅明说,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导言就是写给这些读者看的。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哲学吹响的号角是期望在“生命哲学”中把握“真实”的经验,这种经验同文明大众的标准化、非自然化了的生活所表明的经验是对立的,所以“生命哲学”这个总标题下,经验不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活,而是“乞灵于诗,更甚,乞灵于自然,而最终乞灵于神话时代”;伯格森的《物质记忆》就是把经验看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经验,把时间的绵延看成是经验的本质,诗人成为胜任经验的唯一主体;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便是具有了“伯格森想象”的文本,经验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自然,它在“非意愿的”和“回忆”中构筑了一个孤立着的个体;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试图发现“导致精神伤害的种种类型”,它在精神自我和肉体自我之间架设了扭曲的变形结构,而波德莱尔以一种“搏斗的姿态”表达对这种结构“震惊的防卫”……
波德莱尔的“震惊的防卫”,要保护的是什么?本雅明认为,这种震惊属于“对波德莱尔的人格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经验之列”,它开启的是意象和观念、词与物之间的裂隙,就像纪德所认为的,“这些地方才真正是波德莱尔诗的激动人心之处。”激动人心之处便是在这个机械复制时代出现的抒情诗,而这些抒情诗让每个人都表现自己的意愿力量和集中经历的本领,在不乞灵于诗、乞灵于自然、乞灵于神话中具有社会生活的经验:大众成为波德莱尔的一部分,“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所以大众的出现决定了《恶之花》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暗喻:大众是城市里的大众,波德莱尔不写巴黎人也不写城市,而是在“通感”中描述了“一种寻求在预防危机的形式中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经验”,它以把自身作为美的事物的方式呈现出现。
波德莱尔的“通感”并非是宗教仪式中的运用,而是成为大众的一种经验形式,让自身作为美的事物呈现出来,这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灵晕”:它是一种看的能力,是看见的能力具有的魅力,“这种魅力可以作为补偿它的本能欲望的一种方式。”就像《恶之花》中两行了不起的诗作中所说:“雾一般的快乐朝天边逃去,/一如翅膀后面的空气的精灵。”但是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所说的“灵晕”却在机械复制时代消失了,“波德莱尔对达盖尔照相机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他认为照相是吓人的,是冷酷的,它让灵晕在人们朝达盖尔照相机里看到的时候消失了,“因为相机记录了我们的相貌,却没有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
看的能力被消解,于是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最后一部在全欧洲引起反响的抒情诗作品”,当卑鄙的世界制造了迷失,当耳朵的深处只有幻灭和苦难,当前面看见的是“没有任何新东西”的骚乱,波德莱尔以抒情诗人的身份进行着最后的抗争,“他为赞叹它的消散而付出了高价——但这是他的诗的法则。他的诗在第二帝国的天空上闪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波德莱尔成为第二帝国天空下“一颗没有氛围的星”,他以孤绝的方式,以抒情的经验,成为照见自身的“灵晕”。与波德莱尔以抒情作为其母题不同,在本雅明看来,照见自身“灵晕”的卡夫卡则以寓言的方式“倾听着传统”。
“卡夫卡的作品像一个圆心分得很开的椭圆;这两个圆心一个被神秘体验(尤其是传统的体验)支配着,一个被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支配着。”现代大城市居民的体验是后波德莱尔时代的大众经验,“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即使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像达盖尔照相术的吓人和冷酷依然还在,但是它却变换了形式,变成一种让城市居民麻木的统治力,而卡夫卡重新寻找的“灵晕”却是让经验世界通过“神秘传统”透露出来,卡夫卡在文本中制造了一个互补性的世界,他对包围着他的事物毫无意识,但却对“正在袭来的事物”感受真切,这是作为一个人对事物的感受,“卡夫卡倾听着传统,而全神谛听的人是视而不见的”,所以本雅明认为,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他守住了真理的可传达性和寓言成分,他的作品本质上都是寓言故事,但它们的痛苦和美使之“不得不变得甚于寓言故事”,这种甚于寓言的存在更是卡夫卡“倾听着传统”的一种创造,在只有智慧的余烬时,他依然保留了他的妩媚和自信,“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自己的失败造就的狂热是卡夫卡的一个寓言,是人对事物感受回归传统式倾听的“痛苦和美”,是穿过神秘创造的“智慧的余烬”,当然更是让被官僚机构摆布的现代人看见自己的经验——本雅明把“经验的贬值”看成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战略的经验为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经济经验为通货膨胀代替,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操纵。”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波德莱尔的抒情诗、卡夫卡的寓言将承担起重新拯救经验价值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尼古拉·列斯克夫的故事,不管是远方来客,还是家居者,讲故事的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有人倾听,而讲故事和倾听所构筑的正是“经验贬值”之后需要重建的“交流经验的能力”。
“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和小说“闭门独处”不同,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的经验,它转变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在“指教”中起到了交流的意义,甚至它成为一种经验的永久存放物,“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在讲者和听者的经验同一体中,听者也总会重述这个故事,像保罗·瓦雷里所说:“他谈到自然界中的完美事物:白壁无瑕的珍珠,丰盈醇厚的葡萄酒,肢体丰满的动物,称这些为‘相似的因果长链所产生的珍贵产品’。”因果的累积叠加时间上永无终日,“仅止于尽善尽美。”所以讲故事变成了一种智慧,讲故事造就了史诗,讲故事尽忠于此时,本雅明认为,列斯克夫“讲故事”的最重要意义是:“造化整体并不以人声言说,而是借‘自然之声’发言,如列斯克夫的一个最有意味的故事的题目所称。”借自然之声而发生,列斯克夫潜入到了造物的低层,对事物的看法邻近神秘,他是导师和智者,“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本雅明说,讲故事人的形象,“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已”。
在抒情诗中看见自己的波德莱尔,在寓言故事中强调自己的失败而带来狂热的卡夫卡,在讲故事中让讲者和听者遇见正直的自己,借“自然之声”发言就是发现真实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在机械复制时代正是一种“启迪”。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让艺术品成为可复制的存在,“机械复制首次把艺术作品从对仪式的寄生性依赖中解放出来。”照相术如此,电影也是如此,它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对一幅毕加索绘画的消极态度变成了对一部卓别林电影的积极态度。这种积极反应通过视觉情绪上的享乐与内行倾向的直接而亲密的混合最为典型地表现出来。”但是当被复制的艺术作品成为为可复制性而设计出来的艺术作品,它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在场”,因为,“原作的在场是本真概念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原作的在场,缺少了本真的存在,被复制的艺术品便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晕。”
复制并不只是属于技术领域,本雅明认为,当大众参与到机械复制的狂热之中,它让“量变成质”的巨大谎言中改变了对世界的参与方式,“新的参与方式首先以一种声名狼藉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它把新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大众加以组织,“法西斯主义并不给予大众他们的权利,而代之以提供一个让他们表现自己的机会,并以此视为它的拯救。”而在美学政治上它便表现为战争,“在维护传统财富体系的前提下,大规模群众运动所能确立的目标是且只能是战争。”而这才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看到的悲剧,才是从波德莱尔的抒情诗、卡夫卡的寓言故事和列斯克夫的故事中受到的“启迪”,当经验世界不再倾听,当“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没有闪亮,当借“自然之声”的发言沉默,甚至“既无启示,也无痛苦”的骚动也不再,没有时间和空间在场的机械复制时代只剩下了异化:“人类自我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共产主义会用政治化的艺术来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