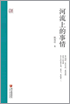|
编号:E29·2120104·0853 |
| 作者:陈前总 | |
| 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年10月 | |
| 定价:26.00元 赠送 | |
| ISBN:9787227048435 | |
| 页数:172页 |
在《代序》中,陈前总说:“重提文学,就是在忙碌浮躁的尘世中寻找那份‘心入’自醉之的感觉。重提文学,就是在功利至上的年代里寻找那份‘凤凰涅槃’后的甜蜜。”而在《后记》中,他说出版这本散文集“无它,一是给自己的青春梦、文学梦‘立此存照’,二是证明自己仍然躬耕着这一亩三分‘山水’。其实这序和后记整整隔了十年,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有多少世事繁华,有多少文字作古,但陈前总还是”微笑着“不断坚守,《人和情》、《山和水》、《长和短》、《刺和箭》、《人和文》,这五辑收入的是陈前总1997年以来写作的近50篇散文、杂文、随笔和文艺评论,而这些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很大,“最早的1997年,最迟的2011年,分别跨越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和工作见习期、成长期”,但是却“见证了我的幼稚和成长”,所以一如“河流上的事情”一样,都是关于时间的某种隐喻,而陈前总似乎有意消弭今与昔的隔阂,在书后的附录里,用10多个页码记述了书中描写的部分老师、亲人、朋友和其他人的当下情况,这“现在进行时”也分明是在对抗着“世事变迁随之带来人情的变化”。
陈前总的祝福短信是在大年初一零点钟声敲响之后收到的,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时刻,我们未曾见面,却隔着千山万水扑面而来,我们之间也只有诗,单纯,却丰富,因为这遥远的祝福,整个夜晚也更像一首诗。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仿佛是有意而为,昨昔与今日,去岁与新年,是一种记忆的积淀,也是生活的开启,放在陈前总身上倒是有些契合。从陈前总的博客上了解到,去年年末已经结婚了,新娘是曾经的同学,而在他的散文集《微笑着的江山》里,特别谈到了“现在进行时”的那些人,说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而从单身走向新的生活,对于陈前总来说,现实会越来越具体,也会越来越丰富。去年,他出版的两本书也像是对过去状态的一种回顾与总结,沉淀在那些时间里,也是为自己开启新的天地的一个切口。
时间会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一路走来,所以会多些感慨,多些自省,特别是陈前总这样一个自称是“深山里的孩子”,每一步都在超越,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所以他说:“一路寻找,在哪一个位置里/可以安放我们久违的笑容》”从最早的1997年到最近的2011年,《微笑着的江山》里都是陈前总岁月走过的积淀,横跨着14年的时间,也横跨着他的青春。所以一路寻找的,必定是可以盛开的青春,那些激情,那些理想,甚至那些冲动。不管是“凄寒的雨夜”传递的母爱,还是赶山风俗中的父爱,还有那些不能忘怀的亲情、友情,都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而对于陈前总来说,岁月里的那些往事都是可以成为精神中最重的那一块,藏在身体的深处,刻骨铭心,然后伴随着长大。
所以,在走出深山的青春岁月的寻找中,陈前总内心有一种矛盾和斗争,那是对世俗的靠近,也是背离,那是对中心的期盼,也是被边缘的无奈。“深山里的孩子”,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写照,何尝没有自己的影子,所以在读陈前总的这些文章,内心里会有深深的共鸣,仿佛就在写我自己,从深山走出,读大学,在一个小城里工作、生活、结婚生子,或者写写诗歌,人生大抵如此,但内心里是有一种潜伏着的呐喊。现实和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他们其实在对面,我们内心的挣扎是因为现实的具体和复杂,而陈前总必须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笑容,用诗歌来抵抗现实的侵袭,“只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有人写下的是享乐,有人写下的是蓄锐。”这样,青春便有了最丰富的表达。
所以,陈前总必须在梦想和理想构筑的精彩世界里,寻找文学。那文学一定触动了我们内心最强烈的部分,在《重提文学(代序)》中,他说“之所以重提文学,是因为很久没有提文学。”,又说,“之所以重提文学,是因为不得不提文学。”很久和不得不,表明着对于自己有了重新救赎的可能,这是2001年10月30日的一篇文章,距离出版这本书已经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在陈前总身上也发生了很多改变,这种改变是不停地为稻粱谋而进行的转身,这种改变是为诗歌寻找另一种出路的奋斗,这种改变是“在忙碌浮躁的尘世中寻找那份心入自醉之的感觉”,这种改变是“在功利至上的年代里寻找那份凤凰涅槃后的甜蜜”。要甜蜜,就必须微笑,这是陈前总的逻辑命题,其实也是乐观面对生活遭遇的最基本表现。
所以“微笑”成了这十年陈前总面对生活的最有力表情,这微笑是“一个人对着漓江的笑”,是“江山装饰了我的笑脸”的笑,是见惯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之后的笑,当然更是对诗歌保持热忱的笑。行走的的江山里,有漓江、鹿寨、铜石岭,“有我们的疲惫和忧伤,也有我们的灵与魂”;行走的江山里也有那历史深处的“鬼门关”,“在我眼里,鬼门关是黑的,漆也是黑的,是包容的、深度的、醒目的、拒绝水货的、不混淆的、暧昧的,是呈现的、冷静的,等等。”行走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对抗着现实,反叛着现实,在要闻、日常生活、爱情、人民币组合成的“曾经熟悉但又陌生的事物”背面,发现诗歌的生存。
又回归到作为一个诗人的陈前总,“南方的圭水小城里,一个叫陈前总的诗歌爱好者,诗意栖居在岭南丘陵上。”而在散文的世界里,陈前总已经成为一个诗评人,站在诗歌的对面,作观赏状,他评论、推荐漆诗歌,桂东南诗歌,他介绍陈琦、朱山坡、伍仟、天鸟、虫儿和那些为诗歌不断努力的同行者,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可贵的坚持,这是浮躁年代的精神栖居地,他用“众声喧哗”和“特立独行”来形容当下现实和他们的努力,而这些品质或许就是陈前总十多年来一路寻找的那一份“安放我们久违的笑容”。
陈前总说:“诗歌是我们的情人。”而“不追风,不媚俗,不自傲;不逐名,不求利,不自贱”是诗人的风骨和旷达,写诗十年,陈前总其实就是在寻找表达自我的方式,在热衷的口水诗中,很容易看出陈前总在文字中的寄托,这种寄托就是在诗歌和现实中找到那条中间道路,找到“久违的笑容”,所以对于陈前总来说,他对于现实并不是革命式的否定,而是汲取灵感,“理想的诗歌应是一种对现实的忠实呈现,这种现实既包括社会的现实,又包括心灵的现实,让事物回到事物中去,还原它们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也就可以理解陈前总身上那种既对世俗靠近又背离的矛盾,既对中心期盼又逐渐被边缘的无奈,也就理解了笑也是一种哭,“包容着我们所有的丑与恶”的微笑是更彻骨铭心的痛苦。
除却诗歌,还原个体,《微笑着的江山》大体是这样一种思路,很明显,文本里面有着对着时间妥协的“立此存照”,尽管看到了陈前总这十多年来青春岁月里的文学梦,看到了不断的努力和诗意的栖居,但是作为一种时间轴线上的汇总,人和事、山和水、长和短、刺和箭、人和文这五辑内容使这册散文集内容过于庞杂,没有诗歌文本的《河流上的事情》来得纯粹,资料式的收录对于陈前总来说,更多是关照自己所走过的那些路,和路上看到的风景,包括乡村、诗歌、爱情,以及江山。
那封面上陈前总的微笑却一直感染着我,是的,那微笑是面对新的时间轴线的表情,也是对“诗意栖居”的乐观坚持,疲惫和忧伤包裹进了我们的灵与魂。走过,便是青春最大的财富,“愈是知道没有的东西愈去追求,骨头自然硬了。”希望从此,我们便抓到了春天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