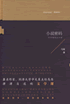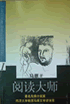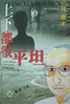|
编号:C28·2140519·1083 |
| 作者:马原 著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35.00元亚马逊25.40元 | |
| ISBN:9787530213070 | |
| 页数:334页 |
“财富中国的一起鸡毛,先锋马原的最新期待”,对于马原来说,腰封上的定位依然是关于“先锋”的,只是这转身之后的“纠缠”里除了财富中国中的那一地鸡毛,是不是也有先锋过后的喧闹和急躁?“卡夫卡+雷蒙·钱德勒,哲学+悬疑——一部从人间烟火抵达生存迷宫的长篇力作”,这样的推荐依然让人觉得马原已经远离了那个孤独世界。作为《牛鬼蛇神》之后复出的第二部小说,马原将笔触伸向了那个商品社会,遗嘱、存款、房产,在这个金钱世界的纠缠中,如何寻找寓意?“这部小说的某个地方写道:姚亮忽然想起了卡夫卡,想起了那些莫名其妙就陷入纠缠的人物,《城堡》中的K,《审判》中的K。”小说刊载在《十月》的时候,卷首语这样写道,也许这也是一把生锈的钥匙:“小说通过一个父亲死后的遗产问题,写出了看似滴水不漏的制度与体系中人的困境,写出了一个个合情合理的小问题给人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麻烦。”
《纠缠》:物化悖论下的泛道德解救
真相不止一个,而是两个。
是眼睛看见的真相,还是故意被蒙蔽的真相?一个或者两个,一个或者无数个,在一种数字呈现的非神秘现实中,真相只不过是我们戴着一副被财富炫化的眼镜看到的一切,而从寓言到现实,从先锋到写实,也是从一个真相变为两个,再变成无数个真相,直到有一天在某种茫然中陷入自我设置的生存迷宫里。
就像从一个马原看见了两个马原,再看见无数个马原,“一部从人间烟火抵达生存迷宫的长篇力作”明明白白写着一种自我迷失的过渡,在书页的下三分之一处,用一层半透明的腰封告示着这样一种困境,只不过在这样的困境面前,即使你看到了背后黑色的封面,看到了被打上印记的“马原”字样,你也无法在“纠缠”的眩晕中找到那种解读真相的钥匙。或者你可以把这样的“生存迷宫”字体再放大,是“财富中国的一起鸡毛,先锋马原的最新期待”,是“当房产与金钱接憧而至,为什么我们会陷入‘纠缠’”,或者再放大,是“2013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的最新期待”——那些刻印在腰封上的文字从来不是为了解读那个生存迷宫,而是要在更弱智的说明中远离“纠缠”,不管是“卡夫卡+雷蒙·钱德勒“,还是”哲学+悬疑“,在一种人为纵横交错的迷宫里,其实并不需要寻找一把解读的钥匙,而是因为在这被放大的字体中,一切都只是营销上的自言自语,它使人看见的不是黑色的封面,不是“纠缠”的图饰,甚至不是作者马原——在一个无数种马原喧哗的文本里,你可以很随意地把腰封揭去,扔进垃圾桶。
这是一种设置好的“脱离”,不属于文本的脱离,不属于作者的脱离,当然也不是从人间烟火到生存迷宫的脱离,它是粘着在一起的现实,是被合成的困境,就像“2013年”之前的《牛鬼蛇神》,在马原的叙述历史中变成返回肉身的一次努力,虽然是一种经历了生与死的颠簸之后的返回,虽然是从寓言世界折回到现实的转变,但至少是在其中收获了一个叫做马原的肉身,而现在,那个拙劣的印章上写着“马原”,那翻过的封二中有着侧身微笑的马原,还有什么是属于“马原叙事”的?“当代著名作家,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简介上标注着他的多重身份,在农民、钳工、记者、编辑之后,是“先锋文学开拓者”,这仿佛是一个终点,接下去再无转变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开创的“叙述圈套”、“以形式为内容”风格都在这个终点上变成某种缅怀,而在《牛鬼蛇神》高调出版之后的《纠缠》,被形容为“归来王者持续劲健的创作实力”,分明是一种在终点处逗留之后的“旋转”,在文字的世界里继续编织,继续叙说,继续颠簸,继续圈套,在一个充满纠缠的世界里体现肉身。而其实,经历了更多的婚姻变故,经历了更多的身体变故,对于马原来说,甚至连肉身都已陷入了危机,而在经历现实的诸多纠缠之后,马原其实已经找不到唯一的真相,他只是在一种混杂着寓言和现实,混杂着精神和肉身的世界里滑行,而他最后睁眼从纠缠的世界里看见的也只是一个没有了自我的“第三人称的社会”。
第三人称没有我,只有他,她,它,以及那集体意义上的“他们”,仿佛都是站立着的陌生人,仿佛都是围拢来的别人,而那个在中间的人可能是创造了文本的哈谢克,或者是卡夫卡,曾经在他们的世界里,看见了那一个变异的“他们”,不管是战争时代还是没落的社会,那些被写出来的“好兵帅克”或者是K,都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活着,不管是“愚蠢”,还是反抗,他们都只存在一个文本的世界,一个已经脱离生存迷宫的世界,所以在马原的世界里,完全变成了“他者”:“2013年1月3日这一天,姚亮终于把那本他已经看了十几年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翻到了最后一页。”十几年的小说翻到了最后一页,是不是代表着过去那个寓言时代的终结?代表着“叙事圈套”的先锋的终结?而姚亮分明是那个远离了西藏的姚亮,远离了文本寓言的姚亮,所以在这本“未竟之作”中,他看到的是一种肉体的终结,“作者哈谢克没能最终写完它就被死神接走了”,以及那种时间履历上的巧合:“非常有趣的巧合是那一天刚好在九十年之前,1923年1月3日。”但是在这样的未竟状态和巧合数字里,对于姚亮来说,不是真正的“释然”,却是一个麻烦的开始。而在这一系列的纠缠中,对于卡夫卡或者K,姚亮也只是以灵光闪现的方式回到寓言状态:“姚亮忽然想起了卡夫卡,想起了那些莫名其妙就陷入纠缠的人物,《城堡》中的K,《审判》中的K。”
“城堡”是不是一种被围困的现实,“审判”是不是生存迷宫的异化?对于好兵帅克,对于K,姚亮只是在“忽然想起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文本的世界,仿佛早已走远,而对于这个第三人称的姚亮来说,在看见之后,在释然之后,却是一个扑面而来的财富世界,令人措手不及,又不得不去面对。鳏居三年的八十七岁老父姚清涧逝世仿佛是这一切变故的开始,这是肉身消灭的一个故事,在死亡面前,留下的是一张遗嘱,两个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们活在现实世界里,甚至活在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现实里,所以在死亡之后,一切的变故变成了理不清的纠缠。
连同三年前逝世的老伴的遗产捐赠给母校檀溪小学,这是遗嘱上的内容,按照估算,遗产的总价值大约在五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人民币之间,这是一个和道德有关的捐赠,彰显的似乎是一种社会正能量,但是在这样一大笔数字面前,却牵涉出更多的法律问题,比如姚亮的前妻范柏就质疑这样一份遗嘱只是姚亮自己的意愿,因为在曾经的交谈中,老父亲说过要把自己的东西留给孙子姚良相,在他的判断中,父子存在着利益上的纠葛,连同姚清涧曾经说送给姚良相的那一对底款“大明成化年制”的五彩手绘瓷瓶都是财产赠予的证明,而姚亮坚持认为自己是瓷瓶的拥有者,他以一种成年人的俯视角度去看待未成年的儿子姚良相。但是当姚良相在出国留学之后,需要经济资助的他已经站在了成年人的行列,所以对于财产有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一种拥有和支配之间,形成了父子之间的积怨,“他有权利要求把自己的东西拿在自己手里。”而在上海的一处房产上,姚亮当初把姚良相的名字写在了房产证上,这在姚良相看来,自己拥有一半的资产,而在姚亮看来,当初写上名字也只是体现了他对于儿子的爱,如何支配这一房产则属于自己的事。
父子积怨,这样赤裸裸的财富纠缠自然是对于爱的一种挑战,而姚清涧的遗产在充满道德意义的捐赠上,受到的是质疑,也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纠缠。比如要开具母亲的死亡证明,比如要证明自己是姚清涧的儿子,比如要证明保险单的“姚勤俭”就是死去的姚清涧,在这样赤裸裸呈现的法律关系中,对也同样面对着父子之间基本伦理关系的确认,十七岁从中学毕业,名字在四十二年前就已经从姚清涧家的户口本上注销了,而如今五十九岁的姚亮必须证明自己就是八十三岁姚清涧的亲生儿子,这样才能拿着姚清涧的房产证去委托中介机构售卖房子,“忽然有人要他证明自己是自己父亲的儿子,他何德何能当此重任啊?”同样面对这一问题是姚亮的姐姐要命,“比姚亮年长四岁的姚明要证明自己是妈妈的女儿,显然比姚亮要明自己是父亲的儿子还要难,因为姚清涧姚亮都姓姚,而母亲却不姓姚,母亲叫褚克勤。”父子、母女,在这种血缘基础上的人伦关系,遭遇到了法律文书缺失的现实,也就是你不如何能证明自己就是那个父亲的儿子,如何证明你就是那个母亲的女儿,甚至你如何证明你就是你自己?
所以在法律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自我以外的异化身份,包括儿子姚良相对于赠予的解读,都在某种程度上销蚀一种爱,甚至慢慢演变成了法律上的纠纷。姚清涧当初没有及时注销死亡的妻子在社保上的名字,所以被起诉为冒用养老金,而姚明和姚亮作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同样面临被起诉,“先是你父亲的不作为,导致占有国有资产的事实;然后是你们的不作为,又延续了你父亲造成的恶果。如果你父亲的行为被判有罪,那么你们的继续也会被判有罪。”当初父亲或者是失误,让对其中事项一无所知的姐弟陷入涉嫌诈骗的困境中,而要证明自己没有违法,也需要相关的证明。
证明是不是可以接近真相?尤其在法律意义上的那些文书,是不是可以让人回归到真实状态?而这样的一种窘境,却完全是因为涉足了一种财富生活,姚亮是大学教授,也拥有自己的私人房产,而姚明拥有更多的资产,可以说他们就是活在那样的一个和金钱有关的世界里,姚明说过:“我也算了解金钱是什么东西,越了解它我就越蔑视它,但是蔑视并不妨碍我喜欢它。”喜欢金钱只是因为凸显了它的价值——不是象征的财富,而是一种支配力:“钱为没有标准的世界定出了标准,人类从此有标准可依,许多事情都因此而筒单了。”所以他们可以出钱请最好的律师,可以用钱打通各种关系,但是即使在这种充满支配的物质世界里,也依然面临着道德被质疑,爱心被怀疑的现实。
甚至,在这个充满支配欲望的世界里什么是真相?是父母血缘编织的爱是一种真相?是各种官司的输赢决定的真相?姚亮对儿子姚良相的爱最后变成了一种隔阂,甚至变成了积怨,在金钱面前,似乎爱被遮蔽,真相当然也变成了一种无法证明自己就是那个我的游戏。而在法律面前,真相无非也是一种用文书、证据和律师组合起来的世界,它的状态不是抵达,而是远离。甚至姚清涧捐赠给檀溪小学的那笔捐款,在校长力拒将捐赠房产变现也陷入了窘境,而更为残酷的是,在这样一种赤裸裸的真相面前,人也只是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质疑用爱绑架的符号,一个支配金钱却又被金钱支配的符号,甚至是一个失去了判断和逻辑能力的符号——姚明在覃校长的刺激下,竟然患上突发性脑溢血,差点连命也丢掉。
而在这个纠缠的现实面前,看起来那种人伦关系虽然有矛盾,但至少脉络是清晰的。但是吴姚的到来又彻底将这种隐藏着时间深处不为人知的人伦挖了出来,他自称是姚清涧的儿子,一张证明信用手印证明他就是姚清涧在老家的发妻所生,是姚清涧的长子。这不仅在解构着原本清晰的父子关系,也在某种意义上解构着父亲的形象:“一个负心汉,花女人家的银子读了许多年书,之后把女人的肚子搞大就拍拍屁股走了。这个人当真是自己的老父亲,是那个一辈子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的姚清涧老先生吗?”从未在生活中出现的陌生人吴姚可能成为另一个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在这个急需要真相的困境面前,律师说出了那不止一个的“真相”:中立的真相,也就意味着吴姚也许就是他和姚明的亲哥哥;偏向于否决吴姚说辞的真相,这才是他们已经议好的方向。也就是说真相变成了两种参杂主观意愿的真相,中立或者偏向,而这两种真相会趋向于不同的结果。姚亮甚至亲自去了老家,律师甚至雇了私家侦探,目的就是证明吴姚是一个骗子,他只想占有姚清涧的一部分遗产。
在这样一个需要制造真相的社会里,一切的爱,一切的人伦,都变成了远离亲情,远离道德的存在,而不管是姚明,还是姚亮,在金钱支配的欲望下,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里,姚亮只是偶尔想到了卡夫卡,想到了不能进入的城堡,想到了无法逃避的“审判”,而姚明也在这赤裸裸的金钱纠葛中,以患病的方式失去了控制力。掌控着几千万的资产,却陷入了被金钱支配的深渊,肉身在这一刻脱变成了“物质”,也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物化”了爱与真相。而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纠缠,马原又以一种人为操作的手法构筑了一种解救的模式,那就是道德。姚亮的新任妻子是基督徒,在这一份皈依上帝的爱面前,帮助姚亮化解和前妻的怨恨;而姚良相的女友玛丽也通过自身的爱,融化了父子之间的积怨,让爱重新回到身边。而打赢那场关于社保冒领的官司,律师最后的致胜武器也是姚亮提出的道德力量:“父亲的捐赠是一个壮举,是百分百的学雷锋行为,是一个伟大灵魂的起程。现在有人意图将这样的壮举变味,给雷锋精神抹灰,有意让这个伟大的灵魂蒙羞,这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答应的事情。”
很难想象,在需要证据、文书以及真相的法律面前,这样的道德力量会成为打赢官司的决定力量,其实这是一种泛化的道德救赎,将姚明的前夫以姚明丧失对女儿监护权为由住进姚明的居所使用的也是一种“计谋”,那“请法院赶秦关走”的七个字只是病态的母亲“交给”女儿的真相,目的只是为了赶走以监护权为名的不义者,所以在泛道德力量下,吴姚的到来最后变成了将姚明唤醒的良药,在姚明还在坚持骂吴姚是骗子的时候,吴姚的反击是“我听说了,这两个东西都有本事,一个有钱一个有名,人五人六的所以才那么嚣张”。而这正是姚明姚亮陷入这一场纠缠的直接原因,在赶出吴姚之后,姚明忽然说出了一句:“小亮,你怎么就不想认他呢?”这是意识回归的表现,也是从物质到肉身,从迷失到清醒的回归,是认亲下的自我救赎。
“居然是大哥的一顿臭骂把你治好了。”而这样的解救是完美的救赎,还是仅仅只是一种突然之间的感化?所以在真相到来的时候,其实谁都没有做好准备,而在一种被绑架的爱面前,所有的解救之路都已经设计好了,这种圆满看上去是剔除了那赤裸裸的法律,那掩盖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判断,但是物化的支配远没有被否定,甚至所谓的现实是为了纠缠而纠缠,那些变故和转折总是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样的解救是不彻底的,当吴姚变成真相,那看不见的一切又以“真相”的名义冒出来,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太又“闯入”了现实,“老太太自称是褚克勤的女儿,是褚克勤参加革命之前在老家生的女儿。”参加革命之前,就如姚清涧在姚亮和姚明之前的那一段被隐藏的历史和人生,永远没有证人,没有亲见的机会,所以在新的纠缠到来之际,“姚亮当真蒙了”变成了一个逃不出去的陷阱,它继续着,它发生着,在一个真相之后,彷如裂变的病细胞,不断地制造新的麻烦,新的危机,新的城堡,以及新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