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6 《诗意的年代》:没有诗意的行为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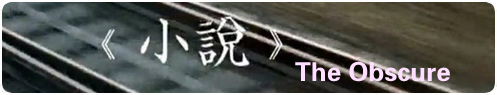
又名《小说》,吕乐的一部未公映的电影,距离1998年的《赵先生》一年,和那部探讨婚姻或者男性生存的电影不同,《诗意的年代》抛弃了电影最起码的叙述技术,以及那份隐喻的解构,看起来平淡,重复,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残酷——我说的残酷是我以为这是一部电影,一种艺术的虚构,但其实只是一种纪录形式的拆分,一个会议,一种讨论,故意拉长到现实可能的方式,把那层覆盖在电影之上的美学理念都剥光了,留下赤裸裸的行为艺术。
甚至没有专门设计的电影海报。
诗歌、小说、电影,这些词语的组合必定是走向一个艺术的维度,在如何呈现诗意的问题上,吕乐似乎更愿把你抛向一个无边无际的沙漠,找不到绿色,找不到水分,茫茫之中你站在一个点上,然后便是意识里的扩大,扩大,直到你变成沙漠,把原先包围你的沙漠吞噬。我说过,和第五代其他导演相比,吕乐的革命性更强烈,也更彻底,他用一个革命式的举动拆走纪录片与剧情片的框框,将两者放在同一议题与空间自由对话。那是1999年的初秋,吕乐想到了一场行为艺术,然后用镜头记录下来,再然后他觉得沙漠中只有自己,便不再去寻找水源,不再希望走出去,于是电影终究不像是可以公映的艺术,他放弃了把他呈献给那些沙漠之外的人。
这个意图可以通过王朔的《无知者无畏》获得最完全的解答,在《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一文中提到了这个关于行为艺术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时间:九九年十一月八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丁天,王朔
于是便开始了,会议室,服务员,倒茶、抽烟,以及讨论的话题:什么是诗意。对于这个场景,导演和影评人崔子恩曾经在一篇评论里写到:“电影观众和电影批评家看惯了扮装的演员出入画面,无论美丑老幼胖瘦,他们是电影国度中的合法公民,器官健康,行为中肯,面目香喷喷。《诗意的年代》开场不久,却杀出了一群有名有姓、身份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阿城、林白、徐星、陈村、须兰、赵枚、方方、丁天、王朔、马原、棉棉,一串名字背后是他们真实的存在,而且真实地抽烟,真实地喝水,真实地讨论,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对于“诗意”的理解,阿城从中国诗歌的起源谈歌咏言,诗言志,诗歌承载的诗意,陈村认为诗意是酸腐文人的病态思想,并且得意洋洋的将生活一样样的具体化,将乐趣具体化,他认为做人的事就会快乐,人不快乐是有做上帝的欲望。赵枚说,诗意是心灵的生活,特别适合女人的生存状态,方方说如今的社会诗意也是打油诗的诗意,诗意是存在于回忆中的。王朔认为颓废到底才能见诗意,被社会拒绝至极,落到最低点,诗意就产生了,或者说是疯癫的纯粹精神的产物。丁天则认为买车买房才会有诗意,马原也认为诗意是个人的,和文化、历史无关,自由才更有诗意,而钱因为太有用没有诗意,生活只分为两种:解析和不可解析、理性和非理性。
讨论一直持续了三天,仿佛看到吕乐就架着摄影机,固定对准这些“有名有姓、身份确实、出处可查可考的作家”,没有一点动感,只有关于诗意的完整表达,陈村用了3分钟,棉棉用了5分钟,马原用了10分30秒,阿城用了11分30秒,最长的王朔用了13分钟,时间就这样在这个看似高雅的话题中流逝,你仿佛在听一场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身临其中,受益匪浅,但是吕乐的颠覆绝不仅仅提供了一个作家话语权力的舞台,最重要的是,他要在这样的会议记录中找到另外的隐喻。于是,服务员陈晓,从泡茶倒水的配角走向前来,从虚幻形象走向真实,五官清晰,表情丰富。在会议间隔的时候,镜头从架子上拿下来,转向她,铺陈开来,先是和儿子人打电话,充满温馨,之后遇到了在宾馆谈生意的赵子轩,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的恋人。于是电影像电影一样发生了,他们相遇之后,便开始散步、聊天、游戏、吃饭,以及对各自现状的讲述,关于婚姻,关于工作,关于四岁半的儿子,“无所谓好不好”的生活让他们都很平静,不蔓不枝,却在眼神中有着难以摆脱的暧昧,于是他们开始回忆那段时光,在大学里的生活,欢笑、奔跑,看起来真的充满诗意,就如方方所说,诗意在于回忆过去。最后他们坐在一起,陈晓突然触动了,哭着倒在赵子轩的怀中。接下来,便是街道、集市、农田,陈晓独自坐在车上,离开城市,就像电影最初的叙述方式一样,从进入到出走,没有交代最后的故事。
电影戛然而止。似乎陈晓和赵子轩的故事是在回归电影,却也像是在阐释作家们讨论的所谓诗意,从理论到实践,从纪实到虚构,赵子轩是中文系毕业,陈晓问他现在还写吗,赵子轩说写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他现在在做项目,在赚钱,这种生存方式正如马原说到的,写不出什么了,感觉自己是个“无用”的人,过着“无用的生活”。这种“无用”是不是人生诗意的没落,阿城早就提到过诗的没落是因为小说取代了诗歌的位置,新的载体取代了言志的诗歌,所以诗意消失的背后是“小说”的开始,就像那场讨论结束,陈晓和赵子轩坐在草地上陷入绵绵的回忆中,之后,陈晓倒在了赵子轩的怀中,他们进入了小说的虚构中,两个人的暧昧在那个夜晚展露无遗,就像英文片名《The Obscure》一样,朦胧、 模糊和晦涩。最后呢,他们会不会走向更诗意的结局?电影又突然把你拉回到作家现实中,在陈晓独自离开后,作家们开始了关于两个人最终走向的讨论,王朔说惆怅,后悔,徐星说上床,赵枚说,可能什么也没发生,方方说,接着吵架吧,丁天说,可能一个会把另一个杀了,棉棉说,让他们去看卡通片,放松点,陈村说,两个人好不太容易见面,要对对方好一点,令彼此都满意。然后他被服务员搀着离开,而那个服务员就是曾经的陈晓。虚构或者小说,又一次被解构,像极了那种被称为“元小说”的东西,只不过你始终会想到在镜头的背后,吕乐正用计谋得逞之后的满意目光望着这个世界。
“吃饭的时候吃饭,诗意是不可触摸的。”“毁灭的东西里有着诗意。”“诗意和爱一样,是每个人自己需要的东西。”“诗意可以去创造,就像情人节的玫瑰”……在他们关于诗意的伟大讨论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诗意的逐步解构,诗意的年代其实就是没有诗意的年代,编剧之一的刘仪伟说,“赶上世纪末,我们打算做一个向文学致敬的电影。” 而他的虚幻镜头只闪过了2秒,向文学致敬的背后是阿城手中的打火机,是王朔摆弄的烟壳,是开心女人眼前闪现的一堆篝火,是网上观影的四个段落的断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