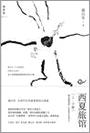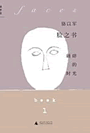 |
编号:C28·2160421·1290 |
| 作者:[台]骆以军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55.00元亚马逊15.80元 | |
| ISBN:9787549554591 | |
| 页数:484页 |
“我们常说单一个体的记忆,比起一座城市的记忆,就像一滴水小时在大海中。但城市有时又年轻又无情地无法消化时间过于悠长的单一个体。”城市的记忆属于压挤逼仄的空间,属于贫瘠苦闷的情感,而那些个体的记忆里,却是青春、欲念、生命和爱。神光笼罩、梦幻蒸发的传奇少女;独守废墟古厝的老人们,把出租车当育婴房的女司机,他们生活在一个压挤的世界,他们都在演同一出戏,然而正因为如此,便有那相逢时的会心微笑——你会懂得他们,他们会懂你,虚无浸泡的夜晚,那些熠熠发光的诈骗挑逗短信,竟也懂得用“寂寞”这个词;而游泳馆置物柜随手可见的号码牌,原来是上帝作弊彩票给你中的摩斯密码……《脸之书》是骆以军《壹周刊》专栏文章的终极精选,它勾勒那些偶遇却难以忘怀的脸孔,倾听那不堪埋没的人间世情。浮生聚散、往事微茫,在一部令人目不暇给的城市浮世绘里看见自己。
《脸之书》:看得见的城市
似乎每一个“许多年后……”的句子都会成为一篇好故事。
——《多年以后》
Book1和Book2,脸之书的这一面和另一面:这一面是眼睛和鼻子的线条,另一面是嘴巴的轮廓;这一面是看见和闻道,另一面是说话和表达——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个简笔画的脸,如何面对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在题辞上,这是这一面的城市,重复而夸张,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而在另一面,一样是《看不见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却变成了记忆:“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重复而夸张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记忆,都是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就像原本分列两册的脸却分明合在了一起,那灰色的腰封从Book1的封面,绕过书脊最终包围在Book2的封底,它连接着Book1和Book2,甚至包容着这一面和另一面。是不是看见、闻到和言说可以合二为一?是不是视觉里的城市和被叙说的城市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在包围的腰封之外,却分明打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翻阅,允许进入,允许看见,也允许看不见,那里是压挤的城市,是密闭空间,是你来我往,是虚张声势,是重叠的情感,是模糊的记忆,是逝去的梦境,而最后依然在这面和另一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在腰封连接而包围的时候,看见其实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也是看见:城市是一个存在,它不会以看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消逝,也不会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状态中虚构。
首先或者是看见,睁开眼睛,也是从那一个留着的进口出发,是一条“末日之街”,那里有感伤的故事,那里有孤独的时光,那里有虚拟的存在,“我们活在一个蜂巢状全景像钟壳内部齿轮自主运转到这般地步的一个社会,或一座城市里。”蜂巢状的全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却是挤压而单调的,却是渺小而封闭的,但是在内部,齿轮却在自主运转着,它告诉你早晨和傍晚,它带你走进白天和黑夜,它经过年轻和苍老——这是时间赋予的原始状态?这是生活给予的存在方式?但是蜂巢状的全景世界里,在人们如幽灵穿过的广场之上,在不被知晓混在同类的成长之中,那自住运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
那个无声无息退出社团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讨厌社团里的“红夹克”,而是在喧闹的世界里独自面对消失的幻术,原本挤满人的广场,原本积极抗争的运动,最后剩下的是漫天飞舞的垃圾,是堆成小山的矿泉水空瓶,空空荡荡回应着一个出院的病人,“问题是,那整个过程,这些警察,像把我们当透明人或幽灵那样穿过我们。”人之存在和不存在,像是虚幻的一个事件,它的热闹会带向一种权利?它的消失会终结一种故事?无非是感伤而已,甚至当年广场权力核心人物成为金融操盘手之后,在婚礼那天却和相交数十年的情人度过了最后一次春宵,而完事之后,既没有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也没有进入说谎的“南部开会”议程,而是跑去另一个房间,“然后召妓”。
感伤的故事,因为那内部齿轮就在那里自主运转,情人和婚姻,事业和政治,都远离最后的那一个夜晚,轮盘如一家机器,是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付出,无非是回到物欲的状态。而留在那里的人呢,情人,妻子,还是那个从医院出院的她,似乎早已经被自主运转的齿轮所排斥,看起来是“孤独时光”,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但是那一对美丽的兄妹,身为私生子却混在人群中是融合的,看不出他们本和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成了“一群爬在一起悲伤的蜥蜴”,“无从分辨出其实是孤独到只剩己一人的那个……”
也是合二为一,却是荒谬的,而分开同样只不过是离开了那一个个齿轮,在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世界里被抛弃,所以十岁父亲去世、母亲和男友去了大陆的慧宁,生活是“对自己负责,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那一对兄妹,毫无隔阂的和那一班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其实都在末日之街里成为另一种幽冥可悲的风景:“我们总想讨好取悦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家伙,我们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
末日之街本就呈现着这个城市看得见的风景,而这也无非是“砸碎的时光”,作为工人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全新豪宅里至少两三百万的装潢,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打烂、砸碎,豪宅里的一切是城市看得见的存在,它或者代表财富,或者代表地位,或者代表权力,最后却是砸碎的命运,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底层的那些工人,通过暴力,通过破坏,将财富、地位、权力都变成废墟。像是一种颠覆,可是只是某个命令而已,站在高处的还是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权力,而带给工人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命运:“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腰脊、膝盖,甚至脸颊到脖子处的肌肉,全浸迷进一种无比舒畅的暴力狂欢。”
是那一幢两三百万的豪宅,还是那暴力狂欢的肌肉,代表着自主运转的齿轮?当破坏和颠覆变成一种命令,砸碎的无非是自己的时光。那老旧公寓地下室里都是给流浪汉、酒鬼或流莺偶尔借宿的大通铺,那平安夜的KTV里是像戴着某种仿佛面具的虚假美少女,那盲人按摩院里是像“十数只白色小生物窸窸窣窣静默地啃食着桑叶”的群盲,那暗街深处包围着荒凉艳丽、腴白芬芳的女孩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秃顶、皱脸、全身邋遢,有的戴了粗黑框眼镜的阿伯”,“岁月静好”在何处?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或者如幻灭的梦,或者是游戏一般的虚拟,美少女梦工厂、偷菜游戏、变形金刚,代表着永恒欲望,却又被岁月强压在世界的底端,连Q君看见桌子那边的妖丽娇媚的女子坐在男人身边,都会怀疑是自己的女友投身在别人的怀抱:“或许是我心魔投射的幻影,我内心底层,本就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撞见这一幕”。
只不过是幻觉取代了现实,只不过“砸碎”了真实,暴力狂欢也罢,欲望投射也好,城市的夸张,在于每一个人的夸张,城市的虚伪,在于每个人的虚伪,而现实在别处,“他知道当他走出那房间,站回那冷酷异境的水泥建筑车道时,那已是另一个和本来的世界并不相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是欲望,是权力,是政治,是暴力,而这个世界是伤感,是孤独,是虚拟,是想象,却又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犯错,又不想让自己陷入孤独,于是,在那辆车上,根本没有尿意,没有颠荡,没有膀胱的鼓胀感,没有塑胶瓶装芦笋汁,没有尿裤子还惨的尴尬,没有司机在后弧镜里恶戏的笑脸,只有端坐在开往山城的公路上,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从未改变的姿势。
城市终究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街道,被看见的夜晚,被看见的咖啡屋,被看见的男女,被看见的豪宅,被看见的地下室,夸张而重复,为的是最后确认一种存在。这是城市的一面,看得见的城市里看得见的那张脸。而在“咖啡时光”之后呢?在“巫云”这个曾经和许多人一起相聚一起聊天的地方,为什么只剩下故人“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头发、牙齿、父子、指甲,这是看得见的老五,却也是看不见的老五,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又去了哪里?甚至不过两百米的巷子里,全部变成了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
时光老去了,就像老五,而回来的我开始寻找的“那个我”,却“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是的,在咖啡时光之后,在看得见的城市之后,需要的是一种记忆。以及由你和我构成,是由我们构成,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像站在对面的两个人,还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忆一起说去三岁时妻子带过的安安。父母离婚,后来母亲又去西班牙学画,小孩子总是赖着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宛若家人”的感觉,但是却只是住在那一段时光里,现在连“巫云”都已经不再,安安又会去了哪里?“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反正很酷的样子……”现在时,却早已经沉浸在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中。
和安安一样,在记忆之中曾经还有在跌跤之后具有忍受痛苦意志的母亲,还有靠一群少年仔打天下的米哥,还有为家庭女教师梦遗的伙伴,还有从鼻子里喝下牛奶从眼睛里喷出来的二人转演员“侏儒”,还有腔调、气质是不折不扣的澎湖台妹却是外省人的阿咪……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也在城市的记忆里,但是当“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到来的时候,记忆也无非是一个重复而夸张的存在,母亲“忍痛的意志终于顶不住那重摔造成的内部坏毁”;米哥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在二十多年后从“他生命里被涂抹销掉”;电影院里用手肘去顶自己家教老师的乳房和在梦中预见一架飞机的空难的伙伴,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消失了;而阿咪呢,终于离开小岛双脚踏地地生活,“如人鱼换上套装、高跟鞋伪扮混迹于人类的城市”。
而在这些记忆之中的人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外,那些记忆之中的事呢,仿佛也逃不出重复的命运:和孩子在大年初七放烟火,“我们两造各自对着河面零星射出的小朵焰星,和一旁那整群人用各式装备以镇压随时从那坏毁建物中矗立而起的恐怖火神之妖魔相比,简直微渺得滑稽。”但却烧着了那一辆水肥车,留下的是开车老夫妇的谴责;想起三十年前的一盒金箔滤嘴的彩虹烟,“像那时代的西门町,反而是一种废弃游乐园般的怀旧、老派、蛾翅粉屑坠落般的陈年纪念物了。”想起“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的温州街……可是当城市再次被看见的时候,那些记忆留下的也只有影子,影子世界入魔术,如幻术,如不存在的假象,我作为一个“种树的男人”,终于在疯狂地搬了近四十袋土和各种植物到五楼之后,终于腰椎变形错位,那“空中花园”像是对于我最好的慰藉,却也是破碎时光最后的物证,而损毁的身体或如记忆一样,再也无法回来了。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真正过去了。”夏天过去,时光过去,记忆过去,城市也走向了看不见的现实,一觉入梦的感觉,但毕竟还可以留存那一些梦境,“梦十夜”仿佛是最后留存着的片段,幻术一般,启示着曾经存在、未曾走远的记忆,于是在我家对面和平教会被拆除的时候,我梦见了“极靠近幸福的时刻”:“一种浓郁的树干木材、树叶青草味、树根湿泥的芬芳将我们包围……”于是即使在嘶嘶嘶的瓦斯外泄声传来的时候,他也梦见了和前妻在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说了一句:“别回去了吧?我们找间旅馆过夜。”梦中有美好的气味,有美人儿,而一个梦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遇到了现实,许多年后遇到了变故,许多年后遭遇了变化,许多年后是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在梦中的许多年后,她却还在设想着一种在一起的生活:“许多年后,我如果被困在一个状态中,我是假设啦,变老了或是变丑了,更可怕是变傻了。不一定啦,总之变成现在的我也不喜欢的那种人……困在那里头出不去,也许是一幢豪宅,也许是精神病院,也许是一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你会不会来找我?”
“会的,我一定会的。”这是回答,梦中应答,梦中的许多年后,永远有一个“堆满我破烂什物的书房、我的卧室,还让我觉得安心、隐秘”的旅馆,“似乎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可能的旅行,而是旅馆。”是的,每一个梦都是“幸福又虚荣的时光”,每一个梦里都可以看见美好,每一个梦都在真实中看见自己,梦是另一个世界,梦中的我们是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重复而又夸张之后,是被看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