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29 冷暖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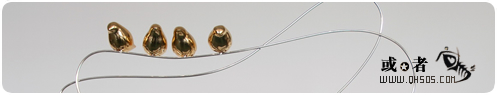
不冷也不暖,只是下了雨。不是密集而来的雨,是散漫滋润的雨,在这样一个不偏不倚、不冷不暖的日子,地上隐隐的潮湿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颓然,只是不行走,就那样从某一高处俯视下来,看见了大地,看见了人群,看见了许多易逝的雨和时间。
高处俯视,其实像是停留在树上的鸟,也不是一只,是一群,叽叽喳喳,就那样变成了聒噪者说,满嘴的符号,就像那小说中唱着的歌:“普-蒂-威特?普-蒂-威特。威特,威特。”是梧桐树上的声音,听不懂的歌声了含着一部小说的全部意义,是一个老去的人的名字?还是一个陷在五号屠场里的罪孽者的称呼,总之是破碎而令人烦躁的。这是下雨的城市里的声音,而在乡村的那株石榴树上,光秃秃的树梢上停留的也是一群,但却不说话,只是站着,很沉寂地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也不惊恐,像是和自己无关。当然,会偶尔俯视下来,那湿湿的地上还有水渍,还有不偏不倚、不冷不暖的时间。
空间被切割成城市与乡村,树上和地面,而在空间之外,时间也是被切割的,它区分了上午和下午,区分了白昼和夜晚,也区分了节日和非节日。每天的每天,都不是没有变化的晴日,也不是从一而终的雨天,而每天的每天用24小时的方式切开,“一个影像切断了我的笑容。那是一匹马。”是的,是一匹马,不是一只鸟,一群鸟,不是聒噪地在树上写着短篇小说的鸟,马的故事已经具备了敌意,在已经被切开的时间面前,冷暖自知。
然后才是一群人,坐在不冷不热的房间里,也不生火,也不取暖,就那样拿着笔记本,当然从来不记录什么,只有一个人,像鸟一样在说着话,也是俯视,也是聒噪,也是关于“普-蒂-威特?普-蒂-威特。威特,威特”的小说,所以五号屠场不是一个象征,是现实,是在不偏不倚、不冷不暖的日子上演的人间冷暖剧,这故事里从来不回避那些被切割的现实,也不会重现切断了笑容的那匹马,只是当一篇小说以讽刺的方式被写满符号的时候,还有谁能忘记那些躲在时间背后的掌掴者,他们虚荣的人生中写满了假善的笑脸,写满了追逐的名利,写满了伪国家主义的自豪和骄傲,当然也写满了不必抗争的奴性。是的,他们是一只从高处俯视的鸟,也是充满聒噪人生的一群鸟。
“我很想画一幅图呈现盲人和非盲人不相等!”那也是小说中的符号,只是盲人和非盲人的不相等早已经是现实,不在画里呈现的现实,刺痛着每一个看不见的人,也刺痛着每一个看得见的人,只是“黑暗与光明也不相等”和“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论断在救赎者眼里都是牺牲品,他们的不相等其实是相等,是毫无区别的存在,引用的话是这样的:“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所以看见和看不见,盲人和非盲人,只是一个做给自己的动作而已,而如果你是一只喜欢聒噪的鸟,你就必须闭上嘴巴;如果你是不喜欢鸣叫的鸟,那么就在飞翔的机会中寻找自由。
不是自由的高度,而是是否劳累,是否能看到地上那些行走的人,那些还在树上聒噪的鸟,或者那些被画出的马,只有他们是不需要自由的,他们只在小说里,在“普-蒂-威特?普-蒂-威特。威特,威特”的破碎声音里,在一出自己写就的人间冷暖剧里,当然,还会偶尔做一个梦,梦见山川,梦见红色,梦见左右,也梦见一匹马。
以梦为马,鼻子是唯一线索,只是在画马的大师那里,一切都开始重新命名:“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
狗变成了聒噪者,而许多的鸟从叶子上跌落,在隐隐的潮湿里埋葬自己曾经唱过的歌,以及虚荣的人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