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4《意大利式狂想曲》:宛如游戏的“傲慢与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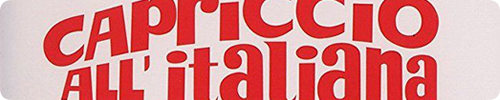
95分钟的电影,被切割成6个故事,是5个导演各自阐述“意大利式”的狂想曲,似乎是断裂的,片段的,甚至是无中心的呈现。但是当被“意大利式”这个修饰语限定,当展现的是“狂想曲”,那种戏谑、夸张的滑稽的风格便成为了一种整体:都有女人,都不涉及宗教,都是对意大利生活的讽刺——或者,正如风格整体性一样,在形式上,似乎都是追求一种游戏式的生活现实。
6个故事中有三个是非常短小的,第一个故事是马里奥·莫尼切利导演的,一群孩子正在兴致勃勃看漫画书,但是一个护育人员走过来,当她发现孩子们阅读的书时,告诉他们这些漫画书充满了暴力,里面是不道德的内容,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这些书都扔进了湖里,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故事,比如小红帽的故事,比如小汤姆大拇指的故事,接着她便开始给孩子们讲述这些道德故事,但是当她讲起小汤姆和食人魔斗争的故事时,小汤姆起先表现的恐惧感,传染到了正在听故事的孩子们,于是,这些孩子开始害怕得哭泣起来。第三个故事是“周末结束”的故事,由莫洛·鲍罗尼尼导演的故事讲目光放在意大利拥堵的交通上,男人和女人从高速公路上回来遭遇了大堵车,带着奇异墨镜的女人一路上喋喋不休说着话,她有时骂那些开车的人不遵守规则,有时候又指责政府没有尽到责任——即使警察动用了直升机监测流量,但是对于缓解堵车根本没有用处。后来在你拥我堵,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发生了摩擦,一辆车被他们撞到了路边的树上,于是女人和男人和那辆车的司机发生了争吵,最后车上的男人辛克森竟然拿出了一把扳手,狠狠敲到了那个司机的头上。事件最后以一篇报纸的报道结束:关于女人的哭泣,关于袭击者,“她问自己:为什么?”而报纸的那张照片里,女人的后面仿佛站在一个警察。第五个故事是罗西导演的,他将讽刺漫画和现实场景结合起来,欧洲国家的一位王后初访非洲某国,当她从专机上下来,拿过别人地给她的一张纸,然后开始了机场演讲,没想到,这张纸上标注的非洲国家名字错了,于是在女人不知情的演说中,在机场迎接他们的非洲国官员非常生气,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愤怒的火焰——在漫画的表达中,欧洲和非洲似乎永远没有对话的可能。
三个故事都非常短小,但是里面却传递出非常浓烈的讽刺味道,护育人员把孩子们自己读的漫画书说成是充满暴力的、不道德的东西,甚至称之为“恶魔”,是怕毒害这些纯真的孩子,但是她自己所讲述的故事却也是另一种暴力,甚至带给孩子们的是心灵的伤害,而且,她不由分说将漫画书扔掉,本身也是一种暴力。一个女人清除暴力,却也是在制造暴力,这是一种背谬,而产生这种背谬的原因就在于一种傲慢: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傲慢,旁观者对参与者的傲慢。而高速路上的故事似乎也是一种傲慢,女人在车上喋喋不休,她指责政府也指责司机,指责开慢车的司机也指责超过他们的司机,那个有着大胡子的司机开在她旁边,她讽刺他是“切·格瓦拉”,当有人试图超越她的车,于是便在摩擦中发生了事故,最后甚至用暴力的方式让自己进了警察局,报纸上报道中的那句“为什么”,从女人的口气中似乎还能感受到她傲慢的愤怒:为什么要处罚我而不是别人?欧洲女王访问非洲国家,更是一种国际间的傲慢,是所谓的文明对于野蛮的傲慢,念错了名字这种低级错误在夸张的清洁中,只能带来一声叹息。
成人对孩子,中产阶级对他人,欧洲女王对非洲国民,都呈现了一种可笑的傲慢,傲慢本身也是一种隔阂,隔阂的深层次意义是缺乏对话。同样是关于女人,最后一个故事也是莫洛·鲍罗尼尼拍摄的,片名直接取名叫“嫉妒的女人”。保罗和妻子席尔瓦娜一起去舞厅,当舞曲响起,人们开始疯狂,在拥挤的人流中,两个人被分开,而保罗几乎沉浸在这种状态中,他和其中一个女人一起跳舞,而当乐队开始演唱,保罗正和那个一起跳舞的女孩坐在一起,甚至他的手放在了女孩的肩上,这一幕正好被妻子希尔瓦娜看见,于是她大声喊叫保罗的名字,直到把保罗叫到没人的地方,这是席尔瓦娜嫉妒心的第一次表现;接着,席尔瓦娜质问他是不是以前经常来这里,是不是还和别的女孩一起跳舞?保罗解释说自己没有来过,而且反问她,这里只有50平米,不是丛林,任何人在一起难免触碰到,但是席尔瓦娜依然不罢休,她一定要保罗说出曾经和那个女人一起在这里跳舞,这是席尔瓦娜嫉妒心升级的表现;在保罗解释无用的情况下,他终于开始愤怒,说自己吃在这里住在这里,每天都在这里,然后抛下一句话:离婚!这时席尔瓦娜才开始退让,“我是个自由的女人,我没有偏见。”但是强调这句话,反而更强化了她的偏见,在还没有走出舞厅的时候,席尔瓦娜为了表现自己没有偏见,也为了挽回给保罗造成的某种伤害,她竟然指着那些女人,让保罗说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保罗也只是敷衍她,后来两个人回家,席尔瓦娜在电梯里犹豫了一下,似乎想想又不放心,回家之后她又再次问保罗,“你是不是会和每个女人上床?”保罗又开始生气,他开始管自己准备睡觉,这时席尔瓦娜爬到了窗户上,扬言如果保罗不说就从窗户跳下去,这是嫉妒心更升一级的表现,但是嫉妒的席尔瓦娜只想要保罗的一句回答,她下来之后反而让保罗从窗户上跳下去,忍无可忍的保罗骂她疯了。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得到平息,席尔瓦娜不断升级的嫉妒心在第二天达到了极值,当保罗挑好了领带和内衣,从家里出发,席尔瓦娜便开始了跟踪,最后保罗进入了一家内设服务机构的旅馆,席尔瓦娜跟了进去并打听到了保罗进入的楼层,当她一步步走上楼梯的时候,一边大声喊叫着保罗的名字,一边则从包里拿出了一把手枪,对着向上的楼梯不停地射击。
| 导演: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 莫洛·鲍罗尼尼 / 马里奥·莫尼切利 / Steno |
从看见和别的女人跳舞,到怀疑会和别的女人上床,从言语的刺激到跳窗的威胁,最后变成了跟踪,以及枪击,席尔瓦娜的嫉妒心一步步升级,而起点仅仅是在50平方米的舞厅里和别人跳了舞,可怕的嫉妒心,可怕的女人,她声称的“我没有偏见”“我只想你的忠诚”其实变成了一种借口,也变成了杀人的武器,当偏见变成嫉妒,当嫉妒变成伤害,这疯狂的背后就变成了毫无理性的“游戏”,而当席尔瓦娜开枪惊动了整幢楼的住户,保罗才从房间里出来,而此时的他下身只穿着短裤,他向大家表示:这只是我们喜欢做的一种射击游戏,然后拥着席尔瓦娜进入了房间,房间门上写着:裁缝店。原来保罗只是在这里做一条合身的裤子,但是在被嫉妒的席尔瓦娜跟踪中,似乎变成了对于偷情出轨的证据收集。
一种游戏化解了矛盾,但是保罗以后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在所谓的游戏阴影之下?席尔瓦娜是个嫉妒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和其他三个短片的傲慢一样,也是一种隔阂,也是缺乏真诚。而隔阂在观念上的表现更体现在斯特诺的第二个故事里,这里所表现的矛盾是嬉皮士为代表的年轻人和守旧甚至古板的老人之间的对立。老人带着性感的女人在路上行驶,遇到了两个年轻人拦着了他们,说要借一下汽油,老人一看他们是嬉皮士打扮,于是拒绝了,不想自己的车在半路抛锚了,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年轻人开着车上来了,相反,他们主动帮助老人,但是老人对他们依然存在偏见,于是到了目的地之后,老人拒绝他们进入自己的房子,但是女人却让他们进去吃饭。于是观念的矛盾和对立更加明显,年轻人扔掉了所谓的经典唱片,然后自己弹着吉他说:“需要音乐来创造和女人相处的心情。”之后另一大帮男女来了,他们一起吃意大利面,一起狂欢,而老人被逼到角落里,只好自己咬着手臂做出痛苦状。

《意大利式狂想曲》电影海报
这是老人在年轻人面前逐渐丧失地位的写照,也是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但老人在弱势中开始了报复,而这种报复完全是在想象中完成的:他变身为一个传播福音的教士,手里拿着圣经,遇到路边的年轻人便指出他们需要净化灵魂,于是带着他们进行忏悔,年轻人之后就消失了,报纸上的标题是:又一个嬉皮士失踪。之后老人又化身为时尚人士,又带着三个年轻人去看拥有宽大空间的车;又化身为街头妓女,勾引男人去所谓的“烧烤店”……—桩又一桩的失踪案在城市里上演,于是警方开始侦查,最后发现就是老人干的,而老头却辩解说:“我不是凶手,我只是想要惩罚他们,所以用引诱的方式剃光了他们的头……”果然那些失踪的年轻人没有被杀死,而是关在一间屋子里,当老人带着警察进去,里面的人都被剃光了头发。
年轻人是所谓的嬉皮士,但是却极易受到诱惑,这是价值观并未成行的幼稚行为,而老人在想象中化身为教士、时尚人士和妓女,混合着神圣和猥亵,而无论哪种身份,都为了解构嬉皮士的价值观,都为了一种惩罚的效用。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嬉皮士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唯一的矛盾,或者说在意大利的现实里,并不只发生价值沉沦的剃头行动,那个警察局长曾经说过:“凶手可能是任何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会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世界里成为凶手,说这句话的警察,抓住了老头,但是当老头问他:“我犯了什么罪?”警察局长却说:“我不知道罪名,但总之你犯了罪。”罪不被命名,是不是一种随意性?而后来,警察局长竟然和穿着得体的老人成了“朋友”,站在统一战线上,因为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像一个嬉皮士那样,对自己对妻子总是不屑一顾,所以守旧派的老人和无知者的警察,所以破案抓到凶手的警察和惩罚年轻人犯罪的老人,成了一个最恶意的结合体。而最后老人去了警察局长的家,对于自己的光头行动进行了另一种解释:“他们的头发总会长出来的。”然后他把那把剃头的剪刀插进了腰间空着的枪匣子里——恶搞了007,仿佛这个顽固的老人变成了守护城市的英雄。
而这一切无非是老人坐在角落里的想象而已,想象就是一种游戏,在游戏里,他成为了高高在上的人,他引诱人,他惩罚人,他不受法律制裁,他最后成了英雄——讽刺和戏谑,也在拥有不同观念的人际间成为了“傲慢与偏见”。而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导演的故事,似乎更具有寓言意义,在舞台上上演的是《奥德赛》,一切都是按照故事的情节在表演,奥德赛因为对妻子的嫉妒,最后怀疑她,而这一切都是那个奥德赛视为最好的朋友的伊阿古设下的计谋。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导演这个故事并不只是演绎《奥德赛》的故事,当电影拍摄一个戏剧,这是一种戏中戏的结构,而这个戏中戏在形式上是解构意义的,舞台上表演的人都是真人,但是却像木偶一样被拉着线,这是对于人的一种物化,人在这里没有感情,没有想象,没有认识,他们只是在被控制的提线中成为一个木偶式的道具,而在演出过程中,提线人会时不时插进来讲话,打破了戏剧结构本身的自足性,使得这个关于嫉妒的故事,也变成了一种现实。
最后因为嫉妒心,奥德赛和伊阿古都受到了惩罚,而他们在这个结局里更像是一个物,在“垃圾收集人”的歌声中,他们变成了垃圾被丢进了垃圾车,最终被倒在成堆的垃圾里,于是在两个人躺着看天的时候,他们望见了天上的白云,于是奥德赛问:“什么是云?”伊阿古说:“云就是凄美的创造。”沦为垃圾而看见了云,这是一种希望?凄美的创造其实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无法改变嫉妒和疯狂的爱,所以最后他们真正,和其他电影片段里的人一样,成为“傲慢和偏见”的牺牲品,也在这“意大利式狂想曲”里陷入无法自拔的游戏陷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