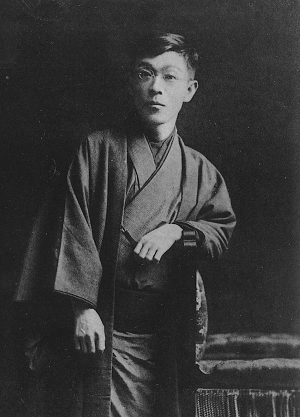2026-02-10《歌行灯》:影子却出奇地浓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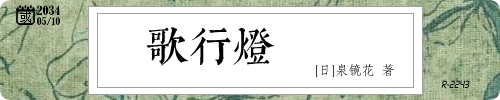
话分两头。那个卖唱的还在乌冬面馆里继续讲述着自己的身世。
——《歌行灯·二十一章》
一头是在凑屋,另一头是在乌冬面馆;一头是艺伎三重讲述自己被继母卖掉之后的飘泊故事,另一头是卖唱的对按摩师讲述自己“曾经杀了一个你的同行”。一头就在另一头的隔壁,在各自的讲述中,在他人的听说中,分开了彼此,“话分两头”就是把故事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展开叙事,而和中国古典小说本身就由说书人的口气讲述故事不同,泉镜花是将讲述者纳入到故事之中,他们自然构成了故事的人物,而小说结构便成为了“故事之故事”的嵌套形式。
讲述者既在故事之外也在故事之内,这是双重的身份,“一个声音碎碎念着《东海道徒步旅行记》第五编上卷开头的那几句话,还是霜月十一月十日那天晚上八点的事。”《歌行灯》一开场就由一种特殊方式构建了小说的叙述结构:列车抵达桑名站,月台上站着的是年纪已六旬但心里还是小伙子的弥次郎兵卫,同行的则是七十来岁的捻平,弥次朗兵卫读着《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上面的那段话是:“热田神宫里的顶粱柱就像爱知县名产宫重大根一样笔直。”之后是:“弥次朗兵卫和喜多八庆幸着往来两边渡口的渡口船平安着岸到达桑名……”一样是弥次朗兵卫,一样是桑名站,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和现实中发生的情况仿佛同步展开,甚至弥次朗兵卫还按照书中的记载要让载自己和捻平的车夫说着同样的话,“这里不说上一句好哟好哟,就对不上《徒步旅行记》的戏啦。”而住进凑屋的时候,他也表示,“如果有喜多八一起跟着来的话,那可就真的跟《徒步旅行记》的情节一样了。”
弥次朗兵卫进入了故事之中,他成为了《东海道徒步旅行记》里的人物,这是一种活在文本中的渴望,泉镜花如此开场,其实就是凸显了讲述者的作用:他将读者带入到文本之中,自己既在文本之内,又在文本之外,既参与到故事之中,又挣脱在故事之外,这显然已经不是“话分两头”这种结构意义甚至形式意义的叙事方式,而是把现实和文本杂糅在一起,起到的效果是:什么是现实真实发生的?什么又是虚构创作的?现实的一头是凑屋的故事,等到艺伎三重出现,当她讲述自己身世,讲述者便真正出场了,“三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泪水就像被人情的温暖融化的寒冰夺眶而出。”爸爸去世之后被继母卖到了鸟羽,在鸟羽被人丢到了海边悬崖,之后被人绑起来沉到海里又拉起来,还好山田新町的大姐花钱将她赎了出来,后来净身向曲艺之神许愿,又安排学了技艺,“我在那片昏暗的、能听到吹过鼓岳松林的风声和五十铃川的流水声的杂树林里向他学习技艺。一招一式,手眼身法,他从背后抱着我,我的身体就自动跳起舞来。”
三重说:“我记得这些。”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三重讲述的是自己经历的事,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切的,它甚至以如此屈辱的方式刻进了自己的骨骼和血液,但是三重“记得这些”也意味着可能不记得这些,身世于是在讲述中变得真假难辨,“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梦境还是现实。”对于一个受到伤害的艺伎来说,那种痛苦、那种屈辱,自然选择了忘记,沉到海里又拉上来,也是毁掉了记忆的真切感,所以它就是一场不该发生的噩梦,它就不应该是人世真实发生的故事。但这只是从三重的遭遇来说,对于小说的叙事来说,当三重既是故事的参与者、体验者,又是叙述者,她当然站在梦境和现实的交界处,而作为故事真正的叙述者,她并不是真正在故事之中,她游离其中,所以叙述并不是客观地再现,而是掺入了主观的感受和想象,变成了梦境之一种,甚至他以另一种方式故意脱离了现实,形成了一种传说。
| 编号:C41·2260119·2419 |
“唉,你在这里也受到这般悲惨的对待。”弥次朗兵卫如此安慰三重,然后将她的遭遇搁在一旁,“一个年轻姑娘,非妖非魔,却表演出如此惊人的舞姿,真的非常吃惊,这才叫停了你的表演,真不好意思。”弥次朗兵卫和捻平还教了她一段真正的能剧表演。这是从现实转向艺术,也意味着从真实转向了浪漫——在这里讲述者开始退场。但是回到艺术世界,也揭开了这个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弥次朗兵卫就是能剧演员、本派第一名角恩地源三郎,而那个叫捻平的老人是自称“雪叟”的是边见秀之进,“演奏小鼓的技艺全国上下无人能及。”真实身份被揭开,他们也从文本的《徒步旅行记》中出来,不再一板一眼再现里面的记述,不再跟着书中的讲述者,出来就是回到更真实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却又是让三重忘掉现实苦难进入的艺术世界,也由此,泉镜花的小说结构完成了从文本退场、从现实退场进入艺术的转向,而艺术就成为了没有叙述者的浪漫、唯美和幽玄世界。
这是这一头的转向,在另一头的乌冬面馆里,卖唱的在火盆里取暖,喝着温热的酒,第一次享受按摩,当他发出感慨,“这世间竟然有这么暖的火,让人想起家乡,反而觉得更冷了。”他也成为了讲述者,让故事进入到了既像梦境又像现实的身世之中,“我喝醉了,还以为自己又看到了幻影。”他曾是身穿条纹龙外套的大少爷,那一次跟随着舅舅去参拜伊势神宫,听到有一个叫宗三的按摩大师,高傲自大,“首先光是‘宗山’这个名字我就看不过,接着‘那帮家伙’这个说法也让人窝火,还有‘三个小老婆’,更叫人怒火冲天。”于是他趁舅舅熟睡去找了宗三大师,经过一番羞辱,宗三竟寻了短见,临死时写下的遗书是:“我诅咒你们流派七代!”按照卖唱的说法,宗三最后死在了鼓岳山麓,“听说他吊死在杂树林的树上,狂风吹得尸体摇来摇去,直到早晨风小了,还在不停地摇着。”很多人为他叫好,人为他将宗三这样厉害的人闭上绝路,唱功一定冠绝天下,而舅舅听说此事之后无法容忍他的冒失,最后将他逐出了家门,而舅舅认为宗三“是一个懂得廉耻应当尊敬之人”,所以还去葬礼上送他最后一程,而卖唱的从此一无所有,他在全国流浪成为了卖唱艺人。
卖唱的讲述自己的身世,他的身份就是讲述者,在故事之外他是事件的参与者,而在故事之外他又是一个旁观者,这个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就是现实有多少是梦幻?而在卖唱的讲述身世的时候,真相也被揭开了,他口中的舅舅就是恩地源三郎,或者说他就是恩地源三郎的养子,他的名字是恩地喜多八——而恩地源三郎就在“话分两头”的另一头,这个真相的揭示让“话分两头”的分支终于走到了一起:当恩地源三郎教授三重表演能剧,当雪叟击打出鼓声的韵律,讲述身世的恩地喜多八也听到了传来的声音,“雪叟在击鼓!他在击鼓啊!”而这里另一个真相也真正浮现出来,三重不是别人,正是喜多八的女儿,当喜多八听到雪叟的鼓声,是不是也看到了女儿的舞蹈?那一刻他是不是感受到了一生的罪孽?艺术能消融这一切吗?
就在这时,从凑屋门口传来一阵清朗的歌声。歌声犹如白虹贯日,直贯三重的心头。夜深了。小镇沉浸在寒冷之中。当虚空中传来若隐若现的笛声的时候,恩地喜多八正一个人躲在湊屋屋檐下歌唱。他的身形在黑暗之中几不可见,影子却出奇地浓郁。月亮高高地在天上照着凑屋的屋檐,在他脸上投下一块扇形的光斑。正仿佛小厅里的舞扇,一内一外,一正一反,契合无间。
|
| 泉镜花:一正一反,契合无间 |
这是泉镜花在这部小说中最唯美的部分,歌声如白虹贯日,笛声若隐若现,身影在黑暗中翩跹,这是艺术的世界,这是浪漫的梦境,身形化作影子,“影子却出奇地浓郁”,泉镜花就是在一种“影子”叙事中让故事在现实和梦境中交错,在讲述者内和外的身份中演绎,“一内一外,一正一反,契合无间。”而实际上,《歌行灯》的结构被后来者津津乐道,在于它的写作手法上更接近于日本谣曲,泉镜花家将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和三年前的往事交叉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三重的身世还是卖唱的身世,都是按照谣曲中“序、破、急”的固定层次发展的:序段酝酿气氛,然后通过破段介绍情况,最后在急段中,让故事在迷离恍惚间进入高潮,当高潮到来,现实退场,苦难退场,悲剧退场,而讲述者则完全退场——它只以最艺术的呈现方式让故事戛然而止。
同样,《草迷宫》作为泉镜花体量更大的小说,依然是讲述者在讲述故事,“人们习惯将三浦半岛的大崩海角称作魔境。”“魔境”就定义了这是一个更幽玄、更诡异的叙事空间:这里夏天海水浴旺季的时候死人最多,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此疗养,一次听到悬崖上传来声音:“那你就去孝敬父母——”少年病情从此加重……但是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茶馆的老人家对来这里云游的小次郎法师讲述的那些故事:总说那些东西就是“石头”的疯子嘉吉,让老人家想起自己和老头子的生活,他们相依为命,内心充满空虚和不安,将这里的“产子石”给游客才能带来一丝安慰;嘉吉被人看不起,还被人绑在船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拿阳伞的女人救了他,这个女人是明神大人的侍女,她给了嘉吉一颗神秘的翠绿色珠子;侍女总是唱着那首悲伤而凄凉的歌,“这是通往秋谷宅子的小路啊。无论谁来都不让过。”这首童谣背后则是秋谷宅子里发生的怪事;“前前后后,那个黑漆大门里,一共出了五条人命。”夜晚总是出现的萤火虫,人们传言就是美女簪子上的绿光宝石……
老人家对法师讲出了这些故事,它们或者发生或者没有发生,或者是现实或者是传说,都是讲述者在讲述,讲述制造了故事的影子,而且在《草迷宫》里,这个影子更是“出奇地浓郁”,“算我在这里求您,能不能请您去黑漆大门里的别墅,诵经超度呢?……”老人家最后这样祈求法师,也从这里开始,故事从讲述变成了亲历,但是和亲历一样,泉镜花以更诡异和幽玄的方式呈现故事,它们是“苦虫”和宰八说到的猫的尸体,绿汁发的谁,消失的菖蒲,还有“苦虫”找来的竹枪,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满是阴谋论:
一在家主鹤谷大人的这所别墅,发生的各种蹊跷事越来越多,仁右卫门心里觉得必须要认真想想是怎么回事了。他话也不说,闷头想了三天两夜,仿佛忽然想通了些什么。真是一场处心积虑导演的阴谋啊。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骗局。他们早有预谋,要把这座宅子弄成一座鬼屋。放着不管的话,就干脆变成了狐狸狼狈的巢穴,就算不这样,也会变成乞丐和流浪汉的藏身所,有人在里面生火就更危险了。这种屋子,就算倒贴钱也不会有人来住。所以,一定是有人想要等着这座宅子彻底空置下来,拔掉腐烂的柱子,揭掉屋顶的瓦片,将其据为已有。没错!没错!一定是明神大神托梦,自己才会看透这场阴谋。仔细一想,最近住在里面的那个流浪书生虽然一脸善相,但像极了小说里的自来也,简直就是盗贼头子;那个傍晚过来的和尚也一定是同伙儿;还有那个开茶屋的老太太也很可疑;那个带着书生来的宰八也肯定被他们同化了;怪不得这次闹鬼事件都跟他们几个有关;等等,装疯卖傻那么简单,嘉吉那个家伙肯定也被他们收买了——肯定是收了他们一坛酒。
面对“黑漆大门”里面发生的怪事,混合着老人家的讲述,所谓诵经超度的法师也在如梦如幻之中,“我是个连法号都没有的僧人。我曾经做了错事,为了赎罪才自行剃发出家。”到底赎什么罪,泉镜花没有写明;黑漆大门里发生的一切是不是罪孽,泉镜花也没有最后回答,故事就这样在真实和梦幻中发生,分不清什么是传说什么是亲见。但是和《歌行灯》一样,最后依然回归到超越现实的艺术之中:少年住客叶越明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手鞠,“我朝着天空中的云朵前行,遇到海就渡海,遇到山就翻山,在沿途村镇借宿。我遍历诸国,其实,是想要把某首手鞠歌……”而手鞠就是曾经母亲留给他的,这手鞠既是梦境也是现实,既让人悲伤又使人怀旧,“那段让人沉醉的手鞠歌,既是梦境,又似现实,又或是幻境……感觉仿佛眼睛看得清晰,但却无法用语言讲清——还有,既温柔,又怀旧,悲伤的,充满人情温暖的,饱含了爱情的,充盈的,还有澄澈,清凉,但又让人打上一个寒战,心中充满苦涩。”他追寻手鞠之歌而来,就是追寻母亲之爱,追寻清香之情,就是追寻遗失的艺术,“一代一代越来越差,没人能唱着歌一直拍到最后。”
没有阴谋论,只有情感的寄托,只有艺术的追寻,这是不是最好的救赎?而在谜底揭晓的那一刻,“草迷宫”在泉镜花的描写下又变得似真似幻:他被头上的声音吓了一跳,看到了漏雨的水渍描绘出的妖怪摸样;巨大的身影从门框里探了出来,穿着白色的麻料单衣服,这个“无处不在的恶左卫门”自称是妖怪;接着是脸上长着两只闪着灿烂银光的眼睛的女子,嘴里的牙齿比针尖还要尖锐;她说自己是叶越明母亲的知己,也知道叶越明此行的目的,说起了母子之间的神情,“母亲于心不忍,终于打破了就连思念儿子都会被认为是恋情的天条规则,在楼阁的白玉栏杆边,拽过桂树的树枝,顺着树枝来到了宫殿外面。”在女子拍手鞠和叶越明告别的时候,法师更是看到了梦境中的一切,“那个身形巨大的魔物的袖子,幻化成船帆。女人躲在帷帐对面。”
是梦境,是影子,是法师看见的真实?还是进入的梦幻?泉镜花没有提供答案,而这也正是讲述者双重身份讲述的结果:讲述者不是老人家,不是法师,不是少年住客,不是苦虫,他们都是故事的一部分,真正的讲述者就是泉镜花,一只脚在故事里一只脚在故事外,既是自己建造了迷宫,又在无法离开的迷宫里,“刚想到这里,一阵风就从树林中吹了过来,树叶变成绿色的急流……天上一丝云彩,啊啊,一丝云彩。”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36]
顾后:疑惑于您最后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