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7《这不可能发生》:毕竟我们有幽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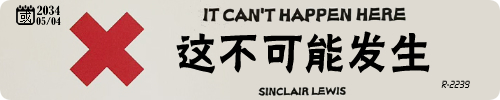
其实不管是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暹罗,还是格陵兰,只要能给他宠爱的那些青年画家一个机会,画出他在异国奇境中英勇挺立的模样,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
——《第三十七章》
腰封上赫然印着“成功预言今日美国的奇书 特朗普当选后卖到脱销”,当白底的封面上写着大大的、红色的“×”,当“这不可能发生”的书名如此醒目,“×”和“这不可能”的双重否定并没有起到警示的意义,在这部小说出版90年后的今天,它的确成为了一种预言:对特朗普政府的预言,对美国民主的预言,对“格陵兰”的预言。
在翻开这本书的一个月前,预言成真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实:2026年1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导演了委内瑞拉“拘捕”总统事件之后,再次引发国家社会热议,他宣称美国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格陵兰岛;之后的14日他再次表示,格陵兰岛对美国“金穹”系统至关重要;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丹麦的抗议之下,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将不会无力夺取格陵兰岛;两天之后丹麦国防军在格陵兰岛再设立临时军事区;1月31日,特朗普终于同意在格陵兰岛的谈判达成一致。对于格陵兰岛的态度,特朗普并非是2026年开年之后的“突发奇想”,一年前的1月7日,特朗普就表示,处于对美国“经济安全考虑”,他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的可能性,他还声称,格陵兰岛居民可以通过投票实现该岛独立或加入美国,此番发言当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哗然,而那时的特朗普还是一个后候任总统,这一言论发表半个月之后的1月20日他才正式宣誓就任第47任美国总统,而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对格陵兰岛的态度依然强硬:3月10日特朗普再次提出希望格陵兰岛并入美国;12月22日,特朗普强硬表态,美国“必须得到格陵兰岛”……2026年开年的言论只不过是他格陵兰美梦的一次次延续。
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国际争端,90年前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当然是对这一现实的最好预言:除了对墨西哥开战的渴望之外,小说中的美国总统萨拉森还希望拥有埃塞俄比亚、暹罗和格陵兰,发动战争就是为了获得领土,“于他而言,战争既能让国内的不满分子转移怒气,又能让自己的英雄肖像永世流传。”在小说中,萨拉森曾经是前总统文雷普的保镖、代笔人、媒体公关和经济顾问,当他用武力推翻文雷普的统治坐上了总统宝座,已经将美国带入了“后独裁时代”,他的野心比文雷普有过之而无不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独裁的魔爪从国内伸向了国际,而这也成为刘易斯对美国政府所谓民主外衣的批判。但是当90年前的小说预言了现实,当独裁统治毁灭了民主,刘易斯真的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警示?
“这事不可能发生”这一否定性的断言来自塔斯布罗,那是扶轮社晚宴结束后,塔斯布罗家的私人酒吧里聚了一群人,主人塔斯布罗、多里默斯·杰瑟普、磨坊主梅达里·科尔、学监埃米尔·司陶白、本地最有分量的银行家罗斯科·康克林·克劳利,还有一位出人意料的宾客——塔斯布罗家的牧师,圣公会的福尔克先生,当杰瑟普预言“等着看吧,等巴兹·文雷普真正接管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法西斯独裁”,塔斯布罗插话道:“也许让个强人来掌权确实不赖,但——这事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塔斯布罗的断言在小说中反复回响,最终成为一个残酷的反讽,刘易斯让这句话从比尤拉堡最有分量的工业家口中说出,绝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细节揭示了美国社会中那些自以为免疫于历史病毒的阶层,他们相信美国的“例外论”,相信大洋两岸的地理隔绝,相信某种神秘的民族性格能够抵御极权主义的侵袭。这种信念的根基,正如小说后来所揭示的,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傲慢:“毕竟我们有幽默感”。
当文雷普的独裁统治初现端倪时,这种“幽默感”确实发挥了作用:米老兵逮捕政治犯时还会说声“真不好意思”,犯人也乐呵呵地跟狱警开玩笑,“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清爽的空气里挨鞭子,跟在普鲁士毒雾弥漫的牢房里戴手铐,一样疼。”刘易斯以冷峻的笔触戳破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泡沫,痛苦不会因为施暴者的口音或气候的宜人程度而减轻,暴政的本质从不因地域而改变。然而,刘易斯的讽刺远不止于文化层面的批判,他更深层的关切在于:当制度遭遇个人权力的系统性破坏时,那些本应起到制衡作用的社会机制为何纷纷失效?文雷普的崛起并非依赖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是精准地利用了民主制度本身的开放性。他的“十五点纲领”混杂了民粹主义的财富承诺、对工会组织的控制、宗教话语的挪用,以及对“外国人”的排斥。这些元素并非刘易斯的凭空捏造,而是1930年代美国政治光谱中真实存在的思潮。而纲领的第四条赫然写着:“我们坚信,美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唯有在全能上帝(我们向他致以崇敬)之下方能成立。”
| 编号:C54·2260103·2414 |
文雷普的天才在于“他从不等机会”,早在被提名前就开始结党营私;更在于他“一边热情洋溢地鼓吹‘只要给我投票就能发财’,一边义正词严地谴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种双重话语的策略,使得反对者陷入认知的困境:当你指控他是法西斯时,他已经抢先占据了反法西斯的道德高地——小说细致描写了文雷普的“蜕变”:“从露天广场喇叭前兜售假药的江湖骗子,摇身变为聚光灯下、讲台之后,拿麦克风兜售假经济学的‘大人物’。”他“一脚踏出飞机舱门、一头钻进轿车;他为桥梁揭幕;他在南方与人共吃玉米饼和咸肉,在北方啃麸皮、喝蛤蜊浓汤;他向美国军团、自由联盟、基督教青年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糜鹿兄弟会、酒吧与侍者工会、禁酒联盟,甚至阿富汗传教会发表演讲;他亲吻百岁老太太、与女士们握手——顺序千万不能颠倒。”而在文雷普就任总统后,他做出了一连串动作:将米老兵合法化为“官方辅助部队”;要求总统获得对立法与行政的完全控制权;在国会否决后宣布戒严并逮捕议员——在程序上竟都显得“合法”;当国会两院以联合决议形式,否决了该提案,文雷普总统宣布国家在“当前危机”下进入戒严状态;随即,一百多名国会议员被接到总统直接命令的米老兵逮捕,那些敢于抗拒的议员被讽刺性地以煽动暴乱罪起诉;最高法院最开明的四位大法官辞职,这种司法独立的溃败并非通过暴力革命完成,而是通过日常的、几乎体面的政治操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雷普的第三道命令是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宣布米老兵被正式认可为正规军的官方辅助部队,虽无薪,却有合法编制,只听命于自己的军官、文雷普本人,以及最高统帅萨拉森,同时下令全国政府军火库立即为他们发放步枪、刺刀、自动手枪和机枪。这支私人武装的合法化,标志着暴力机器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而当企业党发动全国范围的突袭时,七万名精挑细选的米老兵联合地方与州警察,一举逮捕了全国所有已知或稍有嫌疑的罪犯,然后进行军法审判:“十分之一被当场枪决,十分之四被判刑入狱,十分之三被认定无罪释放……还有十分之二直接被编入米老兵,担任稽查员。”当有人抗议称至少六成被捕者是无辜的,文雷普就用一句“制止犯罪的唯一办法,就是制止犯罪!”的英勇发言,完美回应了所有质疑。
总统的权力破坏了制度体系,但是刘易斯揭示的却是独裁统治的一个真正悖论:它并非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拥护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与共谋之上。当多里默斯在报社试图刊登那篇批判社论时,他遭遇的不是政府的直接审查,而是排字房工人的集体拒绝,丹叫道:“我可不干!你这篇社论简直就是响尾蛇的毒液!你想被关进大牢、清晨就被枪毙是你自己的事。但我们排字房开了个会,大家都说,见鬼了,我们可不想跟着陪葬!”朱利安满脸担心地说:“天哪,我真希望你有胆子把它印出来,可又真希望你别这么干!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审查,比自上而下的禁令更为致命,因为它消解了抵抗的道德基础。另外,多里默斯的妻子埃玛的担忧极具代表性,她并非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而是被“你在牢房里肯定连干净的内裤都没有”这样的具体恐惧所俘获,这种对日常生活崩解的焦虑,最终压过了对抽象正义的追求。刘易斯在此展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极权主义的胜利不在于说服所有人,而在于让足够多的人相信,反抗的成本已经高到不可承受。
|
| 辛克莱·刘易斯:我不相信私刑真能对抗暴政 |
但刘易斯并未将责任完全推卸给普通民众,他通过多里默斯·杰瑟普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探索了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道德位置。杰瑟普绝非完美的英雄:他“愤世嫉俗”,对美国历史上的革命也开始“持保留态度”,甚至暗自怀疑“美国自己的两场伟大革命”,即1776年反抗英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内战,“是否也值得重新审视”。这种思想的摇摆,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犹疑,恰恰构成了刘易斯所理解的“真实的人”,而当那个将无数囚犯送进集中营的米老兵头目沙德·勒杜自己也被关进特里农集中营时,多里默斯劝那些密谋干掉他的人冷静点,卡尔·帕斯卡尔火冒三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当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你还真尊重沙德·勒杜这坨野猪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多里默斯的回答是:“我不相信私刑真能对抗暴政。暴君的血,只会浇灌出更多屠杀——”
杰瑟普最终选择发表那篇社论,并非出于某种顿悟或皈依,而更多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不这样做就无法面对自己”的承认,“在文雷普及其企业党的暴政之下,任何诚实的反对者只能面临被屠杀、被铲除的命运。”但发表社论的代价迅速降临,多里默斯毫无自主意识地被四个持枪的米老兵押着,从总统街走上榆树街,往法院和县监狱去。在牢房中,多里默斯开始怀疑一切:“这个独裁政权的暴政,并不是大资本的错,也不是那些干脏活的煽动者的错。是多里默斯·杰瑟普的错!是所有有良心、体面却思想懒惰的杰瑟普的错。是我们让煽动者钻了空子,却没有及时、猛烈地抗议。”这种自我控诉既是道德觉醒,也是刘易斯对读者的召唤,暴政的每一步推进,都需要无数“体面人”的默许与配合。
刘易斯对“后独裁时代”的描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主题。文雷普的流亡和萨拉森的崛起表明,独裁者的个人命运并不能自动带来制度的复原,萨拉森曾经是文雷普的“保镖、代笔人、媒体公关和经济顾问”,他的上台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延续而非断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萨拉森对战争的渴望从国内的压迫逻辑延伸至国际领域,当他“夜夜笙歌,举办酒神仪式”时,刘易斯揭示了独裁者如何将个人虚荣与国家战略混为一谈。而这也成为刘易斯对帝国主义与独裁统治内在关联的深刻揭示。然而,刘易斯的预言性视野也暴露了其局限性。小说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包括秘密出版、跨境联络、武装起义的“新地下铁路”抵抗活动,在叙事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地下出版的影响范围极为有限,多里默斯最终不得不逃亡加拿大,“行李已经收拾好了。他只带了洗漱用品、一套换洗衣物,以及《西方的没落》第一卷”。而小说中的美国最终通过军事政变(曼纽尔·昆将军的起义)而非民主程序摆脱独裁,这一解决路径的模糊性,使得小说的政治思考停留于警示而非建设。
回到那个核心问题:刘易斯究竟在警示什么?腰封上的宣传语将其定位为“成功预言今日美国的奇书”,但这一标签可能简化了小说的复杂性,刘易斯在1938年的话剧首演中警告的是“法西斯主义在美国蔓延的可能”,而非美国民主制度的必然崩溃。他笔下的文雷普政权,在诸多细节上更接近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变体,而非某种土生土长的政治形态。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对比是“美国式”与“欧洲式”的独裁,恰恰表明,刘易斯所忧虑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病毒,而非美国特有的制度缺陷。小说中焚书的情节尤为典型:斯旺主导,皮士礼在旁叽叽喳喳配合,全面禁止梭罗、爱默生、惠蒂尔、惠特曼、马克·吐温、豪威尔斯,以及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一书出版、销售与持有,多里默斯一周前已悄悄转移了《资本论》、凡勃伦著作、所有俄国小说,连萨姆纳的《民俗论》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也不敢留下。这种对思想控制的描写,明显带有欧洲极权主义的印记。
在这个意义上,《这不可能发生》首先是一部关于“可能性”的小说:它追问的不是“美国会不会变成法西斯”,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任何民主社会都可能滑向独裁”。刘易斯通过想象构建了美国式的独裁噩梦,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对于杰瑟普这样的人物,他寄予了某种希望,“因为像多里默斯·杰瑟普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页,紧随其后的描写是多里默斯仍在逃亡,“迎着黎明曙光前行”,而前方是“北方密林深处一间隐蔽的小屋”,那里“几个沉默的男人正等候着自由的消息”,这个开放式的结尾,既是对个体韧性的信念,也是对集体未来的不确定。
刘易斯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当“这不可能发生”的自信遭遇历史的反讽,我们能否在笑声停止之前,辨认出暴政的轮廓?毕竟,刘易斯所嘲笑的那种“幽默感”,在今日的美国依然盛行——只是这一次,没有人能够确信,疼痛是否真的会不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