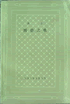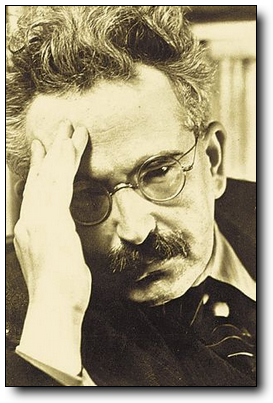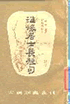|
编号:S44·1951212·0222 |
| 作者:(台)陈黎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
| 定价:4.65元 |
| 页数:232页 |
陈黎的断句突然之间让诗意嘎然而止,又忽然在延续着什么。在当代台湾诗坛,陈黎不算对语言结构得最彻底的,他对句子的断裂情有独钟,对拉丁美洲的诗歌翻译使他的诗带有某些异域的风采。陈黎对比喻地运用比象征更得心应手,比如将海比作荡妇,脑袋比作胶卷,虽然其中有着淡淡的忧郁与思考,但情绪总是乐观的。
《阴影的河流》:我们都是虚伪的两脚动物
墙壁有耳
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
—《墙》
墙壁应该是沉默的记录者,一面立起的墙,一面厚实的墙,一面无声的墙,它从来不说话。但是沉默是用来打破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给它铁钉,用来纪念那些缺席的帽子、钥匙和大衣,我们给它缝隙,用来容纳那些爱情、流言和家丑,当一面墙上被挂上钟、镜,它其实被“我们”复活了时间,那些失去了日子的阴影,那些梦的唇印,似乎都显露出来,似乎“我们”制造了一面墙,似乎“我们”给了墙一种见证的意义。
墙壁应该是沉默的记录者,但是当“我们”出现,还不足以让墙真正记录时间,而是在“我们”之外,有他者存在,因为“隔墙有耳”,耳朵在墙上,其实那一面厚实的墙留下了缝隙,它会听到爱情、流言和家丑,它会在时间的阴影里,在梦的唇印中说话,于是沉默被打破,一面墙其实在制造了隔阂的同时,也破坏了封闭。墙上会有谁的耳朵?在没有安全,不再自我的世界里,对话变成了偷听,隔离变成了猜忌,一种现代病从来没有消失–我们和他者制造了墙,墙也容纳了我们和耳朵之间无休止的纷扰。
一面墙会承载多大的重量?一面墙能忍受多久的寂静?一面墙能记录多少的沉默?一面墙又能挥霍多久的时间?一面墙也像是一本书,也像是一首诗:这是最早阅读陈黎的一首诗,90年代末或者更远,是在一本杂志上,诗歌里的那种孤寂和不安传递出来,竟有些悲哀。而现在一本诗集放在面前,真的变成了一堵墙:诗集早已经泛黄,也是90年代末购买的书一直放在角落里,甚至遗忘。它就是沉默的存在,但当在时间的流逝中重新打开,当以整体的方式阅读陈黎,是不是这本诗集里的情绪也像是一堵墙:是沉默的记录者,却又在“隔壁有耳”的猜忌中变成了对于自身存在的担忧?
一开始是清新的,是充满生活情趣的,那一辑《庙前》仿佛真的是没有一堵墙的隔阂,那里的秋,“女子们都垂着长发/牧歌一般的情绪”,那里阴沉的八月十五,“月亮答应把脸也蒙在被后/睡觉”,那里的访客,总是“把濡湿的脚印带上五楼”,那时的我既是看到黑夜,也能“听到一朵花的开放”,而在充满故事的客厅里,可以看“一集瓷质的麻雀/目不转睛地看着墙上”,然后“成群的蚂蚁,爬一座七彩印刷的/阿尔卑斯”,在客厅里踏青,听马桶里的湍湍急流,鱼游在水箱里,小猫小狗小弟小妹跳跃乎沙发椅上,而小朋友在阳台远足,“床上,嗯大人们运动”。在可爱的生活里,既是有着充溢着欲望的表达,也是在内心世界里构筑了一种单纯的美,对于海的影响,是一个“荡妇”,在一张巨床上,“整日/与她的浪人/把偌大一张滚白的水蓝被子/挤/来/挤/去”。
但是美好而单纯的生活似乎只在墙的这一边,墙的那一边呢?陈黎一开始并不是想用墙来阻隔,而是在墙竖立起来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有耳的故事里所有东西都不再沉默:“我们给它厚度/我们给它重量/我们给它寂静”,我们只是“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在脆弱的世界里,身为情妇的那把松弛的吉他,开始紧张起来,一触即发的姿色不是为了获得愉悦,也不是和大海一样,在“滚白的水蓝被子/挤/来/挤/去”,而是当演奏开始之后,“突然/断了 弦(《情妇》)”突然断了弦,那种充满情趣的生活被一下子打破,这是一种启示,仿佛墙不再隔离浪漫和现实,有耳的世界被打开,从此整个世界都变成在脆弱中“巨大地存在”。
好望角饭店的那个流浪汉,只是靠在“一张后肢悬空的板凳睡成滑梯的/角度”里,滑进了“不用付钱的/天/堂”,而法国妓女静坐在教堂,却被逐了出去,她们向慈悲的圣母所祷告的仅仅是,“我们渴望在自己的床上翻身,仅仅/一个人,不脱掉/我们的衣服”,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干净的”。而作为摄影师,“替花花公子拍照”时,从西贡玫瑰到末开苞的雏菊,见证了花花少爷们“透过催泪枪用滋养的尿水击射罪恶的花朵”,于是,拍照而洗出来的,是一张黑白的风景——月色是白的,大地是黑色的,黑与白构成了男人和女人、占有和被侵、玩弄和受伤,以及肉体和精神的对立存在,“如何说人生如梦,梦如戏,而朦胧的夜是最好的舞台”?
一根弦突然就断了,那些美妙清脆的声音变没有了,一堵墙倒了,那些封闭而享受的生活趣味也没有了,在面对“依靠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的现实里,陈黎大约是体会到了现代人的“荒原感”,引用T.S.艾略特的诗写成的《旱道》完全是一个缺水的寓言,水色的天空里,是一只“火红的瞳孔”,而且要去榨“空汽水瓶里的一滴水珠”,水在哪里?几条金鱼跳出了浴缸,走廊上的女郎想要用冰激凌解渴,小孩子找不到洗手间,而我摸出的一枚镍币买了一杯“自动贩卖的桔子水”——水很珍贵,水很稀少,最后水却在异化:“水色底天空用半只橙黄的瞳孔去榨空汽水瓶的/玻璃/抬头,我的视线吮着墙壁上大大一幅可口可乐/的广告:/凝结的海面新漆着一尊红泳装大奶子的模特儿/不拿瓶子的一只手,捞起/浪花”……
都市生活里怎么会没有水?它们是桔子水,它们是可口可乐,它们在自动贩卖机上,它们在巨大广告牌上,在这里,从生活到寓言,一切都被置换,当初那个大海一样的荡妇,现在变成了“红泳装大奶子的模特儿”——大海是可以容纳的存在,是自由和纵情的象征,而都市广告牌上的模特儿变成了一种制约,一种隔阂,一种如墙的巨大存在,所以在这样的置换中,“我的陶碗/空空。空空”。一种包容了一切的都市病症,在艾略特的“荒原”情结中变成了现代人无法逃离的悲剧,而借着“李尔王”的意象,陈黎更是构筑了一个消解神话消解英雄消解崇高的诗意世界,那是自逐的王,那是激动的王,那是预言了现代生活的王,“你竟说/我们都是虚伪的两脚动物/你开始脱下裤子,雷声隆隆/我看不出你们的差别”,脱掉了裤子还是王?只是在异国的泥土里,在群起的歌舞中,“嘴巴送给广告商鼻子送给化妆品公司眼睛送给歌舞团/生殖器送给美容院/如果怕冷——王啊/就真的让尿,像熔了的铅一般地烫着自己(《李尔王》)”
这不是历史的虚构,这是现实的沉默,广告商、化妆品公司、歌舞团、美容院组成了现代意象,它以最无情的解构方式让一个王脱下了保持尊严的裤子,而在李尔王的口中,我们不都是不穿裤子“虚伪的两脚动物”?“庙前”的仪式已远,生活的情趣已被淹没,所以从那个“虚伪的两脚动物”的预言开始,陈黎构建了一个充满讽喻的“动物摇篮曲”–它们不会动物,他们就是人类自己,而且是变异的人类自己。仙女是出色的舞者,但是戴着面具的他们“分不清头脚身体”;魔术师的夫人和情人的世界里,“弹风琴,喝咖啡,做美容操”,是不是只是魔术的一部分?月下,那个落发的和尚在井湄打水,但是,“他的庙宇,单寂地站在一边”;而囚犯大喊“我杀了人!”却对大人说是无辜的,因为“我们实在是在很黑很黑的黑暗当中,除了一声好像是剪刀的声音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精通戏法的腹语学家”在哭着笑着的世界里制造梦幻,却又骗取情感,“古今迷路的星光都化作一堆珍珠在他的脸盆跌宕”……
 |
|
陈黎: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
|
在“虚伪的两脚动物”存在的世界里,人并不仅仅是虚伪,陈黎其实将这种所谓的虚伪置换给了整体性的现实,而在真正“虚伪的现实”里,人才是“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这是一个被雨水围困的城市,“在一个/抽象多于实在,泼墨时髦过油彩的城市/啊市民们,去辨认你们的教堂尖顶吧/问已经把钟声切割成一堆玻璃片/在一个被雨水所困的城市/我要用疾病 传染你们”;这是一个“被连续地震所惊吓的城市”,最后的惊吓是失去了伦理,“我看到老鸨们跪着把阴户交还给它们的女儿”;这是一个“最贫穷的县区”,“这么多进步的屠宰场、射箭队/这么多骄傲的哲学、香料,议会政治之后/来到这座偏僻的石山”;这是一个送癌症病人回家的黄昏,“所以抬头看到昏沉沉的眼睛下山/大概,也是为了明天/像快要睡着的你,不必再注意落石/在这条连续弯路又不太好倒车的单行道上”……地震、大雨、贫困和病症,对于这个城市,对于我们的现实来说,就是一种让人的生命无限脆弱的存在,它们压制过来,它们笼罩着生活,它们异化了一切,每个人不是自己成为“虚伪的两脚动物”,而是在虚伪的现代生活中像动物一样在摇篮曲中走向一种悲剧,《小丑毕费的恋歌》的小丑毕费便是这一群体的象征,“小丑毕费一夜不能睡/他哭,他笑,在颠倒的化妆镜中”,欲望的皱纹爬上了脸,心情被小心地修饰,但是没有面具,没有恋母情结的小丑,在愤怒和嫉妒中,像“湮没的英雄”把情诗写在“每一张顺手见弃的广告单上”,然后,“在伟大的清晨–/跟着全城的盲肠一起走进阳光的印刷场”。
小丑的恋歌早已经消失,英雄般的情结早已经湮没,连面具都不存在的世界里,自己也成为了广告单上的一员,在被印刷的世界里复制成无数个的名字–一种单数变成了无数个的复数,在都是的广告单、印刷场里失去了自我,还会有什么优越感,还会有什么独立性,还会有什么生活的情趣–都是动物般的存在,在巨大的脆弱中,在巨大的虚伪中,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存在。其实到这里为止,陈黎对于现代病的揭露还是深刻的,他关注的是具体而微的存在,他注解的是个体意义的异化,仿佛一面墙,从最初的保护意义到后来的封闭和隔阂,再到从缝隙里钻出来的流言,最后变成了对于人之存在的压制,不是墙变得沉默,是墙两边的人变成了沉默者。
有时候沉默的记录者虽然无声,却有着巨大的反抗性,但是在陈黎之后的《暴雨》专辑中,这种默默承受却让人感受到的压抑和变异却不见了,他以“暴雨”的摧毁方式向这个虚伪的世界喊出了声音,当沉默被打破,其实也只是变成了巨大的声响。暴雨撕开了岸,暴雨投向了海,是为了“冲刷护卫我们的道德的堤”,是为了“升起自最秘密的生命大海”,是为了诞生一个伟大的爱。暴雨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暴雨之存在在陈黎的逻辑里,是因为另一种暴力的存在,写于1989年的《二月》指向的是枪杀事件,当“枪声在黄昏的乌群中消失”,失踪的是父亲的鞋子,是儿子的鞋子,是母亲的黑发,是女儿的黑发,是秋天的日历,是春天的日历;写于1989年的另一首《独裁》,就像题目明示的那样,揭露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唯一的及物动词:镇压”;写于1988年的《新生》则喊出了去除教条和陈腐的口号:“我们要新的国文课本!/我们要新的地理课本!/我们要新的历史课本!/我们要新的公民课本!”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一日,瑞芳永安煤矿四脚亭枫仔濑路分坑因涌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矿场灾变,那首《最后的王木七》则制造了一种黑色的悲剧:
垂死的废流,黑色的阶梯
凹洼的岩层,黑色的庙宇
巨大的墨水池,黑色的哀歌
沸腾的沟壑,黑色的唱诗班
呜咽的月亮,黑色的铜镜
粗重的麻布,黑色的百叶窗
纠缠的铁道,黑色的血脉
失火的矿苗,黑色的水坝
黑色的窗牖,水之眼睫
黑色的谷粒,水之锄铲
黑色的指戒,水之锁链
黑色的脚踝,水之缰辔
黑色的姓氏,水之辞书
黑色的搏动,水之钟摆
黑色的土瓮,水之忧郁
黑色的被褥,水之愤怒
枪声让一切失踪,独裁制造了镇压,新生是为了反抗旧腐,矿难永远是黑色的记忆……这是陈黎对于现实最真切的关照,人在这样的现实中活着,“以痛苦为不痛苦/以沉闷为不沉闷/以杀伐为不杀伐/以寂寞为不寂寞”,每个人都变成了“影舞者”,而陈黎的目的也很明确,是为了让台湾,让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在“给中国少年”的《罚站》中说:“美丽的岛春天了。少年中国,/你为什么还罚站在习惯的教室里?”春天里的少年应该是自由的,是快乐的,是享受阳光的,但是却罚站在教室里,而且更为可悲的是,一切都早已经“习惯”。少年中国,是陈黎笔下的中国表征形象,但是这样一个少年,习惯于罚站在教室里,所以那些痛苦变成了不痛苦,沉闷变成了不沉闷,杀伐变成了不杀伐,寂寞变成了不寂寞,如此,又该怎样新生?
在这里,陈黎的书写是宏大的,他的愿望也是迫切的,但是很明显忽视了具体而微的现实,解构了真切的个体遭遇,在一种口号式的抒情中,“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的矛盾和对立的张力也不见了。但是还好,在后面的《给时间的明信片》,又让目光返回到了对于个体的叙事,时间变成了诗歌的母题。在这里,陈黎的转向其实是为了在人的归属感中寻找自身的位置,当一个人“睡醒在空旷的成人世界”,他其实面临的是迷失,还好有一种叫做记忆的东西会将迷失的灵魂拉回来,“我们忽然想起?遥远的过去。母亲叫我们起床、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寒流》)”那里有“刚学会国语”的母亲,有不停抽着烟的父亲,有家族具体的故事,有和父母有关的误解、隔阂,即使如此,这一场和时间有关的“家庭之旅”也充满着生活的情趣:“那是我们共有的花园,悬挂在/永恒的时间的回廊/我们携带忧伤漫步其中/把多余的芬芳藏进口袋”。
于是,即使和母亲在街头擦肩而过,也有着一份浓浓的亲情;于是,即使时间制造了阴影和河流,我们也会等待开花结果而后和父母一样老去;于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留在投寄的地方,我们也会学着越过枯枝,像鸟一样飞离……那一面隔墙有耳的墙还在,那一些“虚伪的两脚动物”还在城市里,那一个中国少年还被罚站,但是当“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裂了缝的胸前渗出”时,那“不是血。而是/光”–血已经凝固,光会驱赶寒意和死寂,于是在时间的明信片背面,“啊,世界/我们的心,又/合法而健康地淫荡起来了(《浮生六记·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