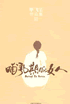 |
编号:C28·2110815·0819 |
| 作者:毕飞宇 著 | |
|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 当当价5.60元 | |
| 页数:282页 |
第一次看毕飞宇的作品是《玉米》,而这本《哺乳期的女人》依然有着浓厚的女性意识和摆脱不了的男权控制。小说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它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他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其实对于女性心理来说,普通读者何止读出了一个哺乳期女人的烦躁和不安,“惠嫂回过头来。她的泪水泛起了一脸青光,像母兽。有些惊人。惠嫂凶悍异常地吼道‘你们走!走——!你们知道什么?’这或许就是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的区别。书应该不错,只是不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系列图书,为何特价得令人不安,25.00元的原价完全出乎意料到了5.60元。
其实,我一直以为毕飞宇是不小心闯进我的阅读世界的,不小心的潜台词是误闯,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深入,或者说,毕飞宇是我阅读世界里最新发现的符号。所以从《玉米》之后,我已经明显产生了对毕飞宇的阅读依赖,从这册《哺乳期的女人》到昨天购买的《推拿》和《青衣》,我被这样一种“充满瓷器质感”的文字所吸引,甚至延伸到了南京作家群上,比如鲁羊,比如曹寇,我不知道是不是南京在地理上处在南北分界的尴尬决定的,总之,我觉得是毕飞宇把我带进了一个古典的阅读世界里,在这里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弥漫开来,如《8床》里的那句话:“处处洋溢出死亡的健康活力。”
但是,对于书名,我还是有一种本能的质疑,在这本收录32篇小说的集子里,作为书名的《哺乳期的女人》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充满瓷器的时代》、《因与果在风中》、《祖宗》、《手指与枪》,我觉得都比《哺乳期的女人》具有更强烈的寓言意义,也更贴近毕飞宇说要表达的“异乡的孤独感”,所以用这篇小说作为书名明显是带着对阅读趣味的挑逗,以性诱惑挟持读者的阅读期待当然违背了毕飞宇小说的意义,所以我的阅读有时会有意绕开这样的表达,而寻找毕飞宇小说背后的历史性、现代性,寻找这些文字背后的孤独、无助、对立。这种阅读的回避与寻找其实正是人为制造隔阂,这种隔阂包括读者和作者、书写和阅读之间产生的背离,说到底,有很多东西是绕不开的,努力去做的事情往往只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我在《火车里的天堂》看到了这句话:“我们厌倦了自我重复,我们无法产生对自己的不可企及。”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剧?不管对于书写者还是对于阅读者,文及其背后的故事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唯一在场的存在,所以不管是对于书名的质疑,还是有意逃避式的阅读,或者都不是面对真诚和富有质感的文字最起码的态度,也就是说,到这里,所有的质疑和逃避都应该消失,都应该回到文字本身,回到毕飞宇的符号中来。在这样的回归中,我竟然最后发现早就存在的秘密:早在10年前,或者更远,我就已经是毕飞宇文字的阅读者,他不是以“不小心”的方式闯进我的世界,他其实早就修补在我的文字世界里。我就是在《武松打虎》中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兴奋地看到了在另一个世纪伏案阅读的背影,说书人的经历在我脑中翻过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就是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心中早就存在的英雄主义,村子打谷场的那场说书,其实是在消灭武松这样的英雄,在消灭一种意义,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说书人在夜晚的死亡,曾那么惊人心魄地闯进我的世界,说书人死了,就是文本的被消灭,那个英雄主义的武松也就不复存在了:“武松提了哨棒没有上山,他没有与大虫相遇,也就是说,他没有打虎。”
我记住《武松打虎》,但是没有记住毕飞宇,明显是一种文本意义在现实中的复制,毕飞宇像是那个说书人,他只是在这个故事中创造英雄,但他同样杀死了英雄,毕飞宇或者说书人的存在是要把你抛向一个历史的虚空中,却又要把你拉回来,让你在这样历史和现实,文本和故事对立中寻找到意义。我忽然发现了阅读毕飞宇这部小说的钥匙,因为10多年前的《武松打虎》,因为毕飞宇成为另一个说书人,或者因为《哺乳期的女人》的诱惑和反诘,总之,我找到了散乱在各处的线索,聚拢在一起,从此,这部小说要开始重重地走向我了。
和《武松打虎》的意义消解一样,毕飞宇正是在寻找文本背后那些意义到底影响了我们多少判断?或者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自我重复的那个孤独者?在时间之外,在历史之外,在习俗之外,我们都是不可逃脱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我在《充满瓷器的时代》里发现了那个词:异乡人,是啊,在自我重复的时代,我们就是被自己异化,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故乡。在毕飞宇看来,这种异乡人的感觉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男人与女人的对立等等,而要消除这些对立,毕飞宇分别用时间、语言、爱情来修补仪式,在仪式的复原中寻找意义,寻找信仰,“信仰沦丧者一旦找不到堕落的最后条件与借口,命运会安排他成为信仰的最后卫士。《因与果在风中》”
首先是时间。《五月九日和十日》中,毕飞宇就直接把生活中对于时间的双重性呈现了出来,昨天和今天,在时间上成为两个男人不同的时间属性,时间在另一种意义上混淆了真实,在《唱破二黄的一朵》中他说:“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昨天等于今天,今天等于明天。”而在时间具有的仪式感上,与《五月九日和十日》异曲同工的是《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他说:“零时,是一个日子与另一个日子相交接的性感时刻。”单纯把时间做一些形式上的阐述并不是毕飞宇想要的,他要把时间切开来,看到历史,看到现时,看到未来,在《武松打虎》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消失,而在《祖宗》中,我们则看到了对于历史的复原。《祖宗》写了太祖母的死亡,作为一个家族的曾经见证者,“太祖母的身上终年回荡着棺材与铁钉的混杂气味。”,而在这样一个标本身上,似乎还在延续着历史,延续着真实和虚构混合的故事,她又长了新牙,在民俗意义上,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它预示着历史将成为一个家族无法摆脱的梦魇,太祖母以“人精”的形式将延续权威,这让整个家族的现实生活破绽百出,最后他们通过合谋“拔牙”的方式消灭了历史,消灭了意义,也使太祖母最后成为的历史纪念物,“破译这里的宇宙玄机”。
第二种途径是语言,这是城乡对立中寻找的一种突破口,“新世纪大厦”和“断桥镇”这两种地理坐标成为城乡对立的符号,一个是28层的生活,一个是农村的世界,一个是遥控的生活,一个是养蚕的世界,《遥控》和《生活在天上》就是直面这样的对立:“这也遥控,那也遥控,城里人还长一双手做什么?”遥控生活代替乡村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器物替代,实际上是现代人寻找不到归宿的寂寞,《生活在天上》的母亲在高层大厦里找不到自己了,物质丰富的背后却是精神的空寂,而在28层养蚕就是一场黑色幽默。所以我们看到了那种无助,那种孤独,还有《卖胡琴的乡下人》的饥饿感:卖琴人这辈子就栽在饿上头,而对于曾经的“艺人”来说,城市永远是不允许他们的存在:“城市的概念是卡拉OK、KTV,MTV;城市的记忆对胡琴早就失却了怀旧。”所以在这样的对立中,语言成为一种解药,在《充满瓷器的时代》中,“蓝田和他的女人有意无意地学起了秣陵镇的声腔音调。这是接近异乡人的唯一途径。”在毕飞宇一系列城乡对立的小说中,语言都成为一种符号,不仅挂在嘴边,也刻进了心里,成为不可更改的身份符号。在《马家父子》中,“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他们父子的隔阂集中体现在语言的自我认同中,“语言即人”,“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即使骂人,他们也以不同的语言划清着各自的界线,而这种分界也在心里上造成了永远的隔膜:“儿子马多的精神沿着北京话的卷舌音越走越远,故意背弃着故土,故意背弃着老马的意愿。”
第三种是爱情的拯救。在这里其实是惜墨如金的,他没有花很大篇幅来描写爱情,来塑造经典的男欢女爱,更多则是对于缺失的爱情的追寻,而在更多意义上,是对性感受的追寻。在《架纸飞机飞行》中仅仅是一个念头:“我有妻子、女儿,居然又想恋爱,这个念头危险之极。”世俗的判断压抑着性感受,在《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作为一个孩子,对于母性哺乳的获取,完全是天性的,是压抑之后的回归,但是却遭到了另一种世俗力量的干预,“哺乳”的性符号完全被消解成了个体意识的萌动。在毕飞宇的很多小说中,男女之情往往以离婚的方式而告终:“离婚真是太容易了,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男人还剩下什么》”,毕飞宇用很多对立的词语来描写这样的感情困境,比如:当出轨的时候,“目光简直,美不胜收”;当说到离婚时,“哭得真美”。但其实这并不是感情沦落的轻松感觉,而是一种信仰的缺失,在《因与果在风中》,当棉桃成为长发飘飘的女人,“罪过(或堕落)把女人还给了女人”,而最后水印出家则预示着信仰的最后泯灭“出家俗人水印出家后重新做了和尚,为正反两方面的人都预备了好条件与好借口。”
时间、语言、爱情,毋宁说是毕飞宇消除信仰缺失的努力,不如说是在这样的努力复原中,寻找到了世界另一种堕落,这种指向让世界更加无助,更加孤独,也更加没有意义,而毕飞宇刻意营造的这个世界就像《手指与枪》中断指的高端五一样:“在抚摩中,高端五体会到的不是抢,而是手的完整。枪弥补了手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