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31 《玉米》:“不许压韵”的女性史诗

“不许压韵!”是诗人楚天最后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是反抗,是愤怒,实则是无助,是压抑,是徒劳,身披白大褂的医生给了他一针,激烈的咆哮变成了迟钝的目光,只剩最后挣扎的呼吸,“像岸边上躺着的一条鱼”,他最后他被送上了救护车,结束了一个放浪诗人的全部历程。
诗人楚天完全不是小说的主角,甚至他完全可以在和玉秧的感情中被忽略,但是楚天却是一个符号,看不惯师范学校的一切,却渴望男女之情,只是这种感情带有强烈的欲望,给8个女孩写情诗的结局是他成为道德维护者的反面典型,他叫出的“不许压韵”的呼声看似在维护诗歌语言的纯洁性,实际上是在颠覆一种守旧的传统道德,他疯了,任何人都把他看成是个疯子,但是有时候最疯狂的并不是疯子,而是疯子背后的社会评价体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压制,而在一切可以被麻醉的乡土中国,“不许压韵”毕竟显得微弱了,而所谓的身体革命也终究是一次徒劳。
回到小说本身。我觉得毕飞宇用一种很高超的障眼法把诗歌力量藏在了具体叙事的后面,你在一个家族式的女性成长中看到了风俗和道德,看到了社会变迁,但其实透过这些故事表现,毕飞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沉重的人性命题,第二人称变成了“第二”人称,在叙述者的背后你能很真切感受到那种不均匀的呼吸,仿佛就躲藏在你的身边,冷不防会龇牙咧嘴对你怒喝,只是藏的太深了,我们都以为是一个在社会和历史中走不出的宿命。就在今年的3月17日,《玉米》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评委在评价中这么说:“生动地探索了文革中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通过环环入扣的家庭冲突和爱的故事,展现了个体和社会的面貌。”
这或许就是大众视野中的《玉米》阅读。从购买的时候起,我就对这本当当价格只有6元多的小说开始误解,这样的出版社闻所未闻,翻开来看的时候,纸张的确很粗糙,比不上其他纸张光洁,也抵不上其他书锋利,我只是把它当成一部了解毕飞宇创作的简单小说而已。但是在越来越深入的阅读中,我才发现原先的认识是一个十足的笑话,我第一次被那种充满张力的语言所折服,很委婉地讲述故事,却把你带向一个温柔的陷阱,直到最后你才发现你已经深陷其中,拔不出来,那些文字都是一把把锋利的刀,要把你划出殷红的血来。
这些血属于女人/女性,在这个二元关系中,血不仅具备生理上的特点,还具有女性被客体化的标志,从玉米的自慰“来填充自己”,到玉秀草垛上被报复强奸,最后到玉秧第一次给了一个家里阳痿、专门揭发男女私情为道德招牌的老师,那些女性身体之痛的血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流了下来,这是男权统治下的代价,她们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得了男权社会的评判,而实际上在女性身体里留下的并不是身份认同的惊喜,而是如玉秀那样“脑子里滚过一阵尖锐的恐惧,男人的恐惧,对自己下半身的恐惧”。
玉米、玉秀和玉秧,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而要在她们的故事中展现女性身体之痛,就必须树立一个参照系,那就是男权社会。三个女人的父亲王连方就是一个男性集权者。他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有着不一般的淫威,在家里他是绝对权威,妻子施桂芳只是他生孩子的工具,在连生七个女儿之后终于生出了儿子,女人是一种工具而已,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在王连生身上达到了高潮,不仅在家里,还毫无顾忌地睡村里的女人,他和有庆家的女人赤条条睡觉,被从水利工地回来的有庆撞见,王连方竟然恬不知耻却像模像样的说:“有庆啊,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实在让人哑然,而有庆家的女人不小心怀上了王连方的孩子,死活要生下来的时候,婆婆竟然说:“怀上就好,你先孵着这个,能怀上就好了哇!”
在王家庄,王连庆就是男性的权威,这种泛化的权威掩盖了道德和法律,以致在被秦红霞的婆婆发现之后,对他的处罚也仅仅是职务上的免掉,而没有追究任何法律上的惩罚,双开除的王连庆“四十二岁出门远行”,表面上是远离了男权,实际上是一次隐形的继续,在他的安排下,玉米嫁给了县里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从王连方到郭家兴,实际上是男权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更具有过渡性质的男人:彭国梁。彭国梁是开飞机的解放军,对于王家庄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权威,具有更强的崇拜性,在和玉米的接触中,她已经越来越被这种权威所折服,即使在最后被怀疑被人睡过而被彭国梁抛弃,玉米还是觉得没有把身体给他是一种失败,甚至是一种耻辱,“他这架飞机要是飞远了,玉米的天空真要塌下来了。”而最后,他用手指来填充自己,在疼痛中获得安慰,也彻底告别了守身如玉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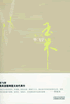 | 编号:C28·2110517·0809 |
玉秀完全是女性身体被男权统治的牺牲品。在村里看电影时就被那些报复他家的男人们强奸,这个被“玉米”称为狐狸精的女人实际上是王连方男性淫威被报复的牺牲品,从此,在她的身体内部留下了对于男权的恐惧,她不敢爱,手里像是永远拿着一把刀子,在和郭家兴的儿子产生感情之后,那种乱伦般的姨妈和侄子的关系让她的爱变成了耻辱,尤其在玉米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亵渎,是见不得人的事。当最后得知玉秀偷人必须生下孩子之后,她内心的道德大厦顷刻倒塌了,她以为这是玉秀最大的丢脸,但其实玉米自己也是一个牺牲品,只不过看上去她的经历更为隐蔽。当玉秀生下孩子,玉米得知是个男孩时,把他送了人,也没有满足玉秀的要求最后见一面自己的骨肉。把男孩送人,或者也可以看成是玉米对男权的反抗的开始,她要用这样的形式来消灭新生的男权。
但显然,这样的消灭显得一厢情愿,对于这个社会现实来说,男权是可以繁衍的,不断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玉秧生活的师范学院就是一个男权统治的另一个小社会,在《玉秧》里,我们能体会到和《玉米》、《玉秀》在整体上的脱节,对于毕飞宇来说,或许是一种新的开始,在这里,都是倾轧,都是怀疑,也都是犯罪。“每个人都在犯罪,每一个人都是罪犯,谁也别想置身于事外。”所以玉秧成了像克里斯蒂娜小说中一般的侦探,负责检举揭发学校的男女关系。而学校校卫队的负责人魏向东则是男权社会的最大统治者,这个以前温和的男人就是因为拳头硬、出手火爆,把学校的革命推向了一个新台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把男权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他成功在玉秧的检举下揭发了好几对男女,另一方面他在交易中慢慢侵入女性身体,没有暴力,只有你对他的信任。有人揭发玉秧怀孕了,魏向东要亲自检查,玉秧完全当成一种工作,而就是用这样的手段,玉秧把第一次交给了他,在血红的记忆中,她身体变得麻痹,变得病态。其实,玉秧作为七姐妹的老幺,从一开始就是男权的牺牲品:“这一来幺妹子很不值钱了,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所做的预备,一个热身,一个演习,一句话,玉秧是一个附带,天生不讨喜,天生招父母的怨。”
玉米、玉秀、玉秧,三个女人的生活史诗,实际上是不能逃脱男权统治的怨曲而已,她们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自己获得的爱情,也没有自己真正的骨肉,甚至她们的身体在一次次遭受戕害中变得麻木。她们甚至没有自觉要跳出男性包围的勇气,只有屈服和妥协,而且更可悲的是,在他们身上滋生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权利阴影:“但是权利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里,捏出汗来,权利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在权利的被压抑和自我争取中,三个女性实际上是走在了一条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宿命之路,沉沦之路。在散发泥土的气息的土地上,充满了美丽的忧伤。
PS:题图为田洪涛演播的《玉米》封面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