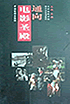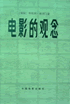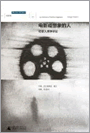 |
编号:Y29·2130220·0945 |
| 作者:【法】埃德加·莫兰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4月 | |
| 定价:36.00元亚马逊25.90元 | |
| ISBN:9787549506910 | |
| 页数:251页 |
“只有电影艺术出现后,想象过程才得以原原本本和完全彻底地显露出来。我们终于能用形象表现我们的梦幻了,因为这些梦幻已附着在实际的材料之上。这种梦幻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清醒状态的生活,它们教我们如何生活或如何拒绝生活。”将想象当做是现实生活的反面,在埃德加·莫兰看来,电影艺术展现了我们心里“既显著又晦涩的潜在部分”,而这个潜在部分是全部人类性的一部分,所以本书的副标题即为:社会人类学评论。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电影,或者说,通过电影研究来探索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埃德加·莫兰在《电影或想象的人》里试图将电影学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人类的精神和外部客观现实的问题,从而使本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电影领域,为人类学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方向。
《电影或想象的人》:每次表演都是我的再生
观众们,如果你们曾经相信我是真人,如果你们曾认为我和你们一样拥有肉体、灵魂和心脏,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死去,那你们和我又有哪些不同呢?你们是血肉之躯还是草木之躯?
彼得鲁什卡是木偶还是拥有灵魂的躯体?它或者他,生活的“另一个王国”里有没有不朽的神明?以及“宗教信仰的源泉”?只是幕布拉开的时候,有着细线,有着小提琴声,有着动作笨拙、不善言辞、但感情纯朴,招人喜爱的那个形象,在集市上它跳舞,表演,以及最后的痛苦、哭泣和期望,但是那些形象和运动,最终却指向一个被杀死的命运,是人的计谋,还是魔术师的名令?只是当幕布再次关闭,死亡变成了可以继续开启的芭蕾舞,继续跳舞,继续表演,继续痛苦、哭泣和期望,以及继续死亡。
只是它说:“每次表演都是我的再生”的时候,一共是有三个木偶的,都是草木之躯,但都是有关爱和恨的灵魂。可爱而有些粗鲁的彼得鲁什卡爱上的是女演员,也是木偶。女演员却爱上了凶狠而外表漂亮的摩尔人,也是没偶,而彼得鲁什卡因为嫉妒得不能忍受,设法破坏了他们的爱情,那个市集的晚上,彼得鲁什卡逃跑,气得发疯的摩尔人追上,一刀就杀死彼得鲁什卡。当舞台变成一个祭台,爱和恨那里有血迹和哭泣,草木之躯背后就是一根细线,就是一个魔术师的表情,所有可以取代的就剩下刺耳的音响、粗砺的线条外加荒诞不经的剧情。可是当幕布变成了一个时代的背景,芭蕾舞的的舞台也绝非是一个祭台,那个成为木偶的芭蕾舞演员却没有一根细线,却没有肚子里的稻草,他最后的墓前,呆坐着彼得鲁什卡,却已经成为一尊铜像。
这是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角色,也是他常常用以自喻的形象。但是当木偶的躯体死去——杀死或者被魔术师控制,那么那另一个王国里一定住着一个灵魂,住着一个理性存在物,一个宗教信仰的源泉。而在埃德加·莫兰看来,这只是参与生命和灵魂有关的雕像、傀儡、木偶和印刷符号,而这些不同的符号最终成为传奇英雄一样,是真实的一种再现。血肉之躯还是草木之躯的电影学意义,其实便是他在《电影或相像的人》里那个化身和变形,一个潜伏着的自我,和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生命在一个王国,和在另一个王国一样,都是符号意义下的再生,是灵魂创造的不朽之躯,木偶或者铜像,魔术师或者芭蕾舞演员,让幻觉的化身成为绝对的客体,“木偶彼得鲁什卡的故事是所有真正虚构的想象人物的故事。”那个王国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的王国,是埃德加·莫兰的王国,是卢米埃尔的绝对现实主义王国,也是梅里爱的绝对非现实主义的王国,他们表演,他们再生,他们用技术的符号编织艺术的梦想,他们用真实的现实创造艺术的世界。
埃德加·莫兰说,早在《人类与死亡》中就指出,“人类对再生的普遍信仰只有两个源泉:一是相信化身,即在映象、阴影和梦幻中出现的另一个自我,他们甚至对此早有感受;二是笃信变形,即生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化身是草木之躯背后的血肉之躯,是铜像背后的墓地里的那个灵魂,自我就在电影的镜头里,这是柏拉图洞穴假说中的影子王国,这是“人类自从举头望天起便产生的疯狂梦想”的另一架飞机,“电影把化身和幽灵的古老世界神奇地再现于银幕。”而这些化身就像木偶在舞台上的所有话语符号传递的那样,“化身和幽灵使我们痴迷陶醉,难以自拔”。在我们并不知晓的身体里,“提供了未曾经历的生活,并以梦想、欲望、向往和规范滋养着我们的生活。”从卢米埃尔的机器时代开始,这种化身的魅力便从我们的未知世界逐渐走向了已知世界,莫兰将其称作是“神灵旅居之地”,而这个在德吕克看来是“人与物的最高诗意形态”,在穆西纳克看来是“人和物的诗意性质”,便是先锋派时期路易·德吕克提出的“上镜头性”。photogenie,这是照相与精神的合一,这是“通过电影放映机显现出来”的魅力,是电影在客观反映现实的时候,“偶然”产生了一种艺术感染力。
埃德加·莫兰将其看做是对电影本质的反思,是电影对于照相技术的一次真正超越,那些“镶在镜框中,贴在相册上,夹在钱包里,被人们端详、爱戴和亲吻”的照片只是“具有从保存道德到施展魔法和再现亡灵等各种功能”,但是更多只是私人占有的“固恋”,甚至它所定格的瞬间也只是完成了技术上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性阐述。而电影的意义是在寻找梦幻的化身,寻找另一个王国里不断重生的可能。这是自身的暗示,这是自我的矛盾,而这样的化身使世界重新焕发出“固有的魔法性:这是个永垂不朽的世界,即亡灵的世界。”在莫兰看来,化身是人类在自我意识之前的基本影像,“它体现在映象或暗影中,投射在梦想、幻觉、迷信、宗教和表象上。”而这只不过为电影提供了揭示自我世界的那种深刻矛盾性,“既像是外在的,又像是同一的:这既是我,又不是我”的“自我替代”现象,在电影的投射中成为另一个符号,而这种“生物或非生物”的化身或者就如木偶彼得鲁什卡对人类的疑问一样,到底是草木之躯还是血肉之躯。
自我替代的矛盾对于莫兰来说,或许是深刻体会的,这个曾经着迷研究的却是共产主义问题,而从共产主义问题转身面对电影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时,一定会有一种木偶般的疑问,那些有关的肉体、灵魂和心脏是不是仅仅是客体世界的一部分,就像幕布、细线和稻草一样,所以莫兰的“自我替代”是一种革命,不仅是从共产主义问题走向电影的“社会人类学”,而且是对笛卡儿时代开始的那种“分离/压缩/简化”的思维方式的质疑,在他看来,笛卡尔时代的思维范式“破坏和损毁了现象的复杂性”,而我们所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范式:“它使我们既能看到事物的异质性和对立性,也能看到其复杂的统一性和互补性。”
化身和变形无疑是莫兰在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重新建构,甚至在这本为1957年出版的《明星》而产生的“副产品”里,要拆除电影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生存悖论:“工业化、资本主义或国家化的电影生产既要排斥创造,又要将创造纳入其中,在创造与生产的博弈中,所有因素都会在人力、偶然、统计、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而这种对悖论的拆除意义也便是一种在“另一个王国”里看到的自己的化身,灵魂的化身,意义的化身,自我的化身。而这种化身正像一个男孩儿对马克斯·雅各布所说的:“人们用死人来演电影。他们找来一些死人,让他们活动起来,这就是电影。”
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开始的化身,在梦想、欲望、向往和规范中滋养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小男孩的问题就直接指向电影的灵魂问题,类似德帕维尔的疑问是:“在这些惊人的写实场面中,他们到底是观众还是演员。”死人活动起来演电影,是一种形态的转变,而客体和主体之间仍然有着一种天然的鸿沟,那便是观众还是演员的问题,化身的目标到底指向哪里?在电影对客体世界的投射-认同中,其实所建立的灵魂世界是一个拟人类和拟宇宙的一个王国,这种“倾向于把主观性结构赋予客观影像”的电影现象的最终目的或许在寻找“梦幻与现实的复合体”,兼纳清醒和梦幻的混合状态将电影带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有着影片具有的客观性物质,是客观性、实体性和合理性的结合,是清醒的技术世界,而那些音响和音乐、虚构的故事,以及情感的参与又让现实看起来充满了虚幻的色彩,那些建筑物会骤然消失或沉入地下,特写镜头中的庞大昆虫让人看不出是舌蝇,在近景镜头中,刚果铁匠打造的刀具远大于实物……是的,当潜伏的梦幻世界会突然淹没客观世界的时候,电影只是对幼稚的观众营造了一个封闭自我的世界,这种侵害也正是一种矛盾:发现自我是为了逃避自我。
所以,莫兰的真正意图是在发问:那个自我的客观世界到底在哪里?那种“非凡的真实性”是不是电影真正追求的?这或许是另一个主题的阐述要点:变形。从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在电影意义上,则是从电影术变为电影艺术,也就是从电影放映机到电影艺术的转变,这是空间的变形,而在这种变形中物体也有灵魂,也在面孔的景观中发现“神奇的视觉”,发现影像背后的想象物,在梦幻、音乐、虚幻、魔力、主观性中获得艺术的魅力。当然,梅丽爱在莫兰看来,就是一个从卢米埃尔现实主义而来的革命者,他的“绝对的非现实主义”将卢米埃尔的电影术融入了梦境,1896年广场拍摄的一分钟便是一种“奇妙变换”,是电影魔术时代的开始,他的场面调度使影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戏剧性表演的道路”。所以,在电影的艺术化道路上,“梅里爱像魔术师一样,使电影术摇身一变就成了电影。”就像那个拉着线创造了三个木偶形象的魔术师,他才是真正的符号,真正的灵魂,真正的信仰源泉,而1896-1897年,滑稽、爱情、袭击、演义等内容纷纷进入影片,电影成了虚构的同义词,而同时,电影中的东西、物品、实物具有了新的性质,成为“主观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只有在这样的变形中,在当电影真正成为艺术的时候,草木之躯才能变成血肉之躯,才能使每次表演都成为一次重生。
其实,这并不是莫兰的终极目标,用社会人类学来构建一个电影王国,才是他的任务,所以在声音、色彩和维度对于电影客观存在的影响中,在梦幻、特技、艺术对于电影灵魂世界的挖掘中,莫兰更希望拥有一种更理性的电影王国,这便是电影语言的意义,而这种电影语言其实并不是对话不是台词,也不是那根细线那块幕布,而是“电影艺术自身产生了一种抽象、推论和概念系统”,一种逻辑、范畴或理性,也就是那个走向最终归宿的logos,这是电影艺术走向象征的本质,在叠化、化入化出和叠印等手法之外,这样的象征便是意义上的符号,包括凋谢的花束、一页页飞逝日历、快速转动的表针、堆满烟蒂的烟缸……“这些压缩时间的表象先成为一种象征,后又成为时间流逝的符号。”莫兰的出发点就是让电影不仅从技术中走出来,还要从那个魔法的晦涩渊源中摆脱出来,“并提升到话语的理性层面”,在莫兰看来,这便是真正的人类存在方式,是在想象的投射-认同中,在“人类半想象的现实”中发现自我的真正意义,发现普世的价值:“我们应当对梦幻提出询问,即把想象重新纳入人类的现实。”
作为完全从人文视角来观察电影的著作,莫兰当然是要在电影的”社会人类学“里建设一个新的王国,建立“人与物的最高诗意形态”的”上镜头性“的电影世界,但是那种理性世界是需要解构想象,还是将想象纳入现实的理性中?莫兰也说过,自我的替代是一个“这既是我,又不是我”的深刻矛盾,而在电影世界里,“发现自我的需求表现为力图强化自我,把千百个想象中的非凡人物当作自己的化身。”这即是说,发现自我是为了逃避自我,所以即使那个草木之躯的木偶能在符号的意义上构建一个灵魂世界,但是它的血肉之躯也只是一根细线下的产物,背后仍然是一个魔术师,“幻觉的化身甚至是绝对的客体”,那么,好了,永垂不朽的灵魂就一定是一次自我之外的虚构,只有虚构不灭,生死不灭,那个王国里就一定会有不断的再生,不断的有幕布拉开,不断的有小提琴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