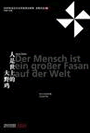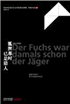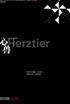|
编号:C38·2211108·1790 |
|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
|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
|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
| 定价:58.00元当当29.00元 |
| ISBN:9787221161772 |
| 页数:296页 |
一个制衣厂女工想要到一个出口服装能到达的美丽国家去,于是在出口衣服里塞进了通讯纸条,期待有外国男人来接应她,被人告发后,她连续三天被传讯,随后工厂里出现了第二批纸条,她因此被解雇,从此必须定期接受警察的传讯。《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某一次被传讯的日子开篇,“我”乘坐有轨电车去秘密警察那里接受审讯,一路上再次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如何被人告发直至被解雇,失败的婚姻,身边的小人,亲密好友如何惨死,父亲如何背叛母亲……最后意识到唯一剩下的幸福——与爱人的平静生活也一直被监视、被打扰。“幸福的失败完美无缺地奔跑着,使我们屈服了。”这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第三部,小说以通过一段乘车路程,回溯了一个人十几年的人生经历,现实与回忆交错展开,顺叙、倒叙、插叙逐渐混合,表现出一个普通女工在艰难时期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
对了,还有第五种可能性:很年轻,美得惊艳,脑子没疯。但人死了。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
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从来不被传讯,但是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被传讯,而且也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两个疯女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比如我和保罗;三种之外是第四种,没有被传讯,也没有发疯,但是人死了——莉莉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是她的幸运,她美得惊艳,也没有发疯过,但是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觉之后,他们逃亡了匈牙利边境,“他被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死了的莉莉成为了第五种人,或者她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在这四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五种,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也没有死去。
不被传讯,没有发疯,也没有像莉莉那样死去,这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也会对世界感到厌倦?被传讯,疯了,死了,是可能性里的几个条件,从不满足于这些条件而厌倦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畸形的?或者说,不被传讯和被传讯,没有发疯和疯了,活着和死了都在同一性中成为荒谬地存在:整个世界都被传讯,整个世界都疯了,以及整个世界都死了,所以没有人能自我辩护,没有人能自我保护,当然没有人能逃离对世界的厌倦,就像书名所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我”和“自己”之间呈现的“不愿”,就是自我的隔阂,就是自我的异化,就是自我的逃避——不是人厌倦了世界,是世界厌倦了所有人,包括唯一的自己。
自己便成为了缺席的人,而作为主体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空位,一个虚拟的第一人称。在“我”和“自己”之间,如果呈现良好的“面对”状态,是不是趋向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扩散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透明以及单纯的存在,它里面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工人之间的深厚阶级情,但是当世界只有被传讯、发疯和死了三种对世界厌倦的可能性结局,那么这些直接、透明和单纯的关系,都将变成“不愿面对”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就如经常喝醉了酒、我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手上的那瓶白酒,人们根据标签上的图片取名“两棵李子树”,它是女人所熟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这种挚爱就像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我和保罗在拍摄结婚照时,我既没有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第二次婚礼所呈现的就是仪式的空无,我和保罗仿佛就是“两棵李子树”,毁灭彼此又不放开彼此。
毁灭和不放开,是把生活固定在封闭的状态中,婚姻如此,爱情如此,单纯的睡觉也是如此,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两棵李子树”的关系学中,谁被传讯了,谁发疯了,谁又死了?从第五种可能开始,死了的是莉莉,和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了之后,她被枪杀在边境,这是一种死亡,但不具有秘密性,因为莉莉曾说,“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而这个表皮下面的核心之死又是什么呢?老军官曾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妻子,在妻子去世之前,他经常进行军事演出,那时的秘密是:“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但是在妻子去世之后,他每天去墓地,这成为了秘密的核心,一种死亡带来的核心,是永远可以被谈论的故事;莉莉呢,在被枪杀之前总是爱上老人,或者是宾馆门卫,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皮货销售商,或者是摄影师,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和老人睡觉,莉莉的说法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真正的核心或者和她的继父有关,她说起想和他睡觉,但是他让她等着,最后她没有顺从,这种想要和他睡觉又没有顺从的心态源于继父和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睡觉,把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盖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莉莉的说法,当母亲不再去教堂,意味着在她看来现在的弥撒“是以给国家领导人祈祷开始的”,就像她和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用死亡盖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完成了新的仪式,这是死亡的延续,莉莉眼里流露出来的刺痛便是对死亡本身的厌倦,于是,继父变成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人,变成了死去了妻子的老军官,而她的这一核心话题依然是被死亡主宰的。当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她的死又是谁制造的?是那个枪杀他的野小子,莉莉的尸体送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他可以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在等待,尽管她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直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一样。”
莉莉的死是一个被谈论的表皮,背后的核心是老军官妻子之死带来的“陌生女人的床”,是莉莉母亲将第一人丈夫的死“盖在自己身上”,是枪杀莉莉的小子得到十天假期而感觉自己像一个人——死亡就像是“两棵李子树”,在毁灭而又不放开彼此中制造着仪式的空无,而空无本身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但是莉莉并不是唯一的死,她的死并不是唯一对世界感到厌倦的可能性存在,还有“我爷爷之死”,那是我曾经杜撰的情节,因为我想去商店买一双高跟鞋,于是我撒了谎,去成立买了鞋,但是谎言也成真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还有和我玩的那个瘸腿男孩的死,天生瘸腿的他总和我在那条被压坏的道路上挖山,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在深度麻醉中再也没有醒来,于是,“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被压坏的马路”;还有父母曾说起过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受洗前就去世了,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看见另一个男孩,就对我说:“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我之所以降生是因为哥哥死了,生命只是一种取代,取代另一个生命,取代一种死亡,当然,它就是一种空无——谎言中“我爷爷”死去,记忆中的男孩再没醒来,我取代哥哥而活着,死亡背后依然后对世界的最大厌倦,在“两棵李子树”所呈现的关系里,死亡本身也成了“两棵李子树”的隐喻,毁灭彼此又不分开,在秘密的核心中甚至就变成了荒诞。
或者,死亡是直接呈现的,是具体表达的,是有和无可以明确被界定的,那些墓地就是死亡的物质证明,而关于对世界厌倦的元素中的“发疯”呢?精神病院里的那两个女疯子是发疯的存在,这也是直接可以界定的,而和死亡一样背后的秘密所具有的核心,对于发疯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他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除了消遣,他为什么要到小区了找神秘的东西?在上女中的时候,晚上我会和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上,然后他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但是那次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一只脖子——爸爸在亲吻女人的脖子,“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爸爸和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女人亲吻,“女儿”变成了女人,这不是一种丧失伦理的疯狂?在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是:白天是拿,晚上是偷,因为工厂属于人民,因为人民来自人民,所以拿走的东西就是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人的袜子被拿走了,衬衫被拿走了,鞋子被拿走了,拿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它的工人裸体走出工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永葆青春,于是工人们这样打招呼:裸体早上好,祝你裸体胃口好,祝你裸体下班愉快……拿和偷被白天和晚上隔开,因此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不是拿走意味着永葆青春的裸体,而是当保罗让偷窃发生,“摩托车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解雇了。”
疯了就是无休止地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就是用借口把丧伦行为说成是爱,就是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也是审讯我的阿布每次打招呼都是用唾沫吻我的手,也是厂里的领导内罗在出差时睡我让我回去之后“表示反对”,也是两名内审员将皮裙强硬套在莉莉身上,“好像我是他的顾客似的。”疯了的现实中当然有谎言,有权力,有欲望,有异化,而“疯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会让每个人都可能被传讯——传讯一开始就成为了“我”摆脱不了的命运,第一句:“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为什么被传讯?核心事件是,他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意大利语:Ti aspetto,这句“我爱你”后面还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这的确是我写的纸条,而且放进了十个裤兜里,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打算嫁给西方人。但是这句话被工厂里的人发现了,被定性为工作场所卖淫,甚至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我不是工厂党员,这也是我的触犯,于是他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打算嫁给西方人,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写下“我等你”的意大利语,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行动,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是我面对自己想要收获的结果,但是它变成了“卖淫”甚至差点成为“叛国投敌”,这是不是一种疯狂?审讯了三天,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在为瑞典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来自独裁国家的衷心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如出一辙,我没有写过它们,但是从“我等你”到“独裁国的衷心问候”,性质完全变了,个体的表达变成了对国家的造谣,于是我被解雇了,于是我接受了传讯。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写的纸条,我被传讯,而他们早就疯了,在一种疯狂的罪恶中,我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是马斯楚安尼,是墨索里尼,是马塞洛——一个意大利通用的姓氏,它代表的是一个虚拟的意大利人,就像虚拟的“我等你”,就像更为虚构的“来自独裁国的衷心问候”。
我被传讯,我坐有轨电车接受传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到戴草帽的老人,带孩子的男人,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在我被传讯的途中,在我的观察中,他们都变成了发疯的人,变成了隐藏着秘密的人,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投射,都变成了被传讯的对象;而丈夫保罗、用唾液吻我的阿布,传讯我的内罗,也成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样对世界感到厌倦——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就是令人厌倦的,就是被传讯的:保罗的母亲从乡下来到重工业城市,“在床上,她通过献出下身成了一名党员。”而我的公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党内积极分子,负责没收财产,他使用香水而被称为“香水共产党员”,“香水是他的第二皮肤。”阿布的身上也散发着香水的味道,法国香水“艾薇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他也是香水共产党员,和像水一样,“共产党员”也成为我公公和阿布的“第二层皮肤”;我“骑白马”的父亲手里抓着灼热的钢铁比抓住自己的理智更像困境,因为他身上也有股香水的味道;还有我的爷爷,曾经在和我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说:“早在一九五一年,这条狗闻起来就有香水的味道了”——香水是第二层皮肤,他们是“香水共产党员”,而狗身上有着香水的味道,就像我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
保罗的回答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被教育得很乖,做我的家庭作业,我父亲把我叫进厨房。他的刮胡子工具放在桌上,炉子上放着热水。他给我的脸上直至鼻孔涂上肥皂,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我当时还没有排成十排的七根胡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开始刮我的胡子,然后去了党小组那里,对我的父亲而言,这属于一个整体。他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之前了,只能和它一起走。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有了胡子代表长大,父亲让他加入党小组变成了成长的仪式,“这属于一个整体”,法西斯分子和非法分子是一个整体,少数人和许多人是一个整体,共产党员和非工人是一个整体,当然,死了的人、发疯的人、被传讯的人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两棵李子树”——这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即使我曾经那么坚决地面对自己,对阿布喊出了:“请您把我的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不再像莉莉那样掉了头发也不敢说,不再对有着“艾薇儿”或“九月”牌香水的香水共产党员屈服,但是“我的”头发真的会是自己的我的和自己真的能组成另一个整体?也许在集权的社会里,在独裁的国家中,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香水是第二层皮肤”的荒诞中,“面对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从“两棵李子树”的状态走向一个人制造的死亡,不彼此毁灭,也不要彼此分开,就像保罗说的,“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