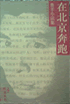|
编号:S29·2210818·1773 |
| 作者:韩东 毛焰 鲁羊 于小韦 著 | |
|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当当27.30元 | |
| ISBN:9787559457370 | |
| 页数:202页 |
副标题:“韩东 毛焰 鲁羊 于小韦四人诗辑”。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他们”诗群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韩东、鲁羊、于小韦以及近年来加入、为“他们”增添鲜活力量的毛焰,他们或蜚声文坛多年,或可在具体领域独当一面,且至今均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本诗集收入四位诗人的160首诗歌作品,这是对他们相近又独具特色的诗学追求、诗歌风貌、艺术主张、创作趣味进行了全新呈现。诗集既是对四人诗歌友情的印证,展现出他们诗艺碰撞的火花与迸发的新生力量,又是对“他们”文学流派创作风采的再现,为当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新鲜素材。本书是“他们”诗群全新的一次文学集结,从编选的角度、范围而言,虽未面面俱到,却彰显出四人一致的诗歌审美与艺术水准,也足见他们作为独立的创作个体所具备的鲜明的写作技艺与思想特性,本诗集可以代表“他们”诗群新的创作实绩和创作水准。
《他们》:一些马路空无一人
那个朋友来玩,坐在
他的轮椅上,手脚做着
胜利的动作,像是一个
诡异的确认键刚刚弹起
——于小韦《在康复中心》
善于观察的于小韦是在康复中心的走道上看到鲁羊的,那时的鲁羊推着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的却是鲁羊的朋友:朋友坐在轮椅上,手脚做着胜利的动作,嘴咧得很大——鲁羊推着轮椅和轮椅上的朋友,似乎也感受到了胜利。
他平时亲切地叫鲁羊为“老鲁”,这是一个如鲁羊在前几年写过的一个小说,是一种“亲切的游戏”:本来鲁羊是病人,本来鲁羊坐在轮椅上,本来鲁羊做出胜利的动作,本来鲁羊咧着嘴。但是鲁羊变成了他的朋友,为什么病人的身份会发生改变?按照于小韦的说法,是因为在医生面前,“老鲁的手指按不下确认键”,于是医生也认为“确认的确是很难的事”,但是当鲁羊的朋友坐在轮椅上成为像鲁羊一样的病人,他手脚做出胜利的动作,就像是“一个/诡异的确认键刚刚弹起”,于是他的嘴咧开来,于是像康复了一样。
和鲁羊有关的“亲切的游戏”以病人按下确认键以及做出胜利的动作、咧开嘴而结束。但是于小韦观察了老鲁,又写下了这个“亲切的游戏”,而且还“给鲁羊”的献诗,为什么他始终没有问那个朋友是谁?为什么找老鲁来玩却坐上了轮椅?为什么他会代替老鲁成为病人又让病人推着?“那会儿还是冬天”,《在康复中心》似乎是于小韦自己的一个“亲切的游戏”:老鲁是老鲁,亲切而自然,代替老鲁成为病人的朋友却没有名字,他成为一个无名者。于小韦对人总是很亲切,除了《在康复中心》写到老鲁、献给鲁羊之外,他还观察了毛焰,也献诗给了毛焰:他们一起吃了很长时间的饭,一起说了很多的话,其中说到了达·芬奇,据说他死的时候是“躺在国王怀里的”,这对于于小韦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而现在当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光芒四射的画面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已经不适合作太多的联想,于是,他们在楼下一处无人看管的地方,拼命抽着烟,那根烟头闪着“黄色红色的光芒”。
于小韦把那天的经历写了下来,后来就变成了这首“给毛焰”的《说了很多话的晚上》,也许那天吃了很长时间的饭、说了很多话、又一起说到了达·芬奇的传闻、还一起坐在楼道里抽烟是他和毛焰两个人的事,但是达·芬奇和国王在场,似乎又变成了关于“他们”的一个亲切的游戏。于小韦在康复中心看到鲁羊和他的朋友,在漆黑的楼道里和毛焰一起说话抽烟谈起达·芬奇,总的来说,于小韦和他们的关系都不错,而他自己也一定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很明显,和老鲁、毛焰之间的“亲切的游戏”,总觉得有些“诡异”,病人不坐轮椅却推着朋友,吃饭谈天却说起四百年前的传闻,这是不是如鲁羊一样“按不下确认键”?没有确认键,就是不确认,就是没有必然,就是偶然,甚至就是空无。
“也许不是这样”成为于小韦不确定的象征:我们等来了等待的东西,也等来了没有等待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想过的东西,甚至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等待过它们”,这是《那个等待的故事》,等待的结果呈现出多元性,它们是等待的东西,是没有等待的东西,是不等待的东西,是从来没有等待过的东西——等待本身只是一个行为,它不涉及结果,所以空无也变成了等待的一部分,但是空无不指向等待的物化。这是于小韦的普遍情绪,在喝茶的时候,“一些东西只有一半/一些事物没有时间/我们正在喝两杯绿茶/地点难以描述(《绿茶》)”《正在发生的事》很可能是已经发生,也可能将要发生,“画一张画/等着去展览会上/写一首诗,等着被人/读到,在一本杂志上/一个人造了一个船/还没有被划走”;或者,有些画看不明白,有些字只是认识,有些东西是晚上的食物,有些诗是以后读的,“这个世界和你有关的/事只是一些,这些/是给你的,那些/是给别人的,一些事是上午的/另一些下午才会发生(《一些》)”……
等待是空无,空无也是等待,正在发生是即将发生,即将发生就是正在发生,一些事和另一些事,是同一也是相异……在不能按下确定键的生活中,于小韦感觉这是一个关于言说、关于命名的问题:本来,“他仍然是那个/叫做某某的朋友,那个/叫钟的,还是叫钟”,但是当不能按下确定键,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叫做陌生人,“只是一个/平常的夜晚,陌生句子/藏在黑暗中,一些/人挤在马路上,一些/马路空无一人(《陌生人》)”你和他们被区别开来,他们在马路上坐着乘凉,他们在马路上聊着天,但是你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句子,藏在黑暗中,所以当他们“挤在马路上”,你的马路却空无一人,陌生人变成了陌生句子,陌生句子在陌生马路上,陌生马路上走过陌生人——这是一个闭环式的结构,陌生人就是陌生人的命名,就像叫还是叫钟一样,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是异于“他们”的命名。
所以于小韦故意制造了一些语言的空无,“读着离现实/很远的一些文字”,脑子里闪过的一只猫,是上午碰到的猫,因为是碰到过而被命名为一句诗,“这会儿它径直走过来,会是/另一个陌生的句子”;还有猫掉毛这件事,它发生了,就像那些植物,就像那些昆虫,就像猫吃掉的一条鱼,都是被命名,都不是它们自己要“长成那样”,就像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以及一个叫贝鲁特的地方;还有说到的“遥远”这个词,也是被命名的词语,也是具有自涉的意义,“这是个很不错的词,你在/说它的时候,说的/既是前面也是后面(《遥远是个不错的词》)”还有“战争”,是一个人碰到时的命名,发生在去年和今年碰到的时候,发生在昨天和今天碰到的时候,发生在上午和下午碰到的时候,也发生在活着和死了碰到的时候,连“一个人马马虎虎地刷牙/很难说那不是战争的一部分(《战争和一个人》”……
于小韦在观察,于小韦在说话,于小韦在写诗,于小韦在命名,等待所等待的,看见所看见的,空无所空无的,其实按不下确认键,是根本不需要按下,因为推着轮椅的老鲁也可以做出胜利的动作,也可以咧着嘴,也可以像没有病一样走进或走出康复中心,就像于小韦在《后天》中写道的:“一个东西正冒着热气/一些事叫作后天”选择是一种行为,选择是选择所为,但是选择也是不选择——抛弃苹果选择橙子,抛弃左侧选择右侧,抛弃沉默选择骂人,抛弃素食选择吃肉,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它是空无,它是“一些”,它是陌生,它是命名,它是不确认,它是胜利,它是挤满了人的马路,它是空无一人的马路。
但是老鲁却不这么看。那天他的确在医院,那天他的确扶着轮椅,那天他的确需要胜利的奇迹,但是那天根本没有一个坐在他的轮椅上的朋友。鲁羊扶着轮椅靠墙边站着,他按照医生的建议,是要通过轮椅慢慢学习走路,所以他开始了观察,和于小韦对自己的观察不同,鲁羊观察的对象是从自己面前走过的“他们”,他们是男的女的长的短的清闲的负重的,他们用脚走路也连着脚踝、膝盖、小腿、大腿和臀部,“仿佛这些才是他们的脸和五官”,于是鲁羊扶着轮椅靠在墙边“悄悄移动自己的两只脚”,通过刚才的观察,“忽然觉得那些走路必须使用的关节和肌肉都娇艳地呈现出来”,最后鲁羊想拉着走过去的他们,告诉他们:“走路是件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而鲁羊获得的更多启示是:“我会说,不为人知使这个奇迹更加不可思议(《走路的奇迹》)”
《走路的奇迹》发生在2019年1月3日,鲁羊详细地记录了写作这首诗歌的时间,这是对于小韦某种观察的补充,而这个确定的日期是不是就是鲁羊真正按下的确认键?和于小韦的“空无一人的马路”不同,鲁羊的确想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按下一些确认键:“有些东西即使几乎不存在,也没有真的不存在/即使那是件丑陋的、无名的器物,早已开始松动/却忽然透出意外的真实性/和颇有把握的幽默感(《几乎不存在的器物》)”从不存在到存在,需要的是找到“意外的真实性”和“颇有把握的幽默感”,所以他把生活“真的不存在”看成是一种“据说”:据说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随机的每一天,据说每一天都脱离了理性和情感的序列,据说每一天的触摸都是全新的,据说我们经历的都是浮生——“据说”是他们在说,“据说”是真的都不存在,“据说”没有前因后果,但是鲁羊要把据说变成“我说”,“那样的诗句虽然有些难以理解/却也美如天籁”。
“我说”是因为内心是一座密林,是因为密林中有春天的到来,“这座曾经冰雪覆盖、无声无息的密林/也就在刹那间迎来了它的春天(《密林之春》)”;“我说”是因为想象可以创造世界,“我把那片山坡当作背景/让爱人置身其中/让她去采下那个橙子/让她采到那个橙子,带着水珠/递到我手里(《爱人和橙子》)”“我说”是因为在冥想中开启新的可能,“我必须输在一招不可能的错棋上/我趁你望向远山的那一会儿工夫/用左手食指的指尖轻轻一推//一枚宝贵的棋子就此变成心甘情愿的损失。(《关于左手的微小冥想》)”当然,对于鲁羊来说,“我说”是要确认一个新的自己:山下的我,眺望山顶的我,并用山顶的我的目光看见太阳,看见大山,看见温暖的阳光,从山下到山上,“我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往返/却不知道从哪里到哪里(《往返》)”往返在我和另一个我之间,他们绘制出的“我说”的线路是明确的,是确认的,是解构了偶然、随机和“他们”相关的一切,而这种往返就是鲁羊代替于小韦“亲切的游戏”而完成“走路的奇迹”。
但是,鲁羊也玩了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叫“装扮游戏”,里面的人是老毛——就是毛焰吧?老毛有一个画架,画架上有一幅画,画里是一只鳄鱼,“鳄鱼很假,我们一眼就看出/是亲爱的老毛装扮而成”,这是游戏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老毛的画架前/坐着一条伟大的鳄鱼装扮而成的老毛”,这是游戏的另一个部分。老毛变成鳄鱼,鳄鱼化装成老毛,在双重意义上构成了这个装扮游戏,于是老毛变成了在公园里散步的鳄鱼,鳄鱼变成在在画布中作画的老毛——游戏完成了身份互换?但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二者当中谁会首先脱下面具/结束这次装扮游戏/或者就此合二为”——鲁羊把老毛放进了游戏中,让老毛装扮成了鳄鱼,在没有脱掉面具之前,他们就是彼此的存在,但是当鲁羊在这个“装扮游戏”中设置了“谁会首先脱下面具”的疑问,是不是如于小韦那样面临着一种不确定?显然,当鲁羊在《装扮游戏》中写下“2019.4.29”这个日期的时候,就像他在医院扶着轮椅学习走路而创造“走路的奇迹”一样,用精确到日的时间确认——鲁羊的所有诗歌都标注了写作的日期,和于小韦不同的是,他一直生活在确认的世界里,随手都按下了确认键。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当鲁羊用老毛玩起这个“装扮游戏”,毛焰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在鲁羊写完关于老毛的《装扮游戏》半年之后,也就是2019年10月5日,毛焰写下了关于鲁羊的《题外诗》,那时他们一起吃完了晚餐,准备相互道别,当时双方都提醒“千万别落下什么”,因为,“否则,我们将万劫不复”,当然最后那根手杖伸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朗声说道:“我必须倚杖而行……”这是被标注了确定日期的诗,纪录的是一件确实发生的事,也变成了毛焰“题外诗”系列的第64首——一切都是确定的,手杖接到手上的时候,当然也去除了“万劫不复”的预言——毛焰甚至比鲁羊更确定,因为不仅是自己,甚至连朋友也都避免了万劫不复的结果。
这似乎也是如于小韦一样是一个“亲切的游戏”,因为毛焰叫鲁羊“老鲁”,和于小韦对鲁羊的称呼一样,和鲁羊对他的称呼一样。但是毛焰在那个晚上写下《题外诗》,半年的间隔似乎在呼应着鲁羊的《装扮游戏》:为什么毛焰变成了鳄鱼还栩栩如生?为什么他们们对调了位置还无人发现?或者说,毛焰发出的疑问是:为什么我要戴上所谓的面具完成“装扮游戏”?毛焰很明显对于“自己”有着一些担心:隔着透明的塑料,通过两只猫的视角发出疑惑:“对面的/究竟是我的同伴/还是那个无法修复的自己(《下午的某一刻》)”所以他的《和自己说》里有着太多的隔离感,自己呆着的时候喜欢和自己说话,看起来是一种“便宜而隐秘的乐趣”,但是一个想要说个明白,另一个却想躲开,一个说“愚蠢”,另一个表示赞美,这是“处于两极的观点在某时集于一身”的自我,对自己说其实不如是成为一个哑巴一个盲者,“只剩下一种意义,便是接近虚无(《只剩下》)”
毛焰显然是在这种“只剩下”的虚无中找寻另一个对话的自己,所以他写了“剩山图”系列,写了“题外诗”系列。在《剩山图》里,他用各种交错、更替的圆圈将空隙填满,然后期待光从斑驳琐碎的缝隙中投射下来,“无穷无尽的影子,黑金一般地洒落”;他希望白昼成为黑夜,就像自己成为另一个自己,“让它们归回自己的来处,无踪迹可寻”;在《题外诗》中,他通过梦让一个人“继续沉睡”,像一个婴儿或孤独的死者,而醒来便是重逢;他把一扇门之外的世界看成是迷途,走进去绕着是忘记了进去的目的,“只有出来,才想起要找的/原来是自己”;即使门打开,前面是无法预判的风景,即使“我们朝向各自的方面”,也是一条平行线上的呼应。所以在面对晚餐结束时的老鲁时,相互提醒千万不要落下什么,一根手杖接过,或许两个人都可以“倚杖而行”——甚至不是两个人对彼此的确认,而是诗人和手杖之间建立了关系,倚杖而行就是相互确认,就是不进入所谓《装扮游戏》,就是一起拿下面具。
于小韦写到了老鲁,写到了毛焰,鲁羊补充了“在康复中心”的经历,写到了老毛的“装扮游戏”,毛焰也写到了老鲁,三个人构成了“他们”,但是也是“他们”中一员的韩东在干什么?韩东在看“电视机里的骆驼”,“我的心思也变得软绵绵毛茸茸的/就像那不是一只电视机里的骆驼/而是真实的骆驼。/它当然是一只真实的骆驼。”韩东在《马尼拉》思考一匹马是不是应该变成马的雕像,“解放这可悲的马/结束它颤抖的坚持/结束这种马在人世间才有的尴尬、窘迫。”韩东吃到了很甜的果子,为了寻找“比很甜的果子还要甜的果子”,他把一筐的果子全吃光了,夜晚,“果子消失/果核被埋进黑暗/那个比很甜的果子还要甜的果子/越发抽象。(《很甜的果子》)”所以韩东没有和于小韦一起吃饭,没有看见鲁羊在康复中心,没有发现装扮成鳄鱼的毛焰。他似乎是一个人,他看见拿着“长东西”走楼梯的人,没有人提到他,“那个人继续走着/带着那件被汗水擦亮的长东西/暂时与世隔绝,并逐渐从深渊升起。(《长东西》)”他看见医院的楼宇之间一些人走着,一些人躺在病床上,一些带轮子的担架在楼道里滑行,“所有这些走着或躺着的人/都是在经过这里时不慎跌落的。(《在医院的楼宇之间》)”他也看见在殡仪馆哭着的女人,“她递过来一块手帕——这太过分了!/那里的手帕也不是手帕/只是事实的一片灰烬。(《殡仪馆记事》)”
他看见,他思考,他写下,韩东更多关注的是那些生死故事,尤其是近旁的亲人,比如父亲,“我很想念他/但不希望他还活着/就像他活着时我不希望他死。/我们之间是一种恒定的关系。”这种恒定的关系是爱,所以“爱真实就像爱虚无”,“我对自己说/他就在这里。在石头和头顶的树枝之间/他的乌有和树枝的显现一样真实。(《爱真实就像爱虚无》”比如母亲,“爱得这样洁净,甚至一无所有。/当她活着,充斥各种问题。/我们对她的爱一无所有/或者隐藏着。”但是真正的爱就像母亲对我们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爱一个活着的母亲/其实是她活着时爱过我们。(《我们不能不爱母亲》)”比如曾经爱过或被爱过的人,“喜欢她的人死了/剩下的只是她喜欢的。/我也不会和她回到从前/打牌一打一个通宵。(《喜欢她的人死了》)”韩东就像那个诗人,写下的是:“到处都是离开家的路”,他也知道,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带你们回家。
韩东流露的是“悼念”的情绪,消失、遗忘、死亡都涌了出来,所以那是一个对韩东来说“乌有”的世界,“四十岁到六十岁/这中间有二十年不知去向。/无法回想我五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是何模样/甚至没有呼啦一下掠过去的声音。”被抽离的时间,被消失的年纪,朋友打电话说起被抛下那列开往北方的火车,韩东再次感慨:“甚至这件事也发生在我四十岁/他三十多岁那年。(《时空》)”从三十到四十,从四十到五十,从五十到六十,十年的整体性时间都变成了乌有的存在,大约是老了,而这种情绪和于小韦“按不下确认键”,鲁羊的“装扮游戏”,毛焰的《剩山图》有着共同的感受,这是属于“他们”在转变和不转变中的心情,这是和“他们”诗人相关必然其实是偶然的诗意,空无或者就是“有”,乌有或者也是“无”,于是,于小韦、鲁羊、毛焰和“心儿砰砰跳”的韩东一起,四个人组成的“他们”走在疫情开始之前“空无一人”的那条马路上: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
往草场走
离草场已经
不是很远了
不知道他们去那儿干吗
没见到他们,否则
你可能是他们
队伍中的第四个人
——于小韦《你们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