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1 那些像灰尘的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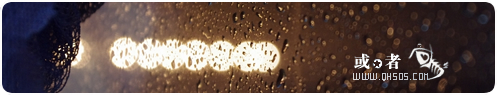
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标志,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路是充满灰霾的,在夜晚灯光的照耀下,尤为明显。而汽车制造的灯光仿佛不是为了看清自己前方的路,而是为对面的车制造一种眩晕的感觉。独立在一个龋龋独行的世界里,夜一下子被缩小,乃至所有通向远方的道路,都被压缩在眼前的寸步之行。
夜晚九点,我去往的是城市边侧的那个地方,路是陌生的,黑暗也是陌生的,我像一个闯入者抵达没有诗和远方的存在,并不是害怕在无人经过的道路上,一种灰霾的覆盖会让我变成如尘土一样的颗粒,而是在这个距离现实太远的城市里,原来我一直就不被明亮的灯光照耀。道路交叉,拐弯,甚至是弧形的环形岛,都是通向一个终点,而终点其实也是起点,在大门口停下,打电话,等待,然后有些惊喜地看见,然后便是离开。
是见到了“老虎”。这仿佛是最后的叙述,而在这陌生的道路开启夜晚之行之前,有许多故事是片段地展开的。先是很突然地接到“老虎”的电话,也是陌生的号码,手机更换之后,原先的信息荡然无存,所以在陌生的号码被接听之后,我也一直以为是一次错误。但的确是他的声音,时间太久了,却没能改变我们身体里的一些属性,包括声音和语调。因为一次公务活动,他将来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我是在惊喜于一种默然之后的突然到达,将时间和空间都压缩在几分钟的通话里。再然后是准备他需要的一些材料,而再然后却也是各自在自己的城市里,相安于各自的生活规则。
而今天下午在偶尔翻看微信的时候,才知道“老虎”和党政团已经来到了我的城市,而且正在汇报,正在会议。白天的事物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他的身份,他的工作,无论如何是无法脱身的,所以当夜晚以规矩的方式降临的时候,我必须从一条陌生的道路驶入,抵达一个不应该陌生的故事。十年,或者十五年,总之,时间被拉得太长,即使两个人终于见面,也总是觉得以很小心的方式才划入到相同的夜。以及,被覆盖在相同的灰尘里——夜制造的暗处里,其实是看不清那脸上的皱纹,只是在时间必然的行走中,大家会心领神会于一种岁月的改变,苍苍,是灰霾里的表情。
一个寝室的过去,一段往事的回忆,有时候会显得太过凌乱,没有完好的片段,最后只是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被激活,像是可以安然回去了,在被叫做青春的日子里想念高低铺的逼仄,想念4088的拥挤,想念一次爬山的激情。可是,这想念却也是被灰尘覆盖在不曾翻阅的日历里,转身从那条路出来,即使手捧着那一杯清茶,也无法看清自己在漫长的时间里走过的那些路。从公务员到镇街干部,再到区里商务局一把手,这是“老虎”的政治履历,其实在这个相遇的夜晚,在这个布满灰尘的城市,完全剔除了好而工作有关的身份,只是坐在一起,聊一些话,重拾过去的片段,或者也可以叫做人生。
不在一个城市,是不是就是遥远的距离?三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西北面,或者东南面,地域之隔不像是一种阻力,但是当我们囿于自己的生活,囿于无力改变的现实,其实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看不见的城市”,都在一种时间和空间制造的隔离中彼此分离。“老虎”打给老马的电话,在响铃之后传来的是“对方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的声音,一种设定的告示取代了亲切地叫一声“喂”;“老虎”给吴巍峰打的电话,是真实的声音,却隔着另一个城市,以及另一种生活,所谓应酬,也是夜晚被灰尘覆盖的无奈;或者还想起了阿柳,三年的援疆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那个更为遥远的城市,只是在“应该已经结束”的猜测中不忍打扰他的夜晚。
原先都是我们,而现在在每一个看不见的城市里,都变成了他,他,他以及他,一个寝室,一种生活的集合,是容易被分解的,甚至变成了碎片,和灰尘的灰一样,飘荡在夜空的虚幻中。虽然“老虎”提议大家相约在今年的夏天,一起聚首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是时间向前延伸,每一个人,他,他,他,以及他,并不一定跟随时间的必然节奏,并不一定在集合的世界里完成对于记忆的鲜活重现——有时候,近也是远,整体也是个体,未来看得见也是看不见。
明天离开,“老虎”只是以经过的方式,在有限的时间里,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划出另一条轨迹。像是一种必然的返回,送他回去之后,再次行驶在陌生的路上,再次在被缩小的夜里,再次在灰霾覆盖的城市里,其实明天就是一个虚拟词,它是想象,是传说,是强迫自己确认可以抵达的终点。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79]
顾后: 《圣殇》:死亡的三种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