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1《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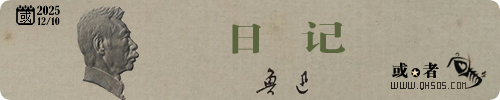
十八日 星期。
只有日期,只有星期,没有天气的记录,没有得信复信的记载,甚至曾经最常见的“无事”两个字也没有写下——几个小时之后,鲁迅逝世,当鲁迅在临死之前记下最后的日期和星期,即使简略,也成为一生最后的文字记录,而那个句号分明是鲁迅对这一日常叙事文本最后的交代,这个“是给自己看的”的日记也许也是鲁迅在最后一眼的回望中完成了对人生的定格。
而从最后的日记回溯,这一年的鲁迅被疾病所缠,他的文字也记录了最后时光的生活片段:六月一日他写道:“又发热。”五日写下了:“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这是六月三十日下午补记的日记,在从五日到三十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鲁迅被病魔折磨,这也是他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了北京继续日记之后二十四年来第一次中断,已经“日渐委顿”,已经“艰于起坐”,甚至对于是否继续记日记也没有了信心,但是稍微好转又继续记录:从七月开始一直到十月十八日逝世前一晚,鲁迅都没有中断,即使七月的日记中“每天须藤先生来注射,又发热”,八月七日写道:“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问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十三日:“须藤先生来注射。夜始于淡[痰]中见血。”九月几乎每天注射,十月一日体重只有39.7公斤,夜晚又发热到三十七度九,十月十日发热到三十八度,但是十月四日的日记上记着:“鹿地君及其夫人来,下午邀之往上海大戏院观《冰天雪地》,马理及广平携海婴同去。”十月十日又和许广平携海婴并邀琈理去上海大戏院观《Du_brovsky》,晚上还为《文艺周报》做一千五百字的短文一篇,在逝世前的十七日,还收到了崔真吾、许寿裳、曹靖华的信,还回复了他们的信,还拜访了朋友,还去了内山书店,还接待了朋友和弟弟周建人……
这些事情都被鲁迅记载在日记中,它们在叙事上是完整的,而这也是鲁迅对日记的一贯作风,他曾经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因为“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日记对于鲁迅来说,就是“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性的存在,这种“非公共性”正是区别于他的文章之所在,即使不是一种隐秘的文本存在,对于鲁迅来说,也是“自我”的无遮状态,所以鲁迅拒绝日记被围观,有次被亲戚看了之后,鲁迅大发雷霆:“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翻过了,这很讨厌,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莫非他以为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么?”
这是完整的私密世界,所以鲁迅在日记中很少触及社会时政,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日记中很少被提及,五四运动那天记有“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五卅运动那天记为“上午访季巿。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三·一八惨案”那天记有“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而1927年4月12日的日记缺记,仅有天气。而和自己有关的一些重要事件节点,鲁迅也只是简略地记录。一九一二年,鲁迅受蔡元培邀请成为教育部部员,五月五日,三十二岁的鲁迅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开始他十四年的“京官”生涯,他的日记也从这时开始保留下来。那一天的日记写道:“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第二天的日记写道:“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蜰虫三四十,乃卧卓上以避之。七日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后鲁迅脱离教育部,七月一日张勋拥戴溥仪“登极”,七月三日鲁迅愤而去职,为此赴部与同人告别,当日的日记鲁迅只有寥寥几字:“雨。上午赴部与侪辈别。”一九二六年发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鲁迅参加了刘和珍和杨德群的追悼会,三月十五日的日记写道:“晴。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同一年鲁迅离开北京去往厦门,日记写道:“三时至车站,淑卿、季市、有麟、仲芸、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七时半抵天津,寓中国旅馆。”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乘船离开厦门抵达广州,日记写道:“昙。晨发香港。午后雨,抵黄浦〔埔〕,雇小舟至长堤,寓宾兴旅馆。下午寄淑卿信。晚访广平。”一九二七年“四一五事变”发生,十六日鲁迅赴中山大学参加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当日日记写道:“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十月三日抵达,日记写道:“晴。午前抵汕头,下午启碇。”
和记载与自己有关的重要社会事件简略写法一样,鲁迅对于和爱人、家人有关的大事,在日记中也是一笔带过,到北京之后鲁迅和二弟、三弟保持联系,他还标记了和兄弟通信的数字,后来他向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于是和二弟同在北京,己未日记十一月二十一日写道:“晴。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鲁迅是日迁居八道弯宅,至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移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共住此三年又八个月,当年十二月返乡迁家至北京:“二十四日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鲁迅记录了和二弟同去东安市场、东交民巷书店、山本照相馆,但是之后和周作人关系破裂,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并没有过多提及兄弟关系破裂的事情,“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成为这一变故的心情表达,而反目之前的“二弟”之后成了陌路人,鲁迅称他“启孟”,十九日的日记写道:“昙。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此后甚至连“启孟”而已很少提及。而实际上,鲁迅对于许广平、海婴的记载在日记中也一样不含过多的情感,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在日记中他写道:“晴。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晚上则是和许广平、三弟去吃饭,然后去百星戏院看戏,这便是鲁迅对人生重要同居生活的记录;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生,鲁迅日记写道:“晴。晨八时广平生一男。”孩子出生只有寥寥八个字,后来给孩子起名、接孩子和许广平出院、拍百日照、六月照都是只有几个字。
鲁迅的这种文风只为一种记录,所以在日记中几乎没有过多的感情流露,当然也没有如杂文中的那些议论:壬子日记七月十九日,因为得知范爱农死了,鲁迅表达了悲痛:“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一九一二年九月观月食,有过一段议论:“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盘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议论道:“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鲁迅和林语堂交恶,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九三三年,二人皆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开始恢复交往,后又渐热络,二月十九日鲁迅日记写道:“晚得语堂信。”二十一日写道,“上午寄林语堂信并稿一篇”,二十七日,“下午往语堂寓。”双方关系开始全面转圜。
少有抒情,鲜有议论,鲁迅的日记记下的便是收复信、观剧、购书、饮酒、会客等,有时最简单:“晴,大风。无事。”或直接两个字:“无事。”但是作为私人文本,从鲁迅日记也能发现一些线索。鲁迅喜欢美食,尤其在北京的那段时间,粗略统计鲁迅早期记于北京的日记中所提到的饭馆名目,大概有六十五家之多,其中既有北京市民阶层所谓“逛小市,听小戏,吃小馆”的“小馆”,也有诸如“同丰堂”之类可做地道满汉全席的高级大饭庄,北京的各大饭馆,鲁迅去得最多的就是位于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一九一五年九月十日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晚齐寿山邀至其家食蟹,有张仲素、徐吉轩、戴芦舲、许季上,大饮啖,剧谭,夜归。”“大饮啖,剧谭”五个字传神地描绘出当时聚友食蟹的酣畅淋漓之快感。鲁迅也喜欢干鱼、风鸡、腊鸭等家乡味道,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鲁迅记道:“午后钦文来,并赠兰花三株,酱鸭一只。”
鲁迅也喜欢买书,每月必有书帐,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买书的情况。鲁迅买书不大挑剔,一九一三年一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留黎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检,因以五金买之。”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写道:“上午书贾持旧书来,绝少佳本,拣得已蠹原刻《后甲集》二册,不全明晋藩刻《唐文粹》十八册,以金六元六角买之。”明明知道绝少好的版本,却还是挑了已经蛀坏的和不全的两部书买下来,花的钱还不少。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鲁迅是这样过的:“……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想买书,又嫌贵,却又不甘心,竟一连逛了十多家书店!二月八日写道:“……同至留黎厂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甚多。出观书店,买得新印《十万卷楼丛书》一部百十二册,直十九元。其目虽似秘异,而实不耐观,今兹收得,但足以副旧来积想而已。”书多了,也会笑自己,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六日日记中说:“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即使身体不适也要看书,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日日记写道:“星期休息,腹仍微痛。终日订书,计成《史略》二册,《经典释文》六册。”头天晚上他肚子“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而第二天竟然在肚子仍在微痛的情况下,装订了一整天的书,第二天又“晚丁《经典释文》四册,全部成”,二十六日更加入魔了:“夜修订《述学》两册,至一时方毕。”装订两册书,到半夜一点才完成,简直痴迷了,接着十一月三十日有这样的记载:“自二十七日起修缮《埤雅》,至今日下午丁毕,凡四册。”
在购书阅书中,其中很多是佛学相关,许寿裳曾经说过,“鲁迅从民三开始,研究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写道:“梅君光羲贻佛教会第一、第二次报告各一册。”这是鲁迅对佛教书籍的第一次记载。到十月十九日,又是梅光羲 “赠《佛学丛报》第一号一册”,第二年四月七日,友人许季上赠《劝发菩提心文》、《等不等观杂录》各一册,九月十六日鲁迅就寄给了在绍兴的周作人,同年,鲁迅还买过《大唐西域记》和《释迦谱》四册。而鲁迅真正投入地大量阅读佛教经典,是从一九一四年四月开始的,鲁迅十八日记着:“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又去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共银六元四角又九厘;五月十五日,鲁迅再往琉璃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中观释论》、《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住毗婆沙论》等;三十一日,又往有正书局买《思益梵天所问经》、《金刚经六译》、《金刚经、心经略疏》、《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八宗纲要》。这里主要涉及《金刚经》和《心经》,同时也关注全部八个主要宗派;似乎是一个多月的读经已经让鲁迅欲罢不能,六月三日,鲁迅“下午往有正书局买佛经论及护法著述等共十三部二十三册”,其中包括《大乘起信论》三种、《发菩提心论》、《破邪论》、《护法论》、《折疑论》、《一乘决疑论》等著名经典;过了三天,鲁迅又买了《心经、金刚经注》等五种六册,《贤首国师别传》、《佛教初学课本》各一册;七月四日,鲁迅又买了《四十二章经》等三种合本、《贤愚因缘经》,这次距离上次买经已近一月;十一日,又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因果经》、《楼炭经》、《四谛》等七经合本、《阿难问事佛》等二经合本等——前后八个半月中,他已经购买了佛教书籍一百三十六种二百三十六册,几乎接近每天一册!
鲁迅日记中,还有一个关涉私人性的话题,那就是和马珏之间的关系,马珏是浙江鄞县人北大教授马幼渔之女,一九二六年为孔德学校学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春在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预科学习,一九二九年春转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鲁迅最早提及她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的日记中:“往孔德学校访品青未遇,留书而出。……寄赠马玨小姐《痴华鬘》一本。三日:夜得马珏小姐信。”马珏在十五岁时遇到鲁迅,她写的《初次见鲁迅先生》在期刊上发表,为了表示亲切,鲁迅还给马珏专门起了一个外号“仲服”,这是鲁迅对马钰独一无二的称呼,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鲁迅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提到和马珏收信回信送书,一九三三年三月,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鲁迅得知后,心内微微惆怅,三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幼渔告其女玨结婚柬。”这是他在日记中最后提到马珏,而与马珏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鲁迅的一个隐秘故事——在鲁迅的信件中,并无关于和马珏的任何书信,也许这书信除了寄给马珏,也成为“只给自己看的文本”。
而在鲁迅中,构成私人性文本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对自己肉身的关注,从初期的“夜半腹痛”“夜胃小痛”“夜齿大痛,不得眠”“咳,似中寒也”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身体并不十分健康,而且还喝酒吸烟,喝酒也常常喝醉,所以鲁迅总是在发病时提醒自己,壬子日记八月十七日写道:“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但是十九日又喝酒了“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和周作人决裂后,因迁居劳累和气愤致肺病复发,次年三月转愈,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写道:“下午访齐寿山,还以泉二百。咳嗽,似中寒。”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鲁迅写道:“肋间神经痛,服须藤先生所与药二次。”十日出现发烧症状,之后一直到十二月二日,连续半个月记下晚上九时的体温数字。而到了一九三六年,身体每况愈下,一月三日写道:“夜肩及胁均大痛。”二月二十三日写道:“改造社作文一篇(即《我要骗人》),三千字。不睡至曙。”四月三十日:“作杂文一篇(即《<出关>》的关》)。失眠。”五月十五日:“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
“自三月二日往藏书室找书,因中寒骤患气。喘,经延医疗治,至三月中旬小愈。是日起又现病状,十六日后连续发热并气喘。自此日见沉重,医生断为肺结核与肋膜炎之并发症。”这是鲁迅大病之始,十八日的日记写道:“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之后日记记录体温,均为发热,五月三十一日:写道:“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明甫译语。胡风来。须藤先生来诊。夜烈文见访,稍谈即去。九时热三十六度九分,已为平温。”但这并不是好转的迹象,终于在劳累中,在发热中,在委顿中,慢慢走向了生命终点——十月十八日的“星期”两字和一个句号,是鲁迅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也是鲁迅这个私人文本“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最真实也最让人泪目的印记。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