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04 4.9公斤的初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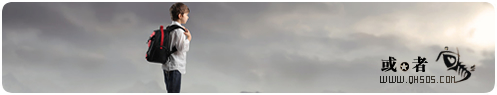
我起初是这样描述场景的:晴朗,蔚蓝,在初冬的布景下,银杏叶一片一片掉落下来,萧杀的季节,完全是泛黄的色彩,没有风它也是那样的姿态,从飘落而至坠落,沉重的样子,这是对一片泥土的皈依,是对大地的回归。而到最后,树上面一定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条的简笔画,而树下的银杏叶铺陈在那里,开始接受腐朽的命运。
这可以不是场景,只是每次经过那两株银杏树的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忧愁,树叶掉落,就在那里真切地发生着。本来就牢牢长在那里,却看着它们从枝干上落下来,不是挣脱,像是被狠狠地推出来,无奈地离开树枝,跌落在地上,命运戛然而止。我说的是作为一棵树的命运,至此终结。接下来,在泥土里腐烂,成为新的泥土,等待第二年以养料的方式再次回到树上。
沉重的代价?对一片银杏树叶的过度诠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往往是沉重,那种脱离大地的轻何尝不是更大的沉重?因沉重而掉落,因沉重而弯腰,因沉重而腐烂。是的,这初冬的场景完全是关于沉重的一个隐喻。
4.9公斤。这是小五书包的重量,毛重。早上上学去之前,我认真打开书包,拿出里面所有的课本、练习、讲义,整理一番,在充分尊重小五的选择基础上,只拿出了几本笔记本没有再放进书包,放在电子秤上称重,数字显示4.9公斤,10斤不到。这个重量在手上已经有些沉沉的感觉了,那些必须装进书包里的就是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美术、音乐等等教材、数本辅导书和讲义,以及练习册。问小五,有些今天不上的科目教材是不是一定要放在书包里,小五说,要的,万一课程有变化呢?也就是说这是小五上学必须的重量,如果剔除书包本身,以及水杯、红领巾、安全帽等的重量,那么书本的“净重”就可能超过4公斤。
小五书包一直没有准确地进行称重,这几天才忽然觉得有些沉重,但其实也不是拿在手里的感觉,是因为忽然就觉得小五的作业多起来了,甚至到了“理解不了”的程度。昨天的回家作业,放学时在单位里做了40多分钟,以为接近尾声了,没想到吃过晚饭回到家,继续在自己的房间里“鏖战”,从语文到数学,再到英语,等他说全部做好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也就是说,所有做作业的时间加起来,有3个小时。如此漫长的作业时间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检查作业的时候我才发现,回家作业里,语文的作业量有些超乎预料的,比如抄写词语,石新学的课文的主要词语,大概20多个,一个抄两遍,还有句子,大概4句,也是两遍,还有背课文,全文背诵。除此之外,还有课外讲义里的一些古诗歌。算下来,光语文就做了一个半小时。
小五本来做作业也不是很快,加上语文几页纸的作业量,自然要花费3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了。其实,这一个学期,对于语文作业还是有些微词,几乎每天都布置得满满的,听写、抄词语、组词、背课文,一切作业样式看起来都如此熟悉,仿佛是面对曾经的我们,几乎都是死记硬背的,问小五刚抄好的一些词语,竟然有几个不解其意,纯粹就是手上的劳动,也只是纸上留下些印记罢了。死记硬背的教学,不想过了几十年还会在小五身上发生,而且语文老师还有一个绝招,比如在父母检查完并签名的孩子作业本里发现错误,不仅孩子要重新订正每个词抄写3遍,而且父母也要抄写,数量则是孩子的十倍,也就是30遍;如果第二次还是没有检查出,学生依然是3遍,而父母则变为60遍。似乎闻所未闻,本来以为只是给父母的“警告”而已,只是保留在学校的短信通知里,但其实真的付诸了实践,很多家长为此像孩子一样,甚至比孩子更要“认真”地抄写30遍或者60遍。
绝非耸人听闻,对于这样的“惩罚”的确有点匪夷所思。这举措的出发点当然是让父母承担教育的责任,但是如此“连坐”的惩罚实在有些矫枉过正,而且似乎太急功近利,孩子的教育并不是单纯是父母的责任,还有学校、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责任,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老师当然也难咎其责。
回到小五书包重量本身,有时候实在有些无语,从一年级到现在,书包每个学期都在加重,这是不是伴随着成长必须增加的重量?我不知道。看着小五一天天长大,其实更多的忧虑反而显现出来,比如学习的自觉性与趣味性,比如看待成绩需要多少的理性和多少的感性,又或者按部就班会不会扼杀游戏的本性。如此,其实都是没有答案的疑问,而当早晨的“目送”也变成了他独自上学,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一次成长。
“事实是,教育正不可避免地变得没有人性。”这句话虽然可能偏颇,但实际上对于教育真的会越来越茫然,这种茫然一方面是教育的方向性,无从下手,也无从突破,只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前行,几乎没有理论的探讨,所有的一切都在实践中,所以这样的实践必定是带着一种冒险精神,前方永远是未知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大抵如此,但是万一前面没有石头呢?另一方面,对于孩子的学习生活也几乎是茫然的。小五很少会讲学校里与同学发生的故事,和谁好或者谁不好?上课心情如何?等等,几乎和幼儿园时一样,对于他的世界,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最多也只是从班级QQ群中了解到一些。
不能承受的重,是书包的分量,还是成长中未知之重?初冬的那些下坠的落叶并不一定是诗意的,它们是在沉重中抵达命运的成长终点,而场景里的那些树叶,那些布景总是会转换成另一种风景,可是必然要经过腐烂的阶段。而重新成长的时候,已不再是初冬,而是春天。
“成长——在其深刻之处——永远也不会改变:会变的唯有它的布景。”我偷偷改了某一个词,就像从4.9公斤的书包里悄悄拿出了不必要的本子和书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