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8大象从不席地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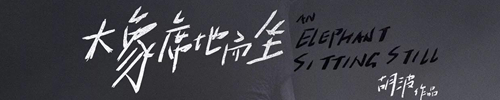
“世界在什么上面?”我问。
“在一只大象上面。”他说。
“大象在什么上面?”
“在一只乌龟上面。”
“乌龟在什么上面?”
“在一台红色剪草机上面。”
——巴塞尔姆《看见月亮吗?》
等等。
如果目光向上,依次经过红色剪草机、乌龟、大象和整个世界,那个最上面是不是站着一个不动声色的上帝?但是其实真正串联起一切的目光是必须向下的,一层一层,经过横向的书本,经过竖向的故事,最后一定在一种必然呈现的东西上面落脚。
踮起脚来看世界,就是在大象上面踮起脚,只不过后来换成了一本笔记本,如上的句子在“等等”之前都被写了下来,这样一来,上面和下面,支撑和压迫,都没有了物体本身的意义,而书写下来的时候,红衣主教一直在阐述价值:“如果有任何价值具有价值,那么它必定处于发生并且是这情况之物的范围以外,因为发生并且是这情况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定不能忽视最上面的上帝,一定不能忽视主教说偶然性的隐喻,当然,也一定不能忽视作为一头大象和一头乌龟同样的命运。
巴塞尔姆的60部短篇小说,像一种纸页摊开的秩序,叠加在每一种笔记本之上,但是没有看见乌龟,没有看见大象,当然也没有看见月亮。看不看得见月亮,其实都不是一种选择,当“脚趾伸到危机四伏的月球环境里去”的时候,那个“月球敌意研究”的人始终没有离开温暖安全的胶囊,所以最后都变成了浪费时间的行为,甚至变成了一种偶然性——抬头看天是偶然,踮脚走路是偶然,打开放在最上面的书是偶然,那么,价值的意义就是“任何价值具有价值”。
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语法调用,其实像是一种回归,而在日常故事里,一直遵循着这种回归,在没有月亮的日子,在分崩离析的故事里,独自寻找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目光。是打着伞的,从一个可能的方向走向另一个可能的方向,其中充满了偶然性:比如在路上会遇见一两个认识但记不起名字的人,会和从来不认识的人擦肩而过,会从突兀出一角墙体的路中经过,也会不慎从储满水的人行道上踩踏下去……是不是无数个偶然会成为偶然的整体?是不是没有价值会变成唯一的价值?
地面之上是一双几乎淋湿的鞋,鞋之上是正在行走的身体,身体之上是一把骨架锈迹斑斑的伞,伞之上呢?一朵朵雨正在盛开,雨之上,是一片没有任何立体感觉的天——天在天上蔓延,天吞没了天。别无他物,是从来不会看见月亮的,一种幻想也丝毫没有了可能,所以从下而上,其实建立的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偶然性在膨胀,最后连同撑伞出行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是一个人在夜晚,何以被命名为价值?
甚至,不温暖,也不安全,就像另一个环境,充满了敌意。雨水带来的寒意像是具有某种季节意义,一个被浸泡在水里的城市,总是希望能有阳光盛开时的一跃,但是跃向何处?依次经过剪草机、乌龟和大象,其实世界最后空空如也;或者像雨水一样滴落于地而成为最下面的存在,于是散乱,于是飞溅,于是水之为水,从来不离开卑微的现实。高处和低处,都以如此必然的方式解构了价值的偶然,还有什么能让人保持一种行走的姿势?
目光平视,既不看见天也不看见地,既不命名上也不命名下,我在中间,以一个游走的身体为标志,偶然而必然,在展开的过程中独自寻找秩序。听说了很多的故事,凄惨的,悲伤的,欢愉的,或者诡异的,都在他处发生,只是听说,便不用系在笔记本里。当然,后来就忘记了,没有了名字,没有了性别,于是,整个城市都缺少人物,在空空的街上,只有挖掘机停顿在那里,下面是一摊扒开的泥,上面顶着一爿苍茫的天。
无法拒绝的是上和下的空无,宛如废墟,在雨水的浸泡中,在大地的沉寂中,一个直行的人,和一条直行的街,组成的垂直体系,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组合——垂直的角度最后却变成了tan90°,一个符号?写在那个笔记本里,打开,却是一种被戏谑的无意义。于是,和无月的夜晚一样,不用踮起脚,不用仰视,谁都无法跨越一片狭长的海峡,谁都无法度过漫长的230分钟,谁都无法消弭生与死的距离,谁都无法绑架“一点也不能少”的故事:
——你知道满洲里吗?我准备去那,那里坐着一头大象。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