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3《敌基督者》: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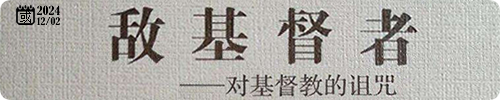
我们的幸福公式:一种肯定,一种否定,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1》
肯定是否定之后的肯定:肯定是诅咒之后的意志,肯定是颓废之后的新生,肯定是败坏之后的自由,肯定是谎言之后的真理……在诅咒、颓废、败坏和谎言之后,肯定而走向幸福,必定是在走向终结之后新的出发,而那个终点被尼采清清楚楚写在人类的履历之上:人们总是根据“不幸的日子”来计算时间,当灾祸发生,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当大洪水制造了人类灾难,基督教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人类救赎的时间,但是尼采问道:“为什么不从它最后一天开始算呢?”也就是说,要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
基督教的最后一天,在尼采看来其实也是第一天,今天是当下的第一天,所以必须在在墙上写上对基督教的永恒控诉开始:“我称基督教为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巨大的内在腐败、一个巨大的复仇本能,对于这种本能而言,没有什么手段是足够有毒、足够隐蔽、足够秘密、足够小人的,——我称基督教为一个抹不掉的人类污点……”当尼采把基督教称之为“巨大的诅咒”“巨大的内在腐败”“巨大的复仇本能”,以及“抹不掉的人类污点”,其实就是将基督教推向了和人类本身为敌的位置,当基督教和全体人类的本性为敌,尼采也不再是一个对基督教发出诅咒的单一的人。
因为“我”已经变成了“我们”——一种复数的存在,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自己”,是因为我们切勿低估了我们自身和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已经是一种“重估一切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活生生地在向所有关于“真”和“不真”的古老概念宣战——我们已经结合成一体,我们就叫做“自由精神”:“只有我们,我们变得自由的精神,才具备条件去理解十九个世纪以来遭受误解的东西”,这是一种交战:本能与激情的真诚和“神圣的谎言”交战。但是,“我们”到底是谁?尼采说,我们是在基督教面前变得郁郁寡欢的人,是被称为“宿命论者”的人,而这样的“我们”也被称为人们:人们是必须在“精神事务上诚实到严力的地步”的人,人们是必须“习于在高山上生活”“俯视政治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可怜废话”的人,人们是“必须得漠然,从不问真理是否有用,是否会给一个人招致厄运……”的人……
或者说,人们就是那些能理解尼采这个“我”的人,理解而结合,便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自由精神,一种否定之后的肯定,一种终结之后的新生,在《序言》中,尼采列出了能读懂他的那些“我们”的条件:我们是少数人,我们生活在遥远的极北净土,我们偏爱面对问题的力量,而且要有勇气去追问,要直面禁区的勇气,要通往迷宫的宿命,“源于七重孤独的体验。聆听新音乐的新耳朵。观看最遥远之物的新眼睛。对于迄今为止保持缄默的真理具有新的良心。还有求伟大风格之经济学的意志:同时保有它的力量和热情……对自己的敬畏;对自身的爱;面对自己的无限制的自由……”力量、勇气、孤独、聆听、观看,以及良心、意志、热情、敬畏、爱和自由……这些都是尼采赋予那些能理解他的读者的定义,“好啦!只有这些人才是我的读者,我真正的读者,我注定的读者: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
一种关系建立起来,只有那少数的“我们”作为读者能理解并且结合成同盟,才能通过藐视超越人类之上,因为在“我们”之外都是其他人类,“也许,他们当中甚至还没人活在世上。”而且,“其他人只是人类罢了。”活在世上或者不活在世上的人类,在尼采看来,他们就是生物序列中的人类,而这样的人类就是一个终点,就像作为“一个巨大的诅咒、一个巨大的内在腐败、一个巨大的复仇本能”的基督教一样,已经走向了它最后一天,他们就是颓废的人,“我的断言是,所有总结了当今人类之最高期望的价值,都是颓废的价值。”他们就是败坏的人,“当一个动物、一个种类、一个个体失去了它的本能的时候,当它选择了、当它更喜欢对它有害的事物的时候,我就称之为败坏。”他们就是没落的人,“在我看来,生命本身就是求生长、延续、力量积聚和权力的本脂:凡是缺乏权力意志的地方就有没落。”他们甚至就是偏离了生命本身的人,“人是动物之中最失败、最为病态、最危险地偏离了本能的一种”——如此种种,是因为,人们已经把生命的重心放在了生命上面,并且将其转移到了“彼岸”,而这种彼岸便是虚无,当被夺取了生命的重心,何来力量、勇气、孤独、聆听、观看?何来良心、意志、热情、敬畏、爱和自由?他们在一种叫做“纯粹精神”的东西里颓废、败坏、没落,最终成为“纯粹的愚昧”,失去生命本来的意义。
| 编号:B82·2200415·1637 |
“对基督教的诅咒”,尼采就是要在这终点开始否定,“必须通过力量、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就是从今天开始“重估一切价值”——一种否定和一种肯定,让发疯前的尼采成为一个“敌基督者”。肯定和否定,其实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区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好就是“一切提高人类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东西”,而坏则是“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基督教就是“比任何一种恶习都更有害的东西”,它在行为上对于所有失败者和柔弱者的同情,所以基督教被称为“同情的宗教”。而对于同情,尼采认为,当一个人在同情的时候会失去力量,因为,“同情将痛苦本身变得富有传染性;有时它还会带来生命和生命能量的整体损失,而这与起因的分量又极不相称。”而且,“同情完全悖逆了发展的法则,发展的法则即选择的法则。”同情是虚无主义的实践,同情“劝人向无”!所以当基督教成为同情的宗教,它就是站在所有软弱者、卑贱者和失败者的一边,“它与强大生命的保存本能正相抵触,并从中树立了一种理想;即便精神上最强大的本性也被它败坏了理性,其途径是教人把最高的精神价值感受为有罪的、误导性的,感受为诱惑。”
如果说基督教是同情的宗教,把同情当成德性本身,败坏了理性,那么那些神学家则是以歪曲价值的方式,颠倒了真与假的感念,危害了生命本能,甚至反而把“提高生命、增强生命、肯定生命、为生命辩护、使之凯旋的反倒被称为‘假’……”这是因为他们不触及现实,反而用想象构建了基督教的体系:上帝、灵魂、自我、精神、自由意志都是纯然想象出来的原因;罪、救赎、恩典、惩罚、恕罪,则是纯然想象出来的结果;上帝、精神、灵魂变成想象出来的存在者;以人类中心论、缺少自然原因的概念,成为想象出来的自然科学;以纯粹的自我误解,并借助宗教-道德特异体质的符号语言,如懊悔、良心谴责、魔鬼的试探、上帝的临近变成想象出来的心理学;而上帝国,末日审判、永生则变成想象出来的目的论……在想象而不触及现实的情况下,精神、骄傲、勇气、自由,以及对感官和感官快乐,都变成基督教的仇恨对象。
而从基督教的起源来说,它的这种同情式的道德,对快乐的仇恨,以及不触及的想象也使之成为一种权力的工具。“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最奇特的民族,在面对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之时,他们以一种极其可怕的意识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存在:代价是极端地歪曲了一切自然、一切自然性、一切实在、以及全部的内在和外在世界。”选择存在,是选择宗教的存在,却在一种“去自然化”的过程中,与任何一个民族能够生存、可以生存的条件划清界限,并且从自身出发创造出了一个与自然的条件相反的概念,“他们以一种无可救药的方式依次将宗教、祭祀、道德、历史和心理学颠倒为自然价值的反面。”当基督教的上帝在去自然化中成为宗教鼓吹者手中的工具,它去除了历史意义;当“上帝的意志”成为教士拥有权力的条件,所谓的“启示”变成了一场“文学伪造”:“一本‘圣经’被发现了——它在僧侣的排场、赎罪日和对于长久‘罪恶’的嚎啕大哭中问世。”当基督教否定了仅存的实在,“神圣民族”“选民”以及犹太性本身都在去自然化、去历史化中被“圣化”;救世主被眼中歪曲,“因为许多原因,这样一种类型无法保持纯洁、完整、毫无添加。”
基督教是从十字架的死亡开始的历史,却变成了原本的象征体系逐步被误解、误解不断变得更加粗糙的历史;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了病态和低俗的信仰,甚至在病态的野蛮中教会取得了权力,“教会是每一种真诚、每一种灵魂高度、每一种精神教养、每一种正直和善良的人性的死敌形式。”当基督教存在、基督性都被化约为一种纯粹的意识现象,意味着基督性本身被否定,两千多年以来被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学神的误解;在这种实在和历史真理不存在的境况下,犹太教的教士们将基督教的昨天和前天一笔勾销,取而代之了一个捏造了的基督教的历史,从而歪曲了以色列的历史,甚至将人类的历史、基督教的史前史都歪曲了——对于教士和教会来说,他们只是获得了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使用概念、教义和象征来对大众实行僭政,来教化牧群”。
基督教的历史被歪曲,基督教的信仰变成了权力,基督教的福音变成了“圣化”的工具,尼采也开始对造世主的上帝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上帝是人心存感激的需要,因为,“这样一位上帝必须能有助益、也能够损害,能做朋友,也能做敌人,一无论好坏,人们都赞赏它。”但是,当基督教变成权力工具,那个上帝自然在违逆自然中被阉割:上帝不断被道德化,他在“每种私人德性的洞穴里爬行”,上帝成了每个人的上帝,成了私人,成了世界主义者……所以尼采认为,上帝已经变得和魔鬼一样,是颓废的产物,而上帝没落之后,他甚至变成了“物自身”;但是这依然不是上帝被道德化的终点,上帝退化成为对生命的意义,上帝成为对生命、自然和生命意志的敌意,上帝是对“此岸”进行侮辱、每一种“彼岸”谎言的公式——上帝的虚无被神化了。
基督教被歪曲而圣化,上帝被虚无神化,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教士是工具化的制造者,尼采提到了保罗,在他看来,正是保罗这个“拉比的逻辑犬儒主义者”完成了从救世主的死亡开始的衰败过程,他把福音书的价值提高到了无可估量的地位,他甚至发明了罪和救赎,“上帝所选中的是世上柔弱、愚蠢、不高贵、被鄙视的人”,这句经典的话让十字架上的上帝取得了胜利,这个象征中的可怕隐秘念头最终变成了神圣的产物:“一切痛苦的、一切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神圣的……我们所有人都上十字架,于是我们都是神圣的……”不是上帝实行统治,是发明了罪的教会开始了统治,“作为一种欧洲运动的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废物、垃圾因素的总运动:——这些因素想要和基督教一道夺取权力。”
基督教变成权力工具,上帝被道德化,尼采并非只是对基督教本身发出诅咒,他批判的是德国历史,批判哲学,批判所谓的现代性。在他看来,德意志的贵族永远是教会的“侍从”,他们永远服务于教会所有“恶劣的本能”,而教会也同样利用德意志贵族,“教会恰恰借助德意志战刀、德意志鲜血和勇气来进行反对地上一切高贵之物的殊死战斗!”德国人从欧洲手中夺取了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果实,那就是文艺复兴的果实,但是在“重估基督教价值”中,他们却集结了一切手段、一切本能和一切天才相反的价值做出的努力:路德作为一个僧侣来到罗马,他本应在罗马向文艺复兴发怒,本应怀着最深的感激去理解所发生的惊人之事:“在基督教的驻地克服了基督教”,他本该用生命、生命的凯旋以及对于一切高等、美好和大胆之物的伟大肯定来取代基督教的“古老的腐败”,但是路德却只是从仇恨中吸取自己的营养,只是在宗教性中为自己着想,他重建了教会,攻击教会,却只是变成了“巨大的徒劳”。和路德一样,德国的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对宗教的战争,最后都变得徒劳无功,“我承认,这些德国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藐视他们每一种概念和价值上的不洁净,藐视他们对于每一种诚实的是与否的胆怯。”尼采对康德的评价是“白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宣布上帝不存在,却又在实践理性中为上帝安排了一个位置,这种以道德出发的安排变成了虚构,“康德的成就只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就:与路德、莱布尼茨一样,康德是用来制止本身不稳当的德意志诚实的另一个止轮器”,因为他只是出于一种对“德性”的概念之敬畏才弄出一套德性来,所以那种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在危害生命,“在所有事情上面都犯错的本能,反自然之为本能,德意志的颓废之为哲学——这就是康德!”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哲学便成为“纯粹精神”的谎言,所谓的真理就在虚无和否定中被颠倒了,神学家成为哲学家,是“以毁灭、侮辱和毒害生命为业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宗教改革,所谓自由战争,所谓“人类向善的倾向”,所谓道德,都变成了对于生命本身的违逆,都变成权力的工具。而现代性,在尼采看来,也是“懒惰的和平”,也是“胆怯的妥协”,也是“道德上全部的不洁净”,现代人就是一个虚伪的怪胎,就是毫不知耻的所谓基督徒,所以在这样的人群中,尼采感受到了一种窒息,“我毫不怀疑我鄙视的是什么、是谁:正是当今的人类,我不幸与之同时代的人们。当今的人类——他们污浊的气息让我感到窒息……”对基督教的诅咒,对上帝的讽刺,对宗教改革和现代性的批判,尼采所做的一切否定其实都是为了找到肯定的力量:在他看来,佛教比基督教“现实百倍”,因为佛教是“善良、温顺、变得过于精神化的种族的宗教”,“佛教把这些人带回到和平与欢乐、回到精神食谱、回到某种身体上的磨炼。”佛教具有的人格正是因为它给事实以权利;《圣经》开头的故事正说明了上帝对科学的极度恐惧,夏娃因为学会了享用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说:“科学是第一宗罪,是所有罪的根源,是原罪。只有这是道德。”所以从另一个意义上将,知识和科学才是令上帝不安甚至恐惧之所在;在全部《新约》中,谁是唯一必须尊敬的人物,是罗马总督彼拉多,对他来说,多一个犹太人和少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这个词被无耻地滥用了,于是《新约》中最有价值的一句话由比拉多说出:“什么是真理!”在《圣经》之外,尼采喜欢阅读的是《摩奴法典》,因为这是一本无比精神化、无比优越的作品,她里面有着真正的哲学:有一处说:“女人的嘴、少女的胸、孩子的祷告和祭品的熏烟总是纯洁的。”另一处说:“没有什么比太阳的光辉、母牛的身影、空气、水、火和少女的呼吸更纯洁的东西了。”处处是生命的影子,处处表现了生命意志,所以尼采说:“像《摩奴法典》这样对女人说了那么多温柔亲切的言辞的书,我还从未读到过;这些胡子花白的老圣者对女人献殷勤的方式,恐怕无人能及。”
否定之后是肯定,尼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重估一切价值,重新建立幸福的公式,所以很明显,对基督教的诅咒,对上帝的批判,对所谓纯粹精神的否定,就是要建立一套生命哲学,实践一种生命本能——在人走向终点之后,真正体现了生命权力意志的便是“超人”:“事实上,一种更高的类型随之显现:这种类型相对于全部人类而言是一种超人。”这样的超人,把生命的重心放在生命上面,这样的超人,通过力量、通过灵魂的高度超越于人类之上,这样的超人不是信徒而是怀疑者,“一个精神,如果要欲求伟大、欲求达至伟大的手段,必定得是怀疑者。”而超人的原型便是尼采所塑造的伟大的怀疑者,“查拉图斯特拉是个怀疑者。源于精神力量和精神力量之过度的强大和自由,通过怀疑来证明自身。”甚至在尼采看来,怀疑也不是幸福的起点,真正否定之后的肯定,终点之后的起点是成为“敌基督者”,于是最后“反基督教的律法”在至高意义上出炉,它是在1888年9月30日,即“在拯救的日子,在第一年的第一天”颁布,它的目的是反对恶习的基督教并进行一场殊死之战:
第一条——任何一种形式的违逆自然都是可恶的。教士是最可恶的一种人:他教导人们违逆自然。用来反对教士的不是理由,而是监狱。
第二条——每参加一次礼拜都是对公共道德的一次谋杀。要比反对天主教徒更加严厉地反对新教徒,要比反对笃信的新教徒更加严厉地反对自由派的新教徒。当基督徒靠近科学的时候,他身上的犯罪因素增加了。因此,哲学家是罪犯中的罪犯。
第三条——那该诅咒的地方(基督教在上面孵养了它的怪蛇蛋)该被夷为平地,并且该作为地上的可耻之处让后世永感恐惧。该在上面驯养毒蛇。
第四条——宣扬贞洁是公开鼓动人们去违逆自然。通过“不洁”这个概念,对性生活所进行的每一种藐视、每一种玷污都是真正的罪,它违逆生命的神圣精神。
第五条——与一个教士同桌进餐要遭驱诼:一个人因此而把自己逐出了诚实的社会。教士是我们的旃陀罗,——该排斥他,让他挨饿,把他赶到随便哪一种沙漠里去。
第六条——该把“神圣的”历史称为该诅咒的历史,这是它该有的名称;该把“上帝”、“救主”、“拯救者”、“圣者”这些词用作脏话、用作罪犯的标志。
第七条——余者由之得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