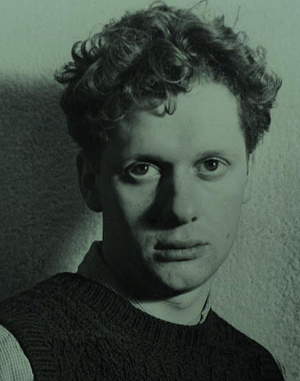2023-05-01《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我梦见自身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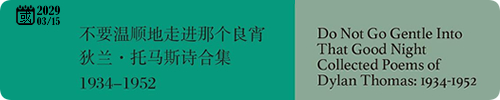
死亡之河流入我握住的可怜之手
我透过他渐弱的眼神,看到大海之根。
镇定地奔赴你受难的山岗,我说
空气离他远去。
——《挽歌》
空气离他远去,大地离他远去,生命离他远去,当“勇敢而冷酷”的人躺下,当“极度孤傲的人”不再转身,留下的是悄无声息的屋子,是蜷缩的内室,是失明的床榻,死亡到来,“安息并归入尘土”。1953年9月15日,狄兰·托马斯写下了《挽歌》的初稿,此时距离父亲去世九个月,九个月,是肉身死亡和用“挽歌”重唤生命的距离,九个月,也是父亲和“我”开始生死对话的时间:父亲死了,傲然不屑地死去,“以最黑暗的方式”死去,注解了“最黑暗的公义”的死亡,但是“死亡之河流入了我握住的可怜之手”,握住,便是对话的行动,便是新生的可能:他的死穿越了山岗,“在情操之下永沐爱意”,他的死在躺下中重新看见了“勃发的青春”,他的死让一切归于尘土,但是我在祈祷,“从正午、夜晚和拂晓前那一刻起”,我透过他渐弱的眼神看见“大海之根”,然后“镇定地奔赴你受难的山岗”……
但是,在写下“空气离他远去”之后,所谓的握住,所谓的祈祷,所谓的奔赴,都戛然而止——1953年为父亲的死亡写下的挽歌,却没有成为儿子继续前行的方向,于是死亡成为了死亡,并在生者写下的挽歌里看见了另一种促然而止的死亡:在写下这首《挽歌》初稿不到两个月,在美国纽约做第四次诗歌巡回朗诵期间的狄兰·托马斯,遭遇了不幸:因为“患上肺炎却被误诊,误用大剂量吗啡而导致昏迷”,11月9日,这位天才诗人在纽约圣文森特医院陨落,年仅39岁。死亡接踵而至,死亡叠加着死亡,他随着诗歌中并不畏惧死亡的父亲而死去,他紧接着不会离我而去的父亲而离去,而当狄兰·托马斯不幸去世,这首维拉内体的诗歌也成为了未完成的永久残片,而唱给父亲的挽歌也变成了自我生命的终止的见证。
诗歌未完成,死亡猝然而至,不仅仅是狄兰·托马斯对父亲经历死亡的一种隐喻,也成为自己难以逃离命运的写照。但是一首完成的诗,是不是可以从死亡的终结中预见新生的开始?也是生与死的时间距离,一年前的1952年3-5月间,狄兰·托马斯编完《诗合集1934-1952》之后写下了一首名为“序诗”的诗,在“上帝加速了夏日的消亡”中,诗人成为了编织手,他“砍劈了这不同形态的喧闹”,他在脆弱的和平下唱起歌,他用这歌声“赞美这一星球”,“歌唱/虽然是一种炙热亢奋的行为,/但我锯齿般扩展的歌声/就是众鸟的烈火/席卷大地的森林”,他让人们听见自己吹奏喇叭颂扬这世界,他让人们看见自己“建立起一叶怒吼的方舟”,在洪水高涨的时代,在恐惧、愤怒的末日,那一首歌“抵达我怀抱中的威尔土”,于是成群的方舟“穿过/波涛倾覆的陆地,/它们敞开爱的怀抱,前行”,那些昂首鸣笛的鸽子,那些越过大海的“年迈狐狸、托马斯雀、大卫鼠”成为“复乐园”的象征,“我的方舟唱响在阳光下,/上帝加速了夏日的消亡/此刻洪水盛开如花”……
上帝加速了夏日的消亡,诗人制造了方舟,毁灭之后的拯救让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此即狄兰·托马斯的“序诗”,它是死亡终结之后的重新出发,它是诗歌王国新的秩序。但是,当狄兰·托马斯用中古威尔士诗歌及法国普罗旺斯诗体完成了这首实验性探索的诗歌,“序诗”又成为了“终章”:直到1953年11月离开这个世界,他再也没有写下一首诗,而这首《序诗》也成为了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上帝加速了夏日的消亡,上帝也把他推向了生命的大洪水之中,终于,“在酒精、性、兴奋剂以及渴望成功调制而成的鸡尾酒中崩溃,透支他作为一个天才诗人所有的能量与癫狂”的狄兰·托马斯湮没于盛开如花的洪水之中,再也听不见歌声,再也看不见方舟,生命“仿佛树叶般/飘起又飘落,/迅然破碎又不灭”……
1952年的《序诗》成为狄兰·托马斯生前的最后一首诗,1953年的《挽歌》成为狄兰·托马斯生命中的“未完成”的残片,诗人仿佛就是一首用生命写就的诗歌,当死亡到来,是不是真的不再被握住?是不是真的“空气离他远去”?39岁的生命最后变成未出发的序诗,变成未完成的挽歌,他一生在构筑的“进程诗学”是不是在出生、死亡中再无重生的可能?“进程”是不是最后必然是一种停顿、停滞和停止?“死亡之河流”是不是必然流经一切的肉体而化为生命的乌有?而实际上,对死亡的关照,对死亡的注解,一直是狄兰·托马斯诗歌的主题,从欲望开始孕育生命,也在欲望终结中走向死亡,他的“进程诗学”的起点其实就是死亡,而死亡之所以发生,就在于欲望的力量。
“世界气象的进程/变幽灵为幽灵;每位投胎的孩子/坐在双重的阴影里。”1934年2月写下的《心灵气象的进程》可以说就是狄兰·托马斯“进程诗学”的“序诗”,心灵气象的进程是将湿润变干枯,将黑夜变白昼,它的起点便是欲望,“阳光下的血/点燃活生生的蠕虫”,“活生生的蠕虫”,暗喻的是“阴茎”,它在墓穴里,然后孕育生命成为“投胎的孩子”,而进程的最后将生与死的幽灵变为亡灵,“而心灵交出了亡灵”——出典于《圣经·新约·启示录》,约翰使徒说:“于是大海交出海底的死人”,幽灵变成亡灵,交出即是对死亡的抵达,由此完成“天启文学”的象征意义:“而子宫/随生命泄出而驶入死亡”。由蠕虫开始,经历将湿润变干枯,将黑夜变白昼的过程,最后心灵交出亡灵,生与死的进程得以建立,而这种建立不是一种封闭的单线结构,子宫随生命泄出而驶入死亡,死亡在子宫里,实际上隐含的是死亡之发生却是新进程的开始,它指向的是重生,于是在欲望、生命和死亡中完成了一种循环却上升的过程,生走向死,死再次走向生,生生死死无限循环,变成了一条让“洪水盛开如花”的河流。
| 编号:S38·2221205·1908 |
欲望孕育了生命,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里,到处是欲望的意象,它们是象征女性身体和生殖器的“脂肪和花朵”,是阴茎委婉语的“密友先生”,是点燃骨头的“太阳鸡巴”,是“环烙上百合的愤怒”的生殖,是血脉、包皮和云彩,是羊水、根茎和玫瑰。《我看见夏日的男孩》里描述的就是这一种欲望的呈现:夏日男孩在毁灭,家园一片荒芜,妙龄少女们带来的是“满舱的苹果”,于是欲望开始了生命的过程,孩子在娘胎里“拨开强壮子宫的气象”,可爱的拇指“划分夜和昼”,他们还“涂抹自己脱壳的头颅”,最后变成种子,然后在光和爱中爆发,“哦,瞧那冰雪中夏日的脉动”。长着满舱苹果的少女,强壮的子宫,手指涂抹头颅,都是性欲的直接体现,它甚至成为性交的隐喻。但是欲望孕育的生命最后也走向了死亡,死亡却是对生命新的召唤,“让我们/从夏日的女人召唤死亡,/从痉挛的情人召唤强悍的生命,/从漂浮大海的漂亮尸体/召唤戴维神灯亮眼的蠕虫,也从种植的子宫召唤稻草人。”深海恶魔戴维·琼斯的神灯被召唤,就是意味着死亡,死亡爬出的蛆虫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起点,于是春天到来,于是出现血液和浆果,于是爱的肌体又变成了湿润,“我长成你父亲般的男人。/我们是燧石和沥青的子孙。”从父亲到子孙,完成了一次从死亡到新生的蜕变。
心灵气象的进程是大自然的进程,是生命的进程,也是人类心灵的进程,狄兰·托马斯将自然四季转变和生命受精、怀孕、妊娠到分娩的过程、人的生老病死结合在一起,阐述“进程诗学”。1933年9月的《当我敲敲门》是狄兰·托马斯展现生物形态进程重要节点的“胚胎诗”:从敲门开始,“肉体任意出入/以液态的手指轻叩子宫之前,/我像水一样飘忽无形,/那水汇成我家乡旁的约旦河”,从液态中出入,到出生,再到饱经风霜,最后死亡,这是一组“活生生的密码”,“我,出自灵和肉,非人/亦非灵,却是必死的灵。”而终将已死的我迎来新生,需要的是敬拜祭坛和十字架,需要以我的骨和肉为盔甲,“两次穿越我母亲的子宫”中完成生与死的转换。同年10月的《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狄兰·托马斯将人的生老病死和自然四季交替结合在一起,“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摧毁我的一切。”1934年的《假如我被爱的抚摸撩得心醉》呈现了生命的四个阶段,从胚胎期到婴儿期,从青春期到衰老期,最后在“性与死亡”中向前推进,“我愿被抚摸撩得心醉,即/男人就是我的隐喻。”
从欲望开始,到死亡结束,从死亡开始,再次进入生命进程,狄兰·托马斯的进程诗学并非是思考“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的死亡,因为,“时光是一种愚蠢的幻觉,时光与傻瓜。”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重要的是死亡之后重新回到生命进程的转变,《我梦见自身的诞生》便是狄兰·托马斯对真正生命进程的思考,我首先梦见的自己的诞生,然后是死去,在诞生和死去组成的进程之后,第二次诞生开始,第二次死亡开始,“恰逢第二次死亡,我标识山岗,收获/毒芹和叶片,锈了/我尸身上回火的血,迫使/我从草丛再次奋发。”一次和两次,不是数量上的叠加,而是一种循环而递进关系的建立,“我梦见自身的诞生”,是生死之后的重生,是重生重死之后的再生再死,“直至/亚当一身汗渍发了臭,梦见/新人活力,我去追寻太阳。”所以对于狄兰·托马斯来说,“死亡也是工具”,人类只是戴着“死尸假面”,只是披挂上斗篷,在死亡发生之后,才是灵魂的醒来,才是锻造初始之神,“我的意象咆哮,从天国的圣山升起。”
要让我梦见自身的诞生,关键就在于解读狄兰·托马斯所说的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种死亡的发生是为了重生?实际上,死亡本身就隐含在出生中,而出生是由欲望构筑的,第一次诞生是欲望中的诞生,这种诞生就构成了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原罪,“在原罪成形之际,分叉蓄胡的苹果,/上帝,动了手脚的守护人,打那走过,/从天国圣山漫不经心地贬下他的宽恕。(《魔鬼化身》)”上帝是动了手脚的守护人,上帝是魔鬼的化身,伊甸园彼岸成为了“在在硫黄号角吹开神话的地狱”。所以欲望在伊甸园里宛如蛇行,它是“这条虫”:“这条虫必然是寓言的瘟疫。”“这条虫的寓言必然是承诺。”当夏娃表达狂热的爱,那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寓言的幕后藏匿十字型的传说”;所以欲望只是一张“兽性大床”,“所有爱的罪人身着盛装去跪拜生命主的圣像,/豆蔻、麝猫香和海欧芹供奉染上瘟疫的新郎新娘,/他们降生这顽童的忧伤。(《是罪人的尘埃之舌鼓动起钟声》)”
|
| 狄兰·托马斯:我,却是必死的灵 |
上帝成为魔鬼的化身,伊甸园里蛇在爬行,十字架被藏匿,欲望变成了兽性大床,这一种原罪的欲望其实只是肉身之欲,狄兰·托马斯发现了“魔鬼化身”的世界,他也看见了充满罪恶的现实。写于1940年1-3月的《有一位救世主》仿自弥尔顿诗歌《基督诞生的清晨》,战争爆发,“在那杀戮气息里,我们掩藏恐惧,/当地球变得越来越嘈杂,避难所和巢穴/愈加喧嚣,唯有保持沉默,再沉默。”沉默是一种态度,那就是反战,“为颓败不堪的家园,/无法养育我们的身骨,/唯有勇敢地死去且永不为人所知,/此刻,我们独自明了,/自身真实而陌生的尘埃/穿过我们不曾进入过的房门。”勇敢地死去构成了狄兰·托马斯当时对死亡的态度,肉身死亡是悲剧,但是灵魂可以得到救赎。而《空袭大火后的祭奠》是狄兰·托马斯对一名死于空袭的孩子的悼念,“我/和哀伤的人们/哀悼/大街上不停息的死亡/一位出生仅几小时的婴儿/一张吮吸的小嘴/烧焦在墓穴黑色的胸膛/母亲的胸乳,怀抱熊熊的烈火。”在这里,狄兰·托马斯用了“Myselves”,这是复数的“我自己”,实际上不再是单一的诗人,而是代表大街上所有伤心的人们表达对死亡的哀伤,这种死亡的背后就是罪恶的“魔鬼化身”,是对肉身的践踏,“是那条蛇那一夜的堕落”;还有《黎明空袭中有位百岁老人丧身》一诗,狄兰·托马斯描写了一位在黎明中“步出家门就死去”的老人,“哦,让他的遗骸远离那辆常用的运尸车,/黎明在他岁月的翅膀上飞翔,/一百只送子鹳在太阳的右手栖息。”《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是他写于1944年-1945年的葬礼弥撒曲,伦敦大火夺去了孩子的生命,“这个孩子庄严而壮烈的死亡。/我不会因她离世/这一严酷的真相而去屠杀人类/也不再以天真与青春的挽歌/去亵渎/这生灵呼吸的驿站。”在他看来,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死亡只发生一次,“第一次死亡之后,死亡从此不再。”
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死了,在伦敦大火中的孩子死了,被炮火击中的老人死了,死亡在发生,那是对生命的亵渎,当狄兰·托马斯发出“第一次死亡之后,死亡从此不再”,实际上他在书写着人类自身的罪恶,书写着肉身的罪恶,这种罪恶就是欲望本身的罪恶。所以要从死亡开始新生,要梦见自己的诞生,就需要寻找肉身之死之后的救赎,在狄兰·托马斯那里,死之重生就在于发现具有灵魂意义的“词语”。“词语,就我而言,就如同钟声传达的音符,乐器奏出的乐声,风声,雨声,海浪声,送奶车发出的嘎吱声,鹅卵石上传来的马蹄声,枝条儿敲打窗棂的声响,也许就像天生的聋子奇迹般找到了听觉。”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狄兰·托马斯这样写到,词语是什么,是生命的声音,是灵魂的韵律,是抛掉肉身之罪后的宣言。“高空广告牌下,失去臂膀的人/有双最干净的手,恰如无情的幽灵/唯独不受伤害,盲人的眼看得最真切。”在《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光》中狄兰·托马斯就书写了一种悖论,失去臂膀的人有一双干净的手,失去的臂膀只是肉身,而干净是手是肉身之死后的词语,盲人是肉身的存在,看得最真切的眼是肉身之死后的词语,也只有去除肉身之罪,才会有干净的手,才会有看得真切的眼睛,在这里,狄兰·托马斯去除的是有罪的肉身,创造的是死亡之后诞生的新肉身,“我一颗高贵的心在爱的国度/心留有见证,必将摸索着醒来;/当失眠的睡眠降临到窥阴的感官,/心依然销魂荡魄,尽管五眼已毁。”《当我乡下人的五官都能看见》中,狄兰·托马斯重塑的手(触觉)、眼(视觉)、舌(味觉)、耳(听觉)和心(感知力)的五官感知力。
而这就是自我诞生、自我重塑的词语:“某些词我用发元音的山毛榉造就你,/用橡树的声音,用荆棘丛生的/州郡的根须识别你的音调,/某些词我造就你,用水的言辞。(《尤其当十月的风》)”写于1932年至1933年的这首诗,是狄兰·托马斯“生日诗”系列中的第一首,生日就是一种诞生,诞生的词语是“透过眼睛破晓蠕虫的冬天”的词语,是“我向你述说渡鸦的罪过”的词语,是“在海边倾听鸟群发出黑色的元音”的词语,词语是肉体的变格,是一个子宫,是一种思想,“我学会表达意愿动词,有了自己的秘密;/夜晚的密码轻叩我的舌面;/聚为一体的思想发出不绝的声响。”最后,词语带来季节,带来青春,“太阳和吗哪,带来温暖和养分。”就像以色列人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粮,“吗哪”就成为词语之诞生的重要标志。而词语世界最终让狄兰·托马斯找到了上帝的信仰,“最初是词语,那词语/出自光坚实的基座,/抽象所有虚空的字母;/出自呼吸朦胧的基座/词语涌现,向内心传译/生与死最初的字符。”最初是词语,便是“太初有言”,上帝在说话,他用词语完成了创世,他将词语变成了思想,他让词语迎来了诞生。
从欲望中来,见证死亡,发现罪恶,最后在词语的救赎中重现上帝之光、生命之光、思想之光,狄兰·托马斯用这样的方式书写了欲、生和死的“进程诗学”,但是写下这些诗作的诗人何尝不是一个肉身?自身的诞生何尝不是在梦中完成?狄兰·托马斯一定看见了自身难以逃离的肉身之罪,“诗人在那多嘴多舌的房室,/敲响生日的丧钟,/辛劳跋涉在他遭伏击的伤口;/苍鹭、尖塔节节祈福。”他看见了自己,看见了死亡,而且就在“生日”中听见了“丧钟”,最后靠近的就是死亡,“我无比闪耀的人类不再孤独,/当我扬帆出航死去。”1949年,狄兰·托马斯写下了这首《生日献诗》,这是他的第四首生日诗,也是最后一首,看见了死亡的狄兰·托马斯终于将生日变成了“杨帆出航死去”的见证,他在酒精和性中为自己唱起了挽歌,他制造了真正属于肉身的死亡,四年之后“洪水盛开如花”彻底带走了生之躯体,连同那些“最初的词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