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6《精神病学的权力》:最终达到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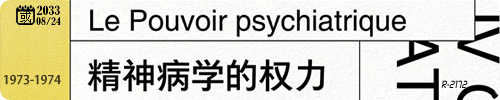
他被单独锁在一个房间里,为了让他不受伤,房间的门窗和墙壁都覆盖着床垫。负责治疗的人向他宣布,他不再是君王,今后得顺从听话。
——1973年11月14日
他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当他突患躁狂症,他便被锁进了一个单独房间里,门窗都做了特殊的处理,为的是在发病时不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痛苦;但是乔治三世还在发病了,他以前的仆人便承担起了对他进行控制的职责,而这种控制首先就是对乔治三世身体的控制。当乔治三世身患精神病失去了自由更被宣布“不再是君王”,当从前沉默、顺从的仆人成具有控制国王身体的力量,这个关于精神病学的著名治疗场景成为了米歇尔·福柯探讨“精神病学的权力”的一个切入口,那就是关于“身体”权力的缺失和重构。
“对秩序而言,身体是用于穿透和塑造的。秩序就像一个大的骨架,发出指令,身体便被穿透和侵蚀。”1973年11月7日,这是福柯开设的“精神病学的权力”的第一课,他直接指出了“身体”在这个权力微观物理体系中的位置,什么是权力,当然就是体现在秩序、法令和权力至上上,在医学体系中,秩序就是一种纪律,无论是对病情进行诊断还是对病人进行治疗,都必须以纪律为条件,“在精神疗养院里,维持平静与秩序,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保持警觉,这一点极其重要。这是治疗躁狂症的基础之一。如果做不到,便不能获得准确的病情评估,无法痊愈,甚至还会产生药物依赖。”皮内尔这样阐述秩序的重要意义,构建穿透和侵蚀身体的秩序其实就是权力,而权力的来源更重要就在于它具有达不到、不对称、无互利性的要求,而对精神病病人进行诊治的医疗需求就体现在让权力发挥作用。
福柯在此前的《疯狂史》中也阐述了权力,而现在回过头来看,《疯狂史》对“疯狂”和权力的研究只是着眼于它的表象分析,或者说研究的是一种感知疯狂,即通过传统形象、幻觉、认知等表征作为研究的开端探讨了17世纪和18世纪对疯狂进行治疗的起源。当回到法兰西学院,福柯认为《疯狂史》研究是一次“中断或终点”,很多问题并没有触及,他提出的尝试是:“如果研究的起点不再是必然会指向思想史的核心表征,而是权力的支配,会怎么样?也就是,权力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一定数量的陈述话语以及可能随之产生的所有表征形式?”权力的话语分析在他看来是权力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衍生出的问题则是:“话语的形成和什么有关?要到哪里去寻找?”这也就成为了福柯在“精神病学的权力”中设下的框架,这个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疯狂史》的终点变成了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绕过了家庭模式和规范、国家机器、制度概念和暴力概念,它成为对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析,而这个分析着重要弄清楚的是两个主题:关于权力的支配和真相的游戏。
达不到、不对称、无互利性的要求是权力的来源和秩序不对称的主要因素,而在精神病院里,它所体现的是:权力不再属于个人,除了医生,还有看守、杂工等替换者,他们构成了分散、替换、交错、潜在差异和错位的权力存在;精神病院内部的权力体系也偏离了一般的规则体系,当权力分配出现了差异性和多元性,规则体系也变得繁杂和散乱,甚至产生了等级,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权力就变成了一种战术,甚至可以说,精神病院就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之所以凸显了权力的战术运用,因为除了控制病人的医生和替换者之外,还有精神病人,之所以他们是精神病人,他们就是“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存在,精神病人是否也会为了权力而斗争……如此的新问题,如此的新现象,对于权力的分配和真相的游戏,就具有了微观物理分析的意义,如何穿透和侵蚀身体就成为了重建精神病学权力和秩序的重要问题。
| 编号:B83·2250901·2344 |
福柯引用乔治三世的治疗场景,就指出了精神病学的权力的一个本质问题:权力的转向。乔治三世作为国王,在没有躁狂症的时候,他拥有的是属于国王的权力,这就是统治权,它是权杖、王冠、佩剑等象征符号,它通过仪式实行国家统治,它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它统治的是人民,但是当他患了躁狂症被锁进了房间,“整个国家机器陷入瘫痪,病人远离家人和周围的一切,流放到偏僻的宫殿。”权力完全被改写甚至颠覆了:他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相反那些曾经听命于他的仆人,反而拥有了对他身体进行控制的权力。这一场景具有精神病学上的标志性意义,在福柯看来就是一种“反向加冕仪式”,他让拥有统治权的国王被免职,从而完全置于从属的位置,“他能掌控的只有自己,也就是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他来说,身体也不再属于自己,因为他的身体不顺从,不听话。当乔治三世被“免职”,当统治权不再,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向了另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就是惩戒权。
统治权以不对等的形式连接了统治者和臣民关系,一边是获取另一边则是付出;统治权的要素主体不是一种个人或个人的身体,它超越个体具有多重性,国王的身体就是王国和王位的象征;统治权的统治关系建立在优先权之上,通过一定的仪式来实现。而当乔治三世成为一个病人,当医生和曾经的仆人对他实行惩戒,对统治权的取代,惩戒权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属性:惩戒权没有二元性和不对等,它的首要特征不是获取产品、部分时间和某种服务,而是整体把握,这就是它的整体性;惩戒权的运行不需要仪式手段,没有典礼和标志,它是一个持续控制的过程;统治权是一种粗暴介入,而惩戒权则是一种干预,它在事情发生之前以监视、补偿、惩罚、施压等手段对可能性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它所针对的是潜在行动;惩戒的实施是通过惩戒装置来完成的,惩戒装置必然有等级之分,因为每一个要素在分配中都必须在既定的位置上,而惩戒的对象必须被看见;这种被看见就是个人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惩戒权具有个体化的特点,它制造服从的个体,并通过监视、记录系统或全景敞式系统,将功能主体与个人身体固定在一起。整体性、持续性、等级性、个体性,这些属性使得惩戒成为权力的最终形式,而在福柯看来,作为终端权力的惩戒权,正是通过权力穿透了身体并“最终达到身体”,它咬住身体不放,它考察身体的动作、行为、习惯、话语,它触及身体的训练、改变和指导。
从统治权转向惩戒权,是权力形态的改变,而从象征转向身体,则是精神病学的权力真正的起点,当身体成为权力的终端,福柯在后来对手稿的补充中就说:“这在方法论上意味着搁置国家和国家机器的问题,脱离关于权威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更重要的是,当个体和身体成为精神病学的考察目标,它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话语,就是为寻找真实性奠定了基础,因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惩戒个体更是哲学-法律上的个体,“法律个体是要求获得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惩戒个体是现实活动中的真实工具。正是在法律个体和惩戒个体之间,在要求获得的权力和实际运用的权力之间摆动,才产生了这种幻象和这种真实,我们称之为人。”
现实的、真实的个体如何在惩戒中最后达到身体?身体又如何书写真实性游戏的真相?福柯首先考察了惩戒装置,沿用《疯狂史》的阐述,福柯再次提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在他看来,这种惩戒装置首先具有个体化,虽然权力的中心是集体的,但终端是个体的,“惩戒从底端形成个体化,使对象个体化。”这样,权力就完全匿名化了,它可以属于监狱长,但是“监狱长”具有的真实效果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即使监狱里没有监狱长,个体仍然被受到监视,“到最后,可能中控塔里根本就空无一人,而权力依然发挥作用。”个体化和匿名化最终使得权力行使民主化,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监视权力。圆形监狱不是一种机构类型,而是一种权力机制,一种权力发挥作用进而获得最大力量的机制,所以,“圆形监狱是一个放大器,在任何类型的机构内部,它都是权力的强化器。”而这个放大器以最强大的权力、最佳分配和最准确的执行目标,它所形式的权力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在惩戒装置中,精神病学的权力体现了对个体化真实性的追求,而对精神病病人的治疗更是体现了一种真实性强权,它所体现的精神病学的权力就是让真实性的操作者成为面对疯癫时的真实性强化器。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勒列特因滥用体罚和责骂等手段进行治疗,被称为是“声名狼藉”的医生,但是福柯从他的精神疗法中发现了这种真实性强权。勒列特面对病人杜佩雷的时候,以一种权力不平衡的方式让权力转移到了医生这一边,这就是一种“外部意志原则”,它将精神病人对自己肯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内部变成了被医生这一外部力量掌控的权力,这就使得医生和病人的权力反转具有了真实性;勒列特通过语言再利用,赋予杜佩雷不同的身份,“同时是德图什、拿破仑、德拉维涅、毕加尔、奥德里安、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并通过杜佩雷对医生、护士、看守进行命名,在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身份中,杜佩雷记住了等级,并在尊重中开始服从,这就是语言背后的真实性;同时,勒列特还故意制造了需求的缺失,这使得需要的真实性得到了加强,更是通过精神病院中的需求显现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当病人的需求缺失,感觉自己的地位下降,“无权享有这一切”,于是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生了病,从而开始劳动、退让、服从惩戒;另外,勒列特还通过让病人接受在精神病院的权力上建立的管理和治疗方法,让他们以第一人称认定自己,这种对身份的承认就是“真理”的陈述,虽然这不是一种名义上的真理,但是病人也通过真理语言而认识了自己,这也是一种真实性。
惩戒不对称,强制使用语言,调整缺失与需求,强加给病人一个必须承认的合规身份,勒列特的这些精神治疗方法,福柯认为他就是完成了关于真理的操作:不仅将权力赋予了真实性,而且在真实性基础上建立权力,这就是精神病院中的同义反复,那么福柯所强调的“真实性”,它的本质是什么?真实性首先是病人面对意志的真实性,这种意志是掌控着精神病人的权力更高的权力意志,它使得病人从反抗到屈从;然后是疾病真实性本身,是含糊、矛盾和令人眩晕的真实;然后是和金钱、需求、劳动的必要性和满足需求的义务。多重的真实性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起来,而这种真实性其实正是为了最终达到身体:它必须是在权力体系中构建的身体真实,一端指向医生,另一端则指向病人,在医生那里它所体现的是作为精神病院延伸的“身体”,而在病人那里则是真正产生“神经病学意义上的身体”。
医生在面对病人时通过讯问与招认、磁疗与催眠、麻醉剂等方法进行治疗,从而提出真理问题,在这里真理不是敞开的、稳定的、已经形成的、经过论证的,而是依照发生的顺序以事件的形式得出从而引起追问并最终产生真理,“这一真理不是借助工具得出,而是由仪式所导致,使用计谋,抓住时机,这不是方式的问题,而是策略的问题。”从事件真理、仪式真理、权力关系真理,到和病人直面、对抗中构建发现真理、方式真理、认知关系真理、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假定并存在的真理,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它的意义就是在病情发作中达到真实性,从而让医生介入。所以医生的干预、检测具有重要的作用,“了解有哪些力量存在,想象它可能产生怎样的结果,做好安排,让病情在对的日子发作。”所以福柯把医院看成是医生的身体,它是医学强权的体现,是医生和惩戒体系结合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来说,医生不管是介入、治疗,还是惩戒,都是为了对疾病真相进行检验,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权力发现新的身体,而这才是真实性游戏的真相所在。
福柯举例了癔病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强权,另一方也展现了强权,他们在斗争、对抗、互相包围、互设圈套、围困和反围困中抢夺着控制权,一方面,医生发出命令,将意志强加于人,但病人总能以假装能力不及的方式来表示不愿意,这里就存在意识与无意识、不自觉与自发等行为的可能性,医生通过调整意志的介入从而夺回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癔病病人受权力控制,被强加了人为的疾病,所以在面对精神创伤的时候,他们反而能够辨认出精神受创者是不是在装病。一个例子是,一名患有癔病性挛缩症的病人热纳维芙躺在担架上,医生以前给她做过催眠使她遭受了癔病的痛苦,这一次医生通过按压卵巢让病情得到了遏制,但是病人之后再度发作,并进入了谵妄期,就在谵妄期,热纳维芙大声喊叫:“卡米尔!卡米尔!抱抱我!把你的那玩意儿给我!”热纳维芙的病症消失了,但是妄想却在继续,而且变成了一种性诱惑,在福柯看来,这就是癔病病人对精神创伤做出的反应,“你想找到我的症状的原因,它能让你对这些症状进行病理学诊断,发挥医生的作用;你想要这种精神创伤,你就会拥有我的整个人生,会情不自禁想听到我讲述我的生活,看到我又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在病情发作中不断地重新开始。”
在医生和癔病病人大战中,热纳维芙的身体就成为了神经病学意义上的身体,而在谵妄的呼喊中,这个身体不再是精神病学中惩戒的身体,也不是神经病学的身体,而是性的身体,它具有的真实性打开了另一个身体通道,那就是促成了性医学的建立。从医院的“身体”到病人的身体,从权力的身体到反权力的身体,从论证的身体到真实性的身体,惩戒所构成的精神病学的权力其实已经具有了更普遍性的意义,这种最后达到身体的权力体系就是科学的一个新起点,只不过,“这对他们而言是最大的快乐,但对我们而言也许是最大的不幸。”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