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8《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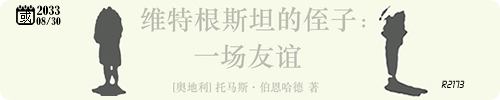
有时我想,我的朋友是为我而死,他要离开人世,以便使我的生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的生存,如果根本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那无论如何也要变得可以忍受些,这个想法并非绝对情理难容。
依然是一个段落到底构成的全文,依然是批判、讽刺甚至谩骂的写作风格,也依然被界定为“散文作品”,这是9月阅读的第四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也是迄今为止读完的第五部作品,无疑,对于伯恩哈德风格的熟悉伴随着一种厌烦,那些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有时候甚至变成了絮叨。这是不是一种重复式的同构?但是伯恩哈德在每一部作品中却试图构筑关于人生、艺术、社会、危机、命运、道德新的世界,而这一本书当然和死亡有关。
同构中的异构,异构有时候也是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对于伯恩哈德作品的观感其实也体现在这部作品中,副标题为“一场友谊”实际上就是一种同构:它是我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之间的同构,保尔身体的疾病、对社会的讽刺、对艺术的观点以及对人生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着我的看法,保尔和我就是在“一场友谊”中成为相同的观察者,或者说,伯恩哈德就是以真实存在的保尔和与保尔之间的友谊为自己发声,保尔是自己的一个“传声筒”——但绝非是《历代大师》中那个博物馆的守卫伊尔西格勒,按照雷格尔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蠢货作我们的传声筒”,而在这部作品中,伯恩哈德以“友谊”的同一性构建了自我言说的传声筒,是为了强调一种合谋性: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在面临死亡的忧患中,两个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相同感悟会更深刻、更彻底也更有普遍性。
“如同保尔几十年与疯癫为伴,我则几十年带着肺病度日;如同保尔几十年扮演着精神病人,我几十年表演着肺病患者;如同他为他的目的利用了精神病人这个角色,我则为了我的目的利用了肺病患者这个角色。”病房里结下的友谊是他们共同面对这个社会和走过人生的契机,也是他们不约而同针对这个荒诞、错乱、可怕社会进行议论、讽刺和谩骂的开始。医治我的医生是萨尔策,萨尔策就是保尔的舅舅,保尔称这个舅舅是“天才和杀人犯”,他走进病房,他进行手术,就是一位天才或杀人犯走进病房、进行手术,一个人既可以是天才也可以是杀人犯,这说明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萨尔策既是奇迹的缔造者,让那些已经病入膏肓的人继续存活,也可以让患者死在自己的手术刀下,而这种生杀大权的使用却完全取决于偶然,患者死于手术刀下,“是事先没有预见的天气骤变引起萨尔策教授烦躁不安,以至于双手变得不听使唤。”从萨尔策既是天才也是杀人犯的讽刺,伯恩哈德接着又开始向医生开刀,“他们如同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至少通过总是给疾病以错误名称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舒适,可这轻松和舒适无异于谋害患者的性命。”他认为所谓的心理医生就是“时代的恶魔”,“他们无法无天,大言不惭地干着一些堪称是暗无天日的勾当。”
在医院里住院、被救治、手术,我们的友谊也体现在对于疾病的看法,保尔住在路德维希病房,我住在赫尔曼病房,保尔身患的是精神疾病,我生的是肺病,住的病房不同,身患的疾病也不同,但都是作为重症正在走向死亡,都是把疾病看做是一种“生存之源泉”:“如同保尔几十年与疯癫为伴,我则几十年带着肺病度日;如同保尔几十年扮演着精神病人,我几十年表演着肺病患者;如同他为他的目的利用了精神病人这个角色,我则为了我的目的利用了肺病患者这个角色。”在我的病房里有一位病人是警察,他是一个喜欢玩二十一点纸牌游戏的人,我也学会了这个游戏,学会游戏之后,“至今无法放弃,这使我常常濒临发疯和神经错乱”;还有一个来自神学院的大学生,是一对法官夫妇的儿子,他们住在维也纳最高雅、最昂贵的住宅区里。警察和神学院的学生,一个代表着法律和秩序,一个代表着宗教和信仰,但是他们也一样会患病,一样会失去财富和权威,一样在游戏人生,一样和我发疯和神经错乱,谁也无法逃离命运的束缚。
| 编号:C38·2250901·2343 |
保尔从前对音乐、赛车和帆船运动有着无比的热情,而生病之后这一切都从生活中消失了,“但时过境迁,他现在哪里还能任凭他对体育的狂热恣意妄为?”通过保尔的改变也在传递着我对命运的喟叹;保尔和他第二任妻子埃迪特在柏林看歌剧的时候结识,他们有着让人羡慕的爱情,但是艾迪特比保尔更早去世,再没有人照顾保尔,他陷在一种无助中,从此一蹶不振,通过保尔的无助我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病人生病期间,健康人完全疏远了他们,放弃了他们,只顾如何保全自己去了。”医生对保尔说接近大自然可以让疾病更好地治疗,也是通过保尔我说出了憎恨自然的想法,医生让我在大自然中生活就是为了战胜疾病,但是活在大自然中更意味着“它会置我于死地”;和保尔一样,我是城里人,在大自然中会精疲力尽,有一次为了读到刊登莫扎特歌剧《扎伊德》评论的《新苏黎世报》,我几乎找遍了维也纳也一无所获,“我早把它淡忘了,自然没有这篇文章我也不会就活不下去。”憎恨自然,实际上在讽刺城市,讽刺城市让人盲目、让人迷失,就像和保尔一起,“他与我在夕阳里坐在纳塔尔我家的院墙旁,还在回想着,他去过多少次巴黎,去过多少次伦敦和罗马,喝过多少瓶香槟酒,有成千上万瓶吧,引诱过多少女人,读过多少本书。”
当然,在友谊中完成同构传递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对文学奖的评论,“颁奖并非如我在首次获得文学奖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会提高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奖都是外行颁发的,他们作为门外汉设立这样一个奖项就像是在人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地在你头上排泄一番。”同样如果获奖者去拿奖了,除了低三下四之外,就是被羞辱,所以对于这种侮辱,唯一的办法就是反过来羞辱他们,我详细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那是距颁发格里尔帕策奖很久之前的事情,我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当时报纸报道说,这次颁奖最终以一场丑闻而告结束。颁奖典礼在政府接待大厅里举行,那位向我致所谓贺词的部长,讲的尽是些不着调的话,是他的一位主管文学的官员为他写的稿子,他在台上照本宣科,比如,说我写过一本关于南太平洋的书,当然是胡说八道了,我什么叫候写过这样的书。这还不算,那位部长还改了我的国籍,在讲话里竟说我是荷兰人,我从来都是奥地利人。他在讲话中还说我是专门写历险小说的,实际上我对这种题材一无所知。他还多次说我是外国人,做客奥地利,等等。对那位部长从讲稿上往下念的这些胡诌八扯,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位来自施泰尔马克的老兄,在当上部长以前,在格拉茨任主管农业的秘书,主要负责牲畜饲养,闹出这样的笑话其实并非他的责任,但这位部长与所有其他部长一样的那副蠢相,让人恶心,但我并不为此感到气恼,我听之任之没有干预。然后轮到我致所谓答谢词,表示我对获奖的感谢,我在颁奖前匆忙地、很不情愿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句话,可能稍微带一点哲理性,其实我只是说人是可怜的,注定要死亡的,我的讲话总共没有超过三分钟,这时那位部长便怒不可遏地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我挥着拳头,他其实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条狗,当即离开大厅,在身后把玻璃门重重地摔回去,致使门玻璃“砰”的一声变成了一堆碎片。所有在场的人都跳了起来,惊讶地望着那位离去的部长。一霎时大厅里,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鸦雀无声。随后发生了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幕:那一伙我称为投机之徒的人,紧跟着扬长而去的部长走出大厅,离开之前也都向我示威,不仅谩骂而且挥着拳头,我清楚地记得艺术委员会主席亨茨先生朝我挥动拳头的样子,也清楚记得,人们在这一刻对我表示的一切其他形式的敬意。
后来报纸上还指名道姓批评我,说我粗暴对待部长抹黑了国家,这个关于“丑闻”的故事正是伯恩哈德亲身经历的,也许正因为它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部作品被界定为“散文”。同样还有伯恩哈德对于剧院演出的批评,应该也是他经历的真实事件,“这些扮演主要角色的毫无才华的演员,几乎没有任何摩擦地就能与观众沆瀣一气,阴险地反对他们所演出的剧目,反对他们所演出的剧目的作者”,伯恩哈德认为这是维也纳几百年来的传统,这一丑恶的行径把德语世界的第一舞台变成了“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戏剧妓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混乱、丑陋、没有道德感、病态的社会正是疾病的根源,保尔病了,我病了,所有人都变成了疯子,变成了被天才或杀人犯处理的病人。
虽然我和保尔在友谊的世界构筑了同一性关系,但是伯恩哈德在同构之外却也在进行着一种异构,那就是保尔最终指向了死亡,而我还活着,“我想,从根本上说,我就是持续了十二年之久的死亡过程的见证人,在这十二年里,我从我朋友之死中,为自己继续生存汲取了很多力量”,保尔一步步走向死亡,十二年治病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活着的人正是从保尔的死亡中得到了启示,这种启示和保尔的身份有关。医生萨尔策是保尔的舅舅,却成为了天才式的杀人犯,而保尔的另一个亲戚就是维特根斯坦,他是保尔的叔叔——这部作品的名字之所以不是《保尔之死》而是《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就是凸显了保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更凸显了维特根斯坦对于伯恩哈德来说的象征意义。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而且是天才哲学家,哲学家意味着什么?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精神富有的人,他特立独行,他追求,他藐视一切的规则,他破坏一切的秩序,他被人看成是疯子,他看别人更是疯子——“今天整个知识界,还有整个伪知识界都知道他的《逻辑哲学论》”,伯恩哈德的这句话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嘲笑。
所以保尔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他同他叔叔路德维希一样具有哲学头脑,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反过来也与其侄子保尔一样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以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名声,另一位,保尔,以他的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也许更富于哲学头脑,另一位,保尔,也许更为疯癫;我们相信这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他的哲学写成了书,而不是他的疯癫,我们认为那另一位,保尔,他是疯子,因为他压抑了他的哲学,没有发表它、公开它,只是把他的疯癫展示了出来。”精神疯癫者就是另一种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家也是另一种疯癫者,伯恩哈德所要强调的就是:哲学家和疯癫者被社会所不容,也唯有他们才能真正看透这个社会。所以保尔的死对于我来说具有的意义,就是这种活着而能看透的能力:
他蔑视当今社会,这个社会在所有方面否认其历史,因此这个社会,如他有一次所表述的那样,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陷入了原子科学那种呆钝状态:他抨击腐败的政府和狂妄自大的议会,同样他也抨击那些满脑子虚荣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所谓擅长复制的艺术家。他质疑政府、议会、民众,以及那些创造性和所谓后创造性艺术及其艺术家,如同他不断地对自己提出疑问。他对待自然如同对待艺术那样,既热爱又憎恨,他以同样的激情洋溢和无所顾忌去热爱又憎恨人们。他作为富人看透了富人,作为穷人看透了穷人,同样他作为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为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终作为疯癫者看透了疯癫者,作为精神错乱者看透了精神错乱者。
富人看透富人,穷人看透穷人,病人看透病人,健康人看透健康人,看透是站在更高的地方,是抽身于这个社会之外,不与人同流合污,永远做一个他者,在这个意义上,看透就是死亡本身,这也许就是伯恩哈德在身患疾病的1982年创作这部作品的原因,死亡在一步步逼近,活着的人无可逃避,但是在死亡的他者中体验并感悟人生,或许就是“看透”的本质,于是在保尔抵达了死亡之后,我也完成了一次看透的行为,“据我所知,参加他的葬礼的只有八九个人,我本人那时正在克里特岛上写一个剧本,我把它完成后,立即又将它销毁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