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02《唐璜》:希望你们从湖边迁往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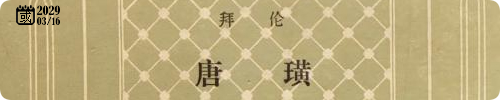
读者呵,我无法强迫你把它读完。这是你的事;一个独立的人格既不应招怨,也不怕受人冷落。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唐璜作为俄国女皇派来的使节来到了英国,看到了“一个报刊、诉讼和毁谤发达的国家”,发现了爱情“不怎么时兴”的国家,但他对这个道德的国度很尊敬,也开始觉得这儿的女人很美。对于唐璜来说,进入英国、发现英国以及生活在英国将开启属于他全新的经历,而这恰好是唐璜第二次旅行的开始:第一次他离开故土西班牙历经海上冒险来到了俄国,这是一次自西向东的旅行,第二次则从俄国来到了英国,以自东向西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逆行”,无论是自东向西还是自西向东,对于唐璜来说,都是对欧洲认识的丰富,都是一种英雄式的成长。
两次旅行在第十二章画出了一条中间标线,而这一章似乎也是拜伦在书写这一英雄史诗时计划的一个中点。在第一章的“开场白”中,拜伦说:“我这一篇诗是史诗,我想把它/分为十二章……”第二〇七节中,他指出第十二章将是最后的终结,“其实在第十二章我还要指出/故事里一切坏人的最后归宿。”本来是计划这部史诗写十二章,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拜伦做出了调整,第二章他写了二百多节,认为这个数目应该是每一章的极限,但此时他已经有了改变整部史诗长度的想法,“本诗将写它十二章,或廿四章:现在我放下笔,鞠躬说声再见,且让唐璜和海黛,为他们的私情,恳求一切赐顾的读者惠予好评。”十二章或者廿四章,或然性本身就显露了改变的可能,到了第三章,拜伦感觉到每一章显得冗长,认为这已经不太像史诗了,于是他想要在重抄时“以一章分割为二”,这种一分为二的做法,拜伦认为“读者绝不会发现”,但也是批评家的见解,甚至举出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观点,于是在之后,每章的节数开始缩减,十二章的计划也最终变成一分为二中被改变。
一分为二,十二章应该就是史诗的中点,廿四章当然是最后的结束,唐璜开启自东向西的第二次旅行也具有了一分为二的标志性意义。但是拜伦没有将《唐璜》写完,1823年5月,他写下了第十七章的十四节,从意大利赴希腊时他随身携带着它,但是这一部分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在行囊中被找到,最终初次发表于1903年厄恩斯特·古勒律治编订的《拜伦诗集》中——第十七章第十四节,拜伦写道了唐璜见到了鬼魂,苍白无神的脸预示着他和鬼魂之间的搏斗,而透过窗格看见公爵夫人,也是苍白的容颜,“而且微颤,仿佛她是熬了整夜,不然就是做梦做得太多一些。”鬼魂和梦境构筑了拜伦这部史诗最后的场景,它以悬而未决的方式让唐璜的命运留出了一个空白。
拜伦没有写到第廿四章,没有交代坏人的归宿,当然也没有呈现唐璜这个英雄的结局,未竟之作留下的当然是遗憾,但是已完成部分,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拜伦在唐璜这个人物身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已经定型,“无法强迫”读者读完,实际上也给予了保持“独立人格”的可能,那么,拜伦历时五年,在逝世时还没有完成的《唐璜》到底呈现了怎样一个史诗故事?拜伦在1818年9月6日写下的《唐璜》第一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出了自己的写作构想:“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此,对这些我就不人云亦云了,而想把我们的老友唐璜来传颂——我们都看过他的戏,他够短寿,似乎未及天年就被小鬼给带走。”拜伦要写的就是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就是唐璜,开宗明义其实也是指出了“英雄”被误解的现实,英雄迭出不穷,但是报刊上连篇累牍的英雄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唐璜,这个短寿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一方面拜伦认为报纸上所谓的英雄都不算真英雄,这当然是一种讥讽:英雄怎么可能“年年有,月月有”?另一方面很多人却忽视了真正英雄的存在,唐璜这一人物出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他够得上英雄。被捧为英雄和被忽略的英雄,这是现实的两种英雄观,拜伦以唐璜这个传说中登徒子为原型重塑英雄,其实就是要用自己的英雄观来驳斥现实流行的英雄主义。
一方面是驳斥和讥讽,一方面是赞赏和挖掘,这便是拜伦写作的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是同一体的两面,它们互为对立,而拜伦的《献辞》更是写作目的的阐述。《献辞》是献给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勃特·骚塞的,骚塞作为“湖畔诗人”,于1813年被英国皇室封为“桂冠诗人”,他在“献辞”中直接指出:“杰出的叛徒呵!你在做何消遣?”将“桂冠诗人”骚塞说成是“杰出的叛徒”,他更是在批评骚塞为代表的“湖畔诗人”,他们是华兹华斯,是柯勒律治,以及所有的反动浪漫主义诗人,“诸位君子呵,由于你们长期以来/不曾见过世面,一意固步自封,你们死守在凯泽克那一隅落,仍旧继续在彼此间心灵交融,于是有了自认为最合理的结论,即诗的花冠只该落在你们手中”,他认为湖畔诗人固步自封,认为他们是“一窠里卖唱的先生”,他们的诗歌“枯燥”“冗长”,所谓的桂冠,只不过是为了声明,却玷污了诗歌,由此,拜伦说:“桂冠大人呵,我现在就向您献出/这以朴实无华的诗句写成的歌。”
对于湖畔诗人的批评,以及对当时英国诗坛的文风和作风的批判,其实贯穿在《唐璜》整部史诗中。在第三章中,拜伦认为文字是有分量的,“一滴墨水/一旦像露珠般滴上了一个概念,/就会产生使千万人思索的东西”,所以哪怕寥寥几字都能传联万代,但是“时间”却“把脆弱的人欺负得多惨”,甚至一张纸都比人长寿,“比他的坟墓、他的一切都更持久。”这种文字比人长寿的讽刺其实就是在批判诗人执著于声誉,声誉是什么,是空话,是幻影,是风,是哲人一笑置之的东西——拜伦甚至举例来说,莎士比亚透过邻人的鹿,培根受过贿赂,泰塔斯和凯撒还在少年时已过恶作剧,克伦威尔还有过戏谑,这些都是坏名声,但是和他们的伟大相比,名声什么都不是。由此,拜伦批评湖畔诗人的名誉观,“例如骚塞/曾经对世人大谈其平等社会/,或如华兹华斯,在未被税局雇用以前,/也给他的叫卖诗添些民主气味;/或如柯勒律治,和骚塞不谋而合,/共同娶了卖帽子的一对姊妹,/这时他那枝飘摇的笔还没有/向《晨报》租出去他的贵族派头。”最后拜伦嘲讽他们的名字“发着罪犯味”,像道德版图上的波坦尼半岛,一切的作为只是给“贫瘠的传记作肥料”。在第四章中,拜伦批评华兹华斯的赌咒:“文风已荡然无存,诗名成了抓彩:只能由俱乐部的蓝衣女士分派。”在第六章里,他称他们为“诸犬”,“我说犬其实是/抬举了你们——狗比你们好得多”,拜伦就是要勾出他们的嘴脸,“正如月亮不因豺狼对她嗥叫/而止步,缪斯也不会在她的诗国/为你们而减色——所以,尽请狂吠!/她仍要对你们的幽窟洒下光辉。”
| 编号:S39·2230306·1928 |
批评湖畔诗人,批评英国诗坛之风,批评诗人的名誉观,拜伦实际上就是在批评英国社会的道德观、教育观,他在诗歌中不时地站出来,以“我”的在场,对英国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和批判。在第一章的开场白中,拜伦介绍了唐璜的父亲和母亲,他一开始说唐璜的父亲是“一个纯粹的西班牙贵族”,说母亲“博学多才,远近驰名”“而品德之高,只有她的才争胜。”但是在唐璜出场之后,母亲变成了“妇德的最端正的化身”,拜伦讽刺道:“连‘嫉妒’也挑不出有任何玷污。哈,尽管别的女人罪过上千条,她可一条也没有,——这才最糟糕。”而唐璜的父亲,则变成了“不学无术”的人。在唐璜被母亲送出去,名义上却是为了考验唐璜,是为了让他成为有德之人。而在第二章,拜伦一开始就讽刺了教育,“哦,纯朴的弱龄学子的教育家!/无论在英、法、荷、西班牙或德国,/我请求你们要动辄鞭打学生,/别管多痛,那有益于他们的道德;/请看唐璜就是例子:最贤的母亲,/最好的教育,他竟然一无所获;/说来很奇怪,真不知什么缘故,/他连人的至宝贞操都保不住。”进而批评这个世界存在的各种毛病,“我们由国王治理,由牧师教导,/由庸医诊治,然后就一命告终;/全不过一会儿:爱情,美酒,雄心,/信念,战斗,尘土,——也许一个声名。”1822年6月,在经过一年半的间歇之后,拜伦重新着手写作《唐璜》第六、七、八章,而这次写作拜伦似乎憋了一肚子气,因为莫瑞不再出版实际,原因是他对诗集前面几章的大胆描写有所顾忌,所以不愿在承担出版之责,于是拜伦在新出版的第六章中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的一段话:“你可认为由于你道德高尚,世间便不再有糕点和啤酒了吗?会有的!而且吃姜也还会辣嘴。”接着他又以诗集受到非难,引用了伏尔泰的两句话:“廉耻逃出了心房,而跑到嘴边上来避难”……“道德越是败坏,就越是谈吐有方;人们想在语言上弥补其在德性上的缺陷。”
批评道德,批评教育,批评诗歌,批评社会,拜伦对种种现象的批评,都是一种破,但是《唐璜》无疑就是他所要立的一个英雄,而破和立的关系在《献辞》中被阐述,也便成为了这本诗集的主题,他认为当“诗的花冠”只落在那些人手中,这是狭隘的见识,“我倒希望你们从湖边迁往大海。”湖边当然是固步自封的湖畔诗人所居之地,它是闭塞的,它是狭隘的,真正的诗人应该面向大海,而且进入大海之中,而“迁往大海”就是一种英雄该有的胸襟,由此拜伦阐述了《唐璜》作为英雄史诗的定位,“我这一篇诗是史诗,我想把它/分为十二章,每一章要包括/爱情呵,战争呵,海洋的风暴呵,/还有船长,国王,以及新的角色;/其中穿插的故事要有三起,/并仿照荷马和维吉尔的风格,/我正在构制着地狱的全景,/好教这一篇史诗不徒负虚名。”
|
| 拜伦:我是和地上的缪斯同行 |
是史诗,是英雄史诗,是有爱情、战争、海洋的风暴的英雄史诗,是仿照荷马和维吉尔的风格书写的史诗,是在地狱全景中安排了坏人最后归宿的史诗,这就是拜伦对《唐璜》整体的架构,唐璜和他遭遇的经历,如何体现拜伦的英雄观?在第一章里开场白介绍了唐璜的父亲和母亲之后,便是父亲“唐·约瑟便已一命归阴”,父亲死去儿子登场,父与子的转换具有的是关于英雄出场的隐喻,父亲不学无术,但是唐璜却熟知各种语言,他广猎科学,精于抽象的玄学,在人文领域更是博览群书,深入钻研,而且他在十二岁时就成为了安静的美少年。唐璜的出场,就具有了英雄的气质,这种气质所包含的是求知热情,是科学精神,是钻研激情,更是一种美,不仅是对父亲无知的一种消解,更是对社会腐朽风气的一种否定。
但唐璜出场仅仅是英雄的静态展现,拜伦在史诗中构筑的旅行经历才是成为英雄的一种动态过程,他在爱情中磨砺,在战争中考验,在大海中搏击,最终塑造成真正的英雄。和唐娜·朱丽亚的爱情是唐璜接受的第一次考验,这个二十三岁的女人“贞洁而又迷人”,明亮的眸子,富有光泽的头发,晶莹得透明的前额,好似天弓的美貌,泛着青春红色的脸蛋儿,她无疑就是美的化身,“魅力之于她有如海有盐,花有香一样天成,或如维纳斯有腰带,爱神有弓”。但是拜伦的审美观并不仅仅在于外表,他认为真正的美“荡漾着一种似是欲念”的东西,而真正的爱是“用于面对诱惑”并且将它战胜而不是逃避,它是“圣洁的神坛的火”,而这把火需要成为英雄的唐璜点燃。于是在拜伦的审美观、爱情观中,英雄终于在战胜诱惑中真正出场,两个人在爱中得到享受,体会到了恋爱之美。但是这也是违背道德的事,因为朱丽亚是有妇之夫,她的丈夫带着火把、亲友和仆从赶到,并发现了唐璜,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朱丽亚勇敢地保护了唐璜,“快跑吧,唐璜!老天哪,不要多问——门开着,你走那常来往的箭道,还来得及逃出去!快点,这儿是花园的钥匙——再见吧,快,快逃!”
战胜诱惑包含在朱丽亚的爱情观中,而勇敢战斗也成为她爱情的表达,无疑朱丽亚成为唐璜第一个爱的女人,也是将这种无畏融进了唐璜的世界,对于英雄之塑造来说是重要的力量。唐璜无法在西班牙呆下去了,看起来是母亲将他从卡提斯送走,实际上对于唐璜来说不只是离开,更是考验的开始,和故土永诀的唐璜感觉自己就是“举国出征的士兵”,而面前的大海又成为对他的考验。在大风大浪中,二百个灵魂脱离了躯壳,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那只狗以及仆人彼得利娄都被生吃,最后剩下的只有唐璜。海上历险是唐璜经历的第一个考验,而战胜了考验的他也迎来了另一个女人,岛主的女儿海黛。海黛也是美的化身,“她的芳龄不及二十,却出落得像一株秀丽的树,婀娜动人”,美在这里有化为力量,唐璜在海黛的眼神中“学会了希腊文初阶”,于是两个年轻人获得了快了,获得了爱,“一个长长的吻,是爱情、青春和美所赐的,它们都倾力以注,好似太阳光集中于一个焦点,这种吻只有年轻时才吻得出;那时灵魂、心和感官和谐共鸣,血是熔岩,脉搏是火,每一爱抚、每一吻都震撼心灵:这种力量我认为必须以其长度来衡量。”
这是灵魂得到升华的爱,拜伦在此阐述了这种爱的意义,混杂着罪,却是美的理想,“据柏拉图说,那是唯美的感受,是感官的无微不至的扩展,它纯属于精神,博大而神奇,自星空降落,就充塞于天地间;要没有它,人生会显得太沉闷。”当海黛的父亲兰勃洛回来,爱也需要经受更大的考验,而勇敢的爱更成为精神的一部分,“爱情在他们是生命,它如此之浓,不是感觉,而是整个的精神内容。”海黛为了救唐璜最后死去,而唐璜受伤之后也落入了人贩子的受众,当他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土耳其,而且在土耳其市场上被出卖。唐璜最终被鞑靼人拍卖,他和黑人巴巴装扮成基督教尼姑,被卖到了苏丹皇宫,而在这里他又遇到了苏丹之妻古尔佩霞,她是美的化身,而这种美就像她的眼睛一样,“一半是欲望,一半是命令”。
对于唐璜来说,另一种考验来自战争,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伊斯迈之战爆发,而这也是这部史诗表现英雄最重要的一部分,“永恒的荷马呵,我现在得描写/一场围攻,比你那篇希腊战报/伤亡要多得多,而且有更凶的/杀人器械,更飞速得叫人难逃;/不过我得承认,像我这支笨笔/若和你竞争岂不是自寻苦恼?/那就像是小溪要和海洋相比——/但我们现代人流血却胜过你”。对于唐璜来说,战争中的锻炼是英雄的塑造的关键,他初次深临战阵,“那深夜的集合,那沉默的行军,又冷峭又黑暗,一点也比不上走过凯旋门下那么精神抖擞”,身为男人,唐璜既能在儿女情长中找到爱,也能够在战争中表现血腥,于是他“跟着他的鼻子和荣誉”,向着炮火最密集的地方冲去。在这场战争中,唐璜杀入战场是激情,是血性的表现,但是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暴力,“在伊斯迈的普遍屠杀中/他从哥萨克刀下救出的女孩”,小莱拉被救下来,这是对生命的关照,而英雄在敢爱敢恨中变得更博爱,“唐璜忍不住挥泪,并立誓保护她”。
这种爱其实也是对死亡的反抗,“死亡正笑对我们所痛惜的一切,请看谁不在时时惶恐!死亡的箭威胁着生命,尽管并没有射出,但谁看见它的狞笑而不恐怖!”唐璜的英雄色彩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具体的表现。之后俄国的女皇喀萨琳爱上了他,经历了战争的唐璜成为了俄国人,也更具有了英雄气质,“唐璜不求于宫廷,反为宫廷所求,这倒是少见的;这多半应归功于他的青春,和他勇敢杀敌的传闻;而像一匹良种马,也归功于血气,和他那换来换去的漂亮的行头”。由此唐璜开启了第二段旅程,他被派往英国,开始了英国的生活。在英国,拜伦让唐璜在所见所闻中英国的社会现象提出批评,而他所遇见的女人也不断丰富着他的爱情观,他成为了贵族涩座上宾,他的身边是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费兹甫尔克公爵夫人、奥罗拉,让唐璜进入婚姻殿堂似乎成为了她们的目的,“肉体和灵魂合在一起,比一个孤独的游魂更强有力。”
但似乎在这里,唐璜所具有的英雄气质逐渐减弱,爱或者美也慢慢变成一种外表上的呈现,唐璜变得矛盾,“唐璜怀着悒郁的心情,悠悠然/像起伏在阴阳两界间的波浪,/在午夜就寝的时候,他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却只是黯然神伤;/呵,不是罂粟,而是悲哀的垂柳/摇摆在他的床前。”也终于在第十七章看见公爵夫人苍白的容颜、微颤于梦境中,一切戛然而止——唐璜如何面对矛盾?如何看待爱情和婚姻?如何寻觅最理想的柏拉图主义?又如何真正成为英雄?拜伦以未竟的方式留下了唐璜式英雄的悬疑,也让自己的生命猝然终结,但是从湖边到大海,也只有唐璜式的英雄完成了转变,冒险,战争,以及爱,组成了英雄史诗永恒的主题。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