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30《清诗别裁集》:惟取诗品之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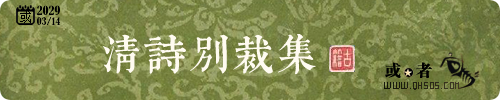
人必论定于身后。盖其人已为古人,则品量与学殖俱定。
——《凡例》
身前是古人和前人,身后是今人和后人;身前已盖棺定论,身后是未知;身前是“虽殚苦心,只抽孤绪”,身后是“窾启未逮,所深望焉”——身前和身后仿佛划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当沈德潜选编了《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又在“时年八十有八”完成《清诗别裁集》,身前和身后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已知:身前的已知是对国朝之诗人的定论,不管是诗人之品量与学殖之定,也是诗作之优劣之定,正是从身前“已为古人”的诗人和诗作之定论,对于后世之诗教也有了盖棺定论。
历时十六寒暑,成书三十二卷,收录九百九六人的三千九百五十二首诗作,《清诗别裁集》的确是一种大体量的构筑,完全超越了《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的容量,对于沈德潜来说,花如此精力编选如此厚实的诗选集,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自己就生在清朝,所见所闻所阅提供了比前朝文本更多的视野,而且沈德潜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即一七六〇年,按照他选诗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时间去世的诗人诗作才可以收录,而这一时期仅占清一代的三分之一强,原名《国朝诗别裁集》的《清诗别裁集》更应该称作“清前朝诗别裁集”——如果沈德潜活过了整个清代,那么还可能收录两倍的诗人和诗作,这样的体量几乎无可想象。正因为沈德潜对于国朝诗的特别感情,在这本别裁集里,收录了不少姓名不彰的作者,他们的专集在“身后”湮没失传,而某些作品依赖此书得以流传,对于清朝前期诗作的保存,沈德潜做出了一定的功绩。
而另一方面来说,沈德潜编选别裁集就是梳理“升降盛衰之大略”,其目的就是在“芟夷烦猥”中让文本“为学者发轫之助焉”,他在《唐诗别裁集》中就说过:“同志者往复是编而因之以递亲乎风雅,如适远道者陆行之有车马,水行之有舟楫。呜呼,其或可至也哉!”后来者有车马有舟楫,方可以远道而行,而这种行就是连接古人和今人,前人和后人,“今人与古人之心,可如相告语矣。”当身前的作为为身后服务,当身前的定论为身后发轫,沈德潜的这种功用观贯彻在他的诸本别裁集里,而这体现的就是他的诗教,在《清诗别裁集》这本反映沈德潜自我生长的“国朝”诗选集中,这种诗教的表达更为直接,在成书而写的《序》中,沈德潜说:“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内外,均沾德教。”这是“圣圣相承”的国朝,这是都为“文思天子”的国朝,这是“均沾德教”的国朝,所以给诗人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余事作诗人者,不啻越之缚,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超大体量的《清诗别裁集》当然是为了证明国朝优于任何一个时代。
但是沈德潜也比较了其他诗集,比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选》,比如朱竹垞《明诗综》,不仅《清朝别裁集》收录诗作不及这两本选集,只有“十之二三”,而且沈德潜谦虚地认为,“自问学殖疏浅,见闻狭隘,中间略作小传,远逊牧斋之详;略存诗话,远逊竹垞之雅。”他们的诗集都是“备一代之掌故”。但是沈德潜由此也提出了自己这本选集有别于他们的优势:“而予惟取诗品之高也。”数量上不及,甚至小传之详、诗话之雅比不上前两者,但是“不嫌其多”却有鲜明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而予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这就回到了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中,这个观点在《凡例》中表达得更为明确,“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他认为自从陆机“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还“奉以为宗”,温柔敦厚之旨渐失,所以沈德潜要利用别裁集的机会重新推崇这一诗教,重新让诗歌具有立言功能。
在《凡例》中,沈德潜对“不拘一格”的温柔敦厚诗教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他选诗的标准是“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突出诗作而非诗人,“盖建竖功业者重功业,昌明理学者重理学,诗特其馀事也。”他认为诗重在言物,言物体现了诗教,“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那些“徒办浮华”的诗文,那些“温柔乡语”的诗作,“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他还认为诗要有理,“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那些“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的打油诗完全是笑话……无论是“以诗存人”的标准,还是“其言有物”的诗观,或者“贵在理趣”的要求,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要有立言的功能,那就是温柔敦厚,而这一切就是沈德潜所说的“诗品”,而且“惟取诗品之高也”。
《清诗别裁集》中收录诗作最多的几位诗人,虽然不是以人存诗,但是在沈德潜那里都体现了他们的诗品。钱谦益的诗作被收录的有32首,沈德潜认为钱谦益“天资过人,学殖鸿博”,在生平著述上,“大约轻经籍而重内典,弃正史而取稗官,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但是在朝代更迭、年岁老去之后,钱谦益的诗观发生了改变,“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向尊之者,几谓上掩古人;而近日薄之者,又谓澌灭唐风,贬之太甚,均非公论。”但是在以诗存人上,沈德潜收录了他那些“激气节,感慨兴亡,多有关风教者”的诗作,而这正体现了他的诗品观,钱谦益的《玉堂双燕行送刘晋卿赵景之两太史谪官》(“玉堂昼暖熏风香,双双燕尾摇仓琅”),沈德潜称之是“为谪官者言”,玉堂双燕“自宜以衔泥补屋望之”,所以,“此立言体也。”他评价钱谦益的《后观棋绝句》(“寂寞枯枰响泬漻,秦淮秋老咽寒潮”)“此牧斋自伤末路也。残局自有胜着,只是人不肯寻耳。”钱谦益在《读史记戏书》中发出了“绛灌但知谗贾谊,可思流汗愧陈平?”的疑问,沈德潜认为,这是“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一种笔墨”。
| 编号:S27·1950310·0101 |
吴伟业的诗作收录28首,沈德潜认为和钱谦益一样,多流露出朝代相迭之后的感慨,而吴伟业更重于故国之思,《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于此。”《病中》曰:“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些诗作都让读者“每哀其志”,但是沈德潜认为,吴伟业的诗作表现在五七言近体,“声华格律不减唐人,一时无与为俪,故特表而出之。”这就回到了重现唐音的诗品上,他的《秣陵口号》(“车马垂杨十字街,河桥灯火旧秦淮”)一诗“沧桑悲感,俱近盛唐”,《恭纪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君王射猎近长安,龙雀刀长宝鞍”)则评价为“颂扬中不失箴规,此惟唐人有之”。收录诗歌24首的龚鼎孳,沈德潜认为他和钱谦益、吴伟业合为三家,其诗歌风格也体现了“唐音”,而且是“少陵意”,《岁暮行》》《姑山草堂歌》《樟树行》都是“用少陵韵”,沈德潜评价说:“合肥时用杜韵,而能以意驱役,绝无趁韵之迹,所以高于众人。”
其他收录诗作较多的诗人有“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闰章和宋琬,分别选诗32首和26首,“今就两家论之,宋以雄健磊落胜,施以温柔敦厚胜,又各自擅场。”尤其是对施闰章“温柔敦厚”,沈德潜冠以“诗品”,他的《叔父同弟阮迟予芜关次日予北发》(“小泊聚江干,帆开泪未干”),沈德潜评价为“家近难归,老于宦途者知之,神明杜陵,乃有此种”,《季天中给事以直谏谪塞外追送不及》(“策马送君君出门,朔风动地卷蓬根”)则完全体现了“忠君爱亲表戍臣心事”。收录47首的王士禛,沈德潜评价他的诗歌“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叶燮收录诗歌21首,“今观其集中诸作,意必钩元,语必独造,宁不谐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队者。”尤侗收录诗歌25首,沈德潜评价说:“开阖动荡,轩昂顿挫,实从盛唐诸公中出也。”朱彝尊收录诗歌18首,沈德潜认为他的诗作“各体具备”,但沈德潜有自己的偏好,“然予所录者,仍以唐体为归。”
很明显,沈德潜所谓“诗品”就在于展现温柔敦厚之诗教,而这一诗品的具体体现,则是“唐音”,“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他否认自己贬斥宋诗,只是自己的志趣都在唐诗,“故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从所尚也。”这种复古主义在《明诗别裁集》中有特别体现,而在《清朝别裁集》里,有过之而无不及。程可则的《送纪载之备兵肃州》(“万古焉支路,迢迢欲上天”),沈德潜评点:“不必奇崛,自是唐音。”顾大申的《雪后登歌风台示沛令》(“一剑收秦鹿,秋风万里心”),沈德潜评点具有“盛唐气魄”;他认为汪琬的《送魏子存之成都同西樵周量贻上》(“凤城垂柳为君攀,西去高轩指散关”)“此犹近唐人体魄”;陆鸣珂的《盘上鸡头关》(“北栈行将尽,鸡头势转雄”),沈德潜认为,“此种竟是唐人绝句,于浑成中见风神,愈咀吟愈有味也。”李念兹的《云》“怀归之作,自是唐音”,严允肇的《诸将杂感》“风格从杜诗中出”,沈钦圻的《送杨曰补南还》“是唐人绝句品格”。
重现唐音或者在诗作风格上得到体现,而沈德潜对于诗品的阐述更在于诗作的“立言”上,丁澎在《慰李琳枝侍御诏狱》中写道:“抗疏今何事,身危直道难。忽闻收北寺,不敢问南冠。草莽臣无状,朝廷法屡宽。圣明知汝戆,频取谏书看。”沈德潜直接指出这一诗作“慰臣直望主恩也”,其中所表达的“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使其成为“一种立言之体”;张玉书在《送邱曙戒前辈之武昌》写道:“猿声夹岸听斜阳,江树苍茫接故乡。却较长沙归路近,行吟何事怨潇湘。”沈德潜指出,这即“圣主恩深汉文帝”意,“是为温柔敦厚之遗。”他还认为张英的诗作大都是“应制诗”,“入词馆者,奉为枕中秘,而风格性灵不系此也。”沈德潜评价傅昂霄的《凉州词》(“九月霜高塞草腓,征鸿无数向南飞”)“温柔敦厚,可与唐贤绝句并读”,王顼龄的《送李天生归养》(“廿年高隐为承欢,诏趣蒲轮却聘难”)“以养母急于辞官,尽子职即以报君恩也。立言有体”,许汝霖的《送张侍御归里》(“孤忠原不问升沉,正气棱棱自古今”“上章教孝,此章劝忠,立言自应尔尔”……
从诗品到诗教,从诗教到立言,无论是表达“直望主恩”的衷心,还是教孝劝忠的教化,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观似乎显得有些露骨,而且,在“以诗存人”上沈德潜也充分突出其诗品,“若传志可考,轶事可传,诗话可引,或详或略,辄缀评论,使读者得其诗品,并如遇其为人。”他认为以前的闺阁诗“多取风云月露之词”,一些青楼、失行妇女的诗作都被选入,但是他这一选本所录则要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诗品,“罔非贤嫒,有贞静博洽,可上追班大家、韦逞母之遗风者,宜发言为诗,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而风格之高,又其馀事也。以尊诗品,以端壹範,谁曰不宜。”僧人之诗当然也可以收录,有“弃儒而逃入禅学者”,有“习日头禅说,以偈为诗”者,但是沈德潜对“能读儒书通禅理者”格外赏之,这也是诗品的一种体现。
于是,在闺阁诗中,他选录了“夫亡无子,请大归守志,以苦节闻”方维仪的诗作,收录“忠臣之女”侯怀风的《感昔》,评价尹琼华:“秉贞淑慎敦孝行,年二十三殁,培基以有子不再娶,重妇德也。”尤其写道了袁枚之妹原机的故事,袁机从小许配给如皋高氏子,后高以子有恶疾,愿离婚,但其实并非是恶疾而是品行不端,但是袁机却说:“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后来嫁过去才知道真相,“高躁戾佻荡,倾奁具为狎邪费。不足,扑抶外,至以火烧灼之。姑救之,殴母折齿。既欲鬻妻以偿博者。”袁机这才回到母家,孝养母氏,高氏子死后,袁机“哭泣尽哀,血泪尽”,一年之后自己也死了。沈德潜将袁机的小传变成了一个故事,但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不是为了增加趣味,而是从其诗品中得知其为人,而袁机的诗品就是人品,“女子中苦行,无逾此也。”袁机写有《闻雁》一诗:“秋深霜气重,孤雁最先鸣。响入空闺静,心怜永夜清。自从成只影,同是感离情。谁许并高节,寒林有女贞。”所以沈德潜评价道:“应自归母家手作。自怜只影,静正守贞,言外绝无怨尤,可以哀其志矣。”
袁机的苦行,作为女子遵守的是妇道,和方维仪的“苦节”、尹琼华的“妇德”一样,在“哀其志”中成为了沈德潜所谓的诗品和人品,它和对唐音重现的复古主义、教孝劝忠的立言论,共同构筑了沈德潜“温柔敦厚”诗教观,身前已定论,身后自当学习,八十有八的沈德潜终于完成了一桩大事,他为国朝诗歌备好了通往殿堂的陆行之车马,水行之舟楫,“四方学者,有谅予之愚,窾启未逮,所深望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