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5《与弗里茨·朗一席谈》:“独”眼看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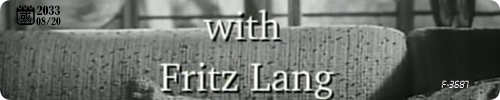
我讨厌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如果导演在拍摄了一部作品后,他们的作品根本表达不了他们的思想,导演还要在访谈中向观众解释影片拍摄动机,这样蹩脚的导演根本不应去拍电影……
一句话并没有说话,但是纪录片却戛然而止,时间停止在第48分钟,而整部纪录片的时长是140分钟,48分钟只占了三分之一,这种“结束”当然是视频上传的原因,而这也意味着威廉·弗里德金对弗里茨·朗的“一席谈”在进入“1975”章节之后变成了一种断裂,而电影基于时间轴展开的弗朗茨电影人生似乎也被推向了一种未知——仅仅距离访谈一年后的1976年,86岁的弗里茨·朗便走完了他传奇的人生。
这种时间的断裂当然不是一种预言,从前一章节的1933年直接跳到1975,也像戛然而止的纪录片一样,被抽离的中间部分也和技术有关。断裂、终止、抽离,在另一个意义上似乎在印证着弗里茨·朗在这次访谈中对电影人生的回顾充满了太多的戏剧性:1917年-1918年是纪录片的第一个章节,弗里德金的镜头对准弗里茨·朗家里的那只钟,就是对于时间的强调,人生就是这样被时间连接起来,从离开家自暴自弃到进入布拉格的餐厅饮最喜欢的马提尼酒;和朋友合作开始写剧本卖钱;一战爆发时参军入伍,受伤后获准休假,遇到了梦中情人,却因囊中羞涩而放弃;舞台剧导演彼得·奥斯塔迈尔邀请他出演一个角色,得到了一千先令的报酬;埃里克·波玛答应将他从奥地利军队中弄出来,然后让他去德国写电影剧本,波玛的承诺没有兑现,奥地利却发生了革命;开始投身电影,写剧本思如泉涌,之后亲自拍摄,1925年《大都会》根据妻子的小说改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乌法公司发生矛盾,公司撤走了投资;1931年拍摄《M就是凶手》,塑造了“社会公害”型人物;1933年拍摄《马布里博士的遗嘱》,因为在最后喊出了反纳粹的口号,被纳粹请去,在去见戈培尔的时候,预感到了不妙,想到了离开的计划,但是戈培尔没有提到那句口号,反而传达元首的想法让他为国家社会主义拍摄一部电影,弗里茨·朗没有拒绝,在离开戈培尔的办公室后马上想去银行取钱,但是银行已经关门,只好拿走了家里的钱,让仆人汉斯去买了一张去比利时的火车票,然后和妻子分完了珠宝,赶往火车站,坐上了火车开始了逃离;到处都是穿黄制服的纳粹士兵,弗里茨·朗装睡,把珠宝和钞票藏起来,纳粹进行检查,唯独他的那间卧铺没有进来,最后终于平安抵达了比利时,也告别了在德国担惊受怕的生活……
| 导演: 威廉·弗莱德金 |
从1917年第一次看电影到1933年逃离德国,弗里茨·朗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遭遇,其中有着太多的变故和偶然,尤其是被戈培尔接见、在火车上完美避开纳粹,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按照弗里茨·朗的说法,这就是命运,“我本来不相信命运,但后来慢慢地改变了看法,命运并非是不可避免、不可改变的,命运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生。”当然最后选择逃离就像是灵念式的召唤,他没有迟疑就选择了这条正确的道路,这的确可以看作是弗里茨·朗对命运的主动把握。但实际上弗里茨·朗所提到的这些细节也有过争议,是否他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难辨真伪是不是就是弗里茨·朗在强调命运的自我创造时,也在表达人生也是可以被创造的?或者说,弗里茨·朗以回忆的方式在创作另一部人生电影?
“与弗里茨·朗一席谈”,弗里德金把镜头对准弗里茨·朗,以固定机位拍摄坐在沙发上的弗里茨·朗,就是把讲述的时间全部交给了他,但是这里有一个隐喻性的表达:镜头前弗里茨·朗戴着眼罩,“独眼龙”的他看着镜头,但是在镜头的前景里,出现的是弗里德金的模糊的后脑勺,它若隐若现,有时出现有时不见,而当这个黑影出现时,脑袋微微偏离的弗里德金露出的是眼镜的左边镜片,而且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这整合正面弗里茨·朗的眼罩形成一种呼应,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部,一个是清晰的,一个则是模糊的,一个是戴着眼罩看不见,一个则戴着眼镜看见——看见和看不见构成的不仅仅是对话的呼应,而且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立,而在访谈过程中,两人就在问和答之间形成了肯定和否定的微妙关系,弗里茨·朗在作答时几乎没有笑容,在驳斥弗里德金的观点时甚至还带着一些情绪,在这个意义上,狭小空间里的对话就变成了正在发生的访谈式电影。
在谈到《大都会》时,弗里德金认为这是一部前瞻性的电影,弗里茨·朗却说自己很讨厌它,弗里德金问:“这部电影和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弗里茨·朗在说出“我不知道”后,又说出了讨厌它的原因:这是改编自妻子的小说的电影,他不喜欢妻子的那个观点:“只有良心才能成为大脑和手的桥梁。”弗里德金之后问他会不会将它拍成有声片的打算,弗里茨·朗似乎很反感这个有些幼稚的问题,“先拍默片,然后拍有声片,如果再回到默片的路上,就会失去电影的节奏感。”当谈到《M就是凶手》时,弗里茨·朗也否认了这是一部谋杀的电影,而是关于“社会公害”的电影,选择彼得·洛作为主角也是因为“没有人相信他这么老实的人会杀害孩子”,社会公害不是用暴力杀人,“我反对在电影中展示暴力,我也讨厌暴力”,《M就是凶手》其实真正揭露社会公害的是最后一个场景,法官说“根据法律”宣判,之后的镜头就是三位母亲,然后他们对社会进行了讨伐:“这不会令我们的孩子起死回生,我们必须更小心保护我们的孩子。”在弗里茨·朗看来,最后的这句呼声才是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但是这个画面被剪掉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种行为也是对电影的公害。弗里德金问他在德国的电影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悲观的世界观?弗里茨·朗非常严肃地说:“当你在电影中涉及到一种社会公害,你没有掌控权,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现实。”
对电影的理解,对社会的批判,对制片人的讨厌,对暴力的否定,弗里茨·朗与其说在完整回忆自己的电影人生,不如说在和弗里德金的问答中寻找某种情绪表达,这种情绪表达是一种独特、独立的“独”眼看世界的方式,而对面的弗里德金在引出话题时又不断被弗里茨朗纠正和辩驳,这是不是让最后那句戛然而止的话具有了某种针对性,他说的是自己,说的是电影导演,是不是也在提醒采访他的弗里德金?而在说到坐在离开德国的火车上装睡时,“我想起了对演员说的一句话,要是你想演得好,就要真正变成你演的角色。”装睡是在演戏,逃离是演戏,人生是演戏,这充满了情绪表达而展开的对话是不是也是在演戏?

《与弗里茨·朗一席谈》电影片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658]
顾后:巍巍青山岸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