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7《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将我们带入隐秘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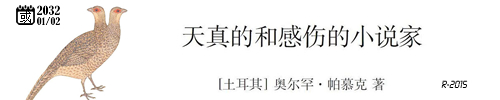
我在哈佛发表这些演讲之后,不断有人问我:“帕慕克先生,你是天真小说家还是感伤小说家?”我想强调,对我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收场白》
作为阅读者,保持着阅读时摘录的习惯,而当摘录完毕进行“二次阅读”的时候,便把文字翻译中的“想像”都统一替换成了“想象”——这并不涉及奥尔罕·帕慕克的原始文本,它只和翻译有关,和汉字有关,和一个读者的理解有关。为什么更偏向于“想象”?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想象,作为名词是在心理学上的一个过程,即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作为动词,指的是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具体的形象;而“想像”虽然在词典上也有条目,但是更多是一种动词,而为名词是和“想像力”结合在一起,等同于“想象”。想象和想像之“象”和“像”的不同,也就在于“想象”是一种偏向于幻想的设想,是对形象的再创造,而“想像”更尊重现实的形象,是一种对形象的再现——想象的对象更多属于意识中可感的形态,比如印象、景象,而想像的对象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比如图像、雕像、人像。
可以通用,也有所区别,在在汉语世界里,它们被称为“异形词”,是殊途而同归?还是同归而殊途?封面的设计似乎也是对这种疑问的解读,素洁的封面上,是一只漂亮的鸟,但这是一只吗?只有一个身体却分明是两个头,两个头朝向不同的方向,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异向的目光正如想象和想像构成的“异形”,所以当它们形成了不同观望和探寻的方向,它们是一体还是二分?封面设计当然不是为了回应读者对于“想象”而和“想像”的质疑,这种一分为二的视角呈现恰恰是为了更具象的方式反应这本书的主题:天真的小说家和感伤的小说家,他们的目光是相异的,他们看见的世界是不同的,当然他们创作的小说也是有区别的:谁在想象?谁又进入了那个想像的世界?
奥尔罕·帕慕克2008年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六场诺顿演说,在演说中他引用年轻时读的席勒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以“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为宗题,区别了这两种小说家创作方法。席勒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天真的诗人,一类则是感伤的诗人,按照帕慕克的理解,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率真地写诗,不会顾虑文字具有的理智或伦理意义,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在他们看来,诗就是自然赋予的一个有机印象,诗人就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写诗就是将自然赋予的诗性通过自然造化的诗人写出来,所以,“诗应该不加反思地就流出笔端,诗甚至可能是获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种力量的启示。”而感伤的诗人是多情的,是反思的,他们不确定词语是否涵盖了真实,是否可以达到真实,也不知道他是否可以传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关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更加注重自己写的诗,在反思甚至质疑中,他会对感觉本身有所怀疑,所以当把自己的情感和感知融入诗行的时候,诗人会考虑更多教育的、伦理的、理智的原则。
席勒是从诗歌方面区别了天真的和感伤的作者,当帕慕克引用席勒区别的两类诗人,一开始并没有将其变成“小说家”,而是从一个阅读者的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帕慕克是从读者的身份切入这个区分的,就像第一讲的主题一样: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在创作小说之前,帕慕克就是一个纯粹的读者,在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什的家里,他阅读了父亲的藏书,找到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书,“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由此决定成为一名小说家。”那么,除了成为小说家的理想之外,帕慕克在阅读时到底意识到了什么?阅读小说,可以目视,可以想象,可以半心半意,帕慕克则是在一种“被吸入”的状态中,他说一开始那些打开书页前现实中的影子慢慢淡化、消逝,随着一页一页的深入,新的世界在面前展开,而且越来越具体和清晰,“就像那种神秘的绘画,在倒上试剂的时候,就会慢慢显现出来。”这就是被吸入而进入的状态,从此内心那片宽广和深远的景观伴随着暗中涌动的阴影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不了多久,这种剧烈的、令人疲倦的思维努力就会产生结果,一幅我渴望看到的宽广景观在我面前展开,犹如烟雾消散后一片广袤的陆地,呈现出所有栩栩如生的细节。”最后,小说叙述中的事物就完全变成了自己眼前的事物,而自己也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轻松愜意地临窗而立,眺望窗外的景色。”
| 编号:E39·2240905·2173 |
这种阅读的感受,帕慕克认为是“恍若进入梦境”,亦幻亦真也就将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混淆了,“我们阅读故事就像在看风景,我们的心灵之眼将故事转化为图画,努力让自己融入图画的氛围之中,受其感染,并且实际上在不断地追寻它。”正是这种体验让他对小说有了特殊的感情,“我们在长远的视野和飞逝的时光之间穿梭,在普遍的思想和特殊的事件之间游走,速度之快非其他任何文学体裁可以赐予。”也许这就是他爱上阅读小说的原因,对比于席勒所做的区分,帕慕克认为,天真的读者就像是乘车穿过大地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理解窗外的乡野和人,相信窗外景观的力量,也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甚至自己完全融入了这片大地,而感伤的人会认为窗外的风景被窗框限制了,他们在窗玻璃上还发现了泥点,于是他们陷入了沉默。当自己是一个读者进入小说世界,当小说世界混淆了虚构和现实,帕慕克并没有成为天真的或感伤的单一读者,他说自己在天真和感伤之间徘徊:观察到了场景并跟随着叙述,然后把词语转化为意识中的意象,同时提出疑问,哪些是真实的体验,哪些则是想象,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现实真的就是小说叙述中的那样?在阅读中获得了在诗意和韵律体验中的快乐,开始对小说人物和作者进行道德判断,自己收获了知识、深度和理解……
帕慕克将阅读小说时意识所执行的操作归结为9点,其中最后一点是:“我们全神贯注地追寻小说的隐秘中心。”在他看来,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一个关键就是有一个隐秘中心,和史诗、中世纪传奇或传统冒险叙述不同的是,小说的人物复杂,小说关注日常生活,小说深入现实世界,它之所以拥有独特的力量就在于存在这个隐秘的中心,“更准确地说,小说依赖于我们相信其中应该有一个我们要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追寻的中心。”这个中心存在的意义也是不断激发阅读兴趣所在,帕慕克认为,阅读小说就是进入梦境,就是在忘记其他一切事情中获得世界的知识,获得世界的知识就是“为了建构自我,塑造灵魂”。帕慕克说到这个隐秘的中心,是从阅读的角度去发现和探寻的,但实际上当他爱上阅读之后,要成为一个小说家就成为了强烈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作者也是阅读的意识之一,那么,帕慕克对天真的和感伤的读者的混杂状态也进入到了如何成为一个融合虚构和现实的小说家使命。
他写完《纯真博物馆》之后,会收到别人对小说提出的问题,很多读者会问的问题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凯末尔是不是就是你?小说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当然不是作者自己,但是凯末尔却又有着帕慕克自己的影子,看起来矛盾却恰恰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哪些部分基于真实生活体验,哪些部分出自想象,这样的追问无疑是阅读小说的乐趣之一。”这是阅读小说的乐趣,也是小说创作的意义:将虚构与真实融合起来,将天真和感伤结合起来,“读小说和写小说一样需要在这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徘徊。”之所以这是读者和作者共同的问题,之所以是天真和感伤的融合,就在于小说的意义就是“将我们带入其许诺的隐秘真相,带入中心”。在这里,帕慕克也从阐释学的角度说明了作者和读者的区别:作者创作句子,他可能会为读者预设一个细节,读者阅读,也可能会认为作家是为自己设计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典型的镜子说,帕慕克当然认为这样的小说阅读体验是被“染色”的,因为,读者和作者从来不会对小说的虚构性达成一致,按照阐释学的说法,作者写完小说,小说交到读者手中,作者就死了。但是这种死却不是一种写和读之间的断裂,帕慕克用另一个角度解读是:“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当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
而这恰恰就是帕慕克所强调的作者和读者的同一性,不是对文本主题理解的同一性,而是那种进入世界的同一性,那种共同探寻隐秘中心的同一性——帕慕克要远离两类读者,绝对天真的读者,因为他们认为小说就是作者的自转,另一类是感伤的读者,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小说都是绝对的虚构,“我必须提醒你们要避开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体会不到阅读小说的乐趣。”阅读小说是为了追寻中心,“像成长小说里年轻天真的主人公满怀好奇、真诚和信仰去寻觅生活的意义,我们将努力朝着小说的中心前进。”创作小说也是在追寻这个中心,所以再次回到“小说家”的角色,帕慕克回顾了自己从阅读者变成创作者,在追寻这个隐秘中心道路上所走过的路,也揭示了如何在这个世界里让读者有寻找的乐趣。“小说艺术的根本问题不是主人公的人格或性格,而是故事里的宇宙如何呈现给他们。”他既有天真的一面,也有感伤的一面,既有天真和感伤之间的矛盾,也有两者的融合——这个“他”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小说家本人,“超越自我的限制,将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观看尽可能多的事物”,就像登上山顶的人,是为了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
帕慕克是在创作完成《纯真博物馆》之后举行了这次演说,所以他直接举了博物馆的例子,他很早就有想法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座个人博物馆,后来在写作工作室附近的楚库尔主麻区买下了一座废弃的建筑,将这座1897年的建筑改造成了博物馆空间,在这个博物馆里,帕慕克搜集、购买了很多物品,它们是1975年至1984年很多普通家庭用过的物品,包括各种旧药瓶、一袋袋纽扣、国家彩票券、扑克牌、衣服和厨房用品。为什么要收藏这些物品?帕慕克是为了写作,在他看来,这些物品不是只有纯粹的“物性”,而是真实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是情感的存在,他将这些物品写进了小说中,变成小说中的物品,就在于让读者的想象力参与进来,就是要把不同的人生展示出来,就是构建那个隐秘的中心,“小说家努力传达他个人的世界观,同时也通过他人的眼睛观看世界。”小说家完成小说是为了呈现这个中心,而读者进入小说是为了探寻这个中心,写和读并不是要形成对主题理解的同一性,而是在共同发现和构建这个中心,“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中心之间的距离显示了小说的精彩和深度。”
写作和阅读都是将现实的材料融入到这个中心,阅读和写作也都是在中心中发现生活的意义,这种融合在本质上也是将天真的和感伤的结合在一起,诺顿演说之后有人问帕慕克,“你是天真小说家还是感伤小说家?”帕慕克说:“对我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理想读者当然也是如此,在这个隐秘中心建构的世界里,不管是殊途同归还是同途殊归,不管是异向的寻找还是异形之词,它们最终还是一体的:在想像中再现,在想象中创造。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