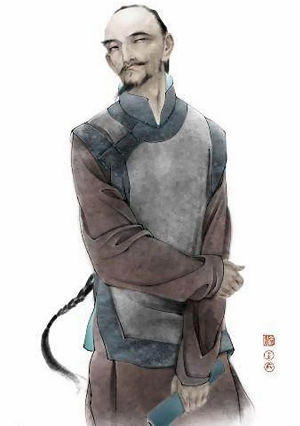2025-10-02《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得读一切书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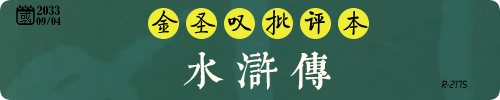
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
——《序三》
11岁时因患小病告假出塾便以书为消息,从《法莲华经》到《离骚》到《史记》,再到《水浒》,终于获得一片新天地,“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12岁时得贯华堂古本,边日夜手抄,然后“谬自评释”,最终成为今本。从11岁时发现新天地,到12岁痴迷于《水浒》,经久岁月和《水浒》结下不解之缘,对于金圣叹来说,《水浒》的魅力就在于其书其作者,“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在他看来,“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之所以从《水浒》中看到了文章之精严,金圣叹遂将其看作是“读一切书之法”,这一切之法不仅对于自己来说如此,更在对天下学者来说是一条大道,“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实际上这种读书心得传递出两种信息,一是金圣叹对《水浒》及其作者施耐庵给予极高评价,“第五才子书”的称呼既是对文本而言也是对作者所言,他在《序一》中就阐述了什么是“才”:“才之为言材也。”以材而为才,“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另一方面,“才之为言裁也。”以裁而为才,“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有才不是构思、立局、琢句、安字这些表面功夫,而是体现一种心手同至的境界。金圣叹分为几种不同的境界,“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真正有才之人,“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
在提出今人之标准和古人的境界的不同,金圣叹无疑批评世人的苟且,“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他把施耐庵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董解元之书都看成是才子之书,就在于他们能在心尽气绝、面犹死人之难时能让才“前后缭绕”,方能成书。但是金圣叹对《水浒》又另眼相看,之所以天下文章无出《水浒》之右者,就在于它成为了“文章之总持”:他在《读第五才子书》中就指出了《水浒》的方法和《史记》相同,但是又胜于《史记》,“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史传和小说创作的不同,“《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金圣叹在回目之前的评点就指出,“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
| 编号:C24·2240805·2162 |
而这也指向了金圣叹对于施耐庵创作主旨的阐释,《史记》是“缓急人所时有”,这是司马迁著书的旨意,而施耐庵却是保暖无事中伸纸弄笔,于是寻了个题目,然后写出锦心绣口,这便是施耐庵做书的“心胸”,“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实际上这里金圣叹已经从《水浒》中读出了小说家自由创作的心境,而这种自由创作也让这本书成为叙事学的一种典范。《水浒》和《史记》不同,是体裁相异所致,但是《水浒》和其他小说类比呢?金圣叹认为,《三国》热人物事体说话太多,“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则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更要命的是,《西游》中遇到难题,都是南海观音来救了。《水浒》超越《三国》《西游》就在它的“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就在于他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鲁达既有粗鲁也有精细,李逵则是“天真烂漫到底”,林冲“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阮小七则是“第一个快人”,如此等等;当然,《水浒》之魅力更在于它丰富的文法,有倒插之法,就是将后边咬紧蓦地插到前边来,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都是如此安排,有夹叙法,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就是此例,有草蛇灰线法,武松景阳冈大户就有许多“哨棒”字,“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还有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
关于《水浒》之文法、之结构、之人物,在金圣叹每回的细细点评之处更可观之,他以小说家的眼光透过文本表象深入《水浒》之本质,从而揭示了“为读一切书之法”,更让《水浒》从故事变成了真正的文学。从结构上看,他在《楔子》中就指出如何“看书”,看书的目的就是洞悉著书者的意图,“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所以看书就要知道什么是得意处和不得意处,什么是转笔处和难转笔处,什么是趁水生波处,什么是翻空出奇处,什么是不得不补处和不得不省处。比如楔子,在金圣叹看来,“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而中间又有奇楔:《水浒》以诗起,“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这便是这部大书的诗结,即以“太下太平”起,呼应最后卢俊义从梦中闪开眼,看见牌额上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写到嘉佑三年三月三日,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金圣叹认为年月日合为九数,是为数之穷也,而穷生变,所以,从这句话就可看出“变出一部《水浒传》来”;洪太尉游山,“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在这里施耐庵先写风次写吼再写大虫,除了是文笔的运用之外,则是“初开簿第一条好汉”,接着洪太尉继续前行,“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写得出色。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也是先写风次写响再写蛇,文笔运用之外,“开簿第二条好汉”,第一条好汉是大虫,第二条好汉是花蛇,暗含着此后的线索,因为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引出的梁山第一人就是史进,而史进遇到猎虎李击,李吉就告知在少华山上没有獐儿、兔儿,史进却充满疑惑,“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金圣叹点评说:“以獐儿、兔儿引出虎儿、蛇儿,曲折之笔。”因为接下去李吉就说出了原因,是因为一伙强人扎下了山寨,聚集着喽啰,为首的三位大王,第一个叫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则是“跳涧虎”陈达,第三个是“白花蛇”杨春,这是梁山伯一百单八人的“三地煞”,而“跳涧虎”和“白花蛇”不正呼应着洪太尉游山所遇见的大虫和花蛇?“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檃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檃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
| 金圣叹:《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 |
这便是“开簿第一条好汉”和“开簿第二条好汉”在结构上的体现?而洪太尉在遇见大虫和花蛇之后,真人对他说:“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这也意味着“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即一百八人“并不伤人”,那个牧童正是天师,“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这也奠定了一百八人都是“额外之人”。洪太尉游山之中强行进入伏魔殿,又打开了陷在泥里的石碣,“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止,奇绝。”打开石碣一道黑气放出,冲到半天里三座百十道金光,这便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组成的一百零八将,“他日有称我者,有称俺者,有称小可者,有称洒家者,有称我老爷者,皆是此句化开。”而在结构中,整部《水浒》即以石碣为起始,最后则是石碣为终止,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中宋江就名人掘开泥土,不到三尺深浅,就看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数文字,这便是“以石碣止”,金圣叹评点曰:“—部天书以石碣始,以石碣终。章法奇绝。”
除此之外,第七十回除了忠义堂石碣受天文而排座次之外,还有最后卢俊义惊恶梦,“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在金圣叹看来,这最后一梦也是结构安排上奇绝的体现,“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它所呼应的那个起始之梦就在第十三回,晁盖对吴用说起自己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还有斗柄上的一颗小星化作白光而去,这是七星聚义的开始,金圣叹将此梦看作是梁山泊聚义的真正标志,是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处”而晁盖是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人”,他的梦就是一百八人的梁山泊之梦,但是这个梦所证明的梁山泊故事“都无实事”,因为一百八人的故事声色烂然,却起于一梦,“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乎,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从晁盖之梦开始,到卢俊义之梦终结,“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
从“天下太平”而起,到“天下太平”而终,从石碣而始到石碣而终,从梦始到梦终,这种种的奇绝章法都体现了施耐庵在整体布局上的前后呼应,但是当金圣叹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不仅仅只是在文法和结构意义上的,这是金圣叹对《水浒》善读的体现,而这种善读已经超越了施耐庵的文本,它已经转变为金圣叹的文本,“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这种种的结构所体现的就是“大眼节”,“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在这里金圣叹其实已经从纯粹的阅读和点评转变为对第五才子书的“改造”:为什么《水浒》一书从“天下太平”而起到“天下太平”而终,从石碣而始到石碣而终,从梦始到梦终?因为这是符合金圣叹的文本结构,而这种符合论就是著名的“腰斩”而留下七十回本。一方面金圣叹以小说家的眼光删减了每回的开篇诗、“但见”“有诗为证”后的韵文,减弱全知全能的声口,就使得叙事流畅,文气连贯,这当然是一种叙事学的改造,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腰斩”一百回本或一百二十回本而成七十回本,在金圣叹看来这是《水浒》唯一可以流传的版本,而这已经不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改造,完全体现了金圣叹对于水浒英雄归宿的一种理想主义表达。
手头有两部《水浒传》,一部是以明末杨定见序袁无涯刊的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传》为底本的《水浒传》,另一部则是金圣叹批评本的《水浒传》,对比阅读,百二十回本的引言成为了七十回本的楔子,但是引言在“有诗为证:万姓熙熙化育申,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中作结,之后转入“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开始的第一回,没有“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甚么?”也没有“一部七十回正书,一百四十句题目,有分教: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蛟龙。毕竟如何缘故,且听初回分解。”这一切都构成了金圣叹的“楔子”。而整部《水浒》,经过金圣叹腰斩之后以《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结,卢俊义梦醒之后吓得魂不附体,睁眼看见堂上的匾额就是“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在金圣叹看来这才是“真正吉祥文字”,到此作结,当然没有了百二十回本之后的重阳节菊花之会,也正是在筵席之中宋江大醉,然后叫人取来纸笔写下了满江红一词,然后在乐和单唱中说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而这一句话就变成了水浒关于招安的不同派别,武松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而李逵怒目圆睁:“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将桌子踢得粉碎。
可以说,宋江大醉中写下满江红说出心中招安的想法,以及武松和李逵等人的反对,是一百二十回水浒传的一个经典名场面,也是水浒英雄命运的重大转折点,而金圣叹就是从这里“腰斩”了水浒,为什么金圣叹要如此腰斩?当卢俊义做完梦后看“天下太平”四个青字,金圣叹电平为“真正吉祥文字”,是因为“天下太平”注解着一部水浒英雄的归处,既然是归处,何必走向太平之外的“招安”结局?这一玄机在金圣叹看来更意味着古本《水浒》原来的面貌,“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七十回之后的故事不仅是画蛇添足,更是一种改窜,而这种改窜就是如百二十回本那样把“忠义”二字附注于《水浒》之上,“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
为什么《水浒》不应该是一部“忠义”之书?在《序三》中金圣叹阐释了“忠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在他看来,“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但是施耐庵的《水浒》从题目上来看,就是远离忠义,“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离忠义之庙堂而成江湖,那么就是一种凶物、恶物,为天下之共击、共弃,如果说水浒是一种忠义,那么整个国家就没有了真正的忠义,甚至是一种反忠义,“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的《水浒》,如果冠以“忠义”,“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这就是一种不“善读”的表现,而且会带来祸害,《水浒》的真正意图就是:“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金圣叹要削“忠义”而成《水浒》,就是真正从表象看本质,“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就是一种明志:“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
金圣叹的这种观点既体现在他对整部水浒的文法和结构的解读上,更体现在对水浒人物的点评上,“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一百八人有一百八人性格,但是性格的背后所体现的却是施耐庵之志。他在《读第五才子书》中把一百八人分成上上人物、上中人物和下下人物:鲁达、李逵、林冲、吴用、花荣、阮小七、杨志、关胜都是上上人物,秦明、索超、史进、呼延灼、卢俊义、柴进都为上中人物,在这里金圣叹把武松虽定为上上人物,但却是上上之上上,是天神,是天人,而宋江则是下下人物——武松和宋江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这种对人物的定位其实就体现了金圣叹腰斩之志。在宋江之前,对于梁山好汉聚义之事,金圣叹找到了他们的“初心”,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史进在少华山有一段表白,“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这就是史进的初心,史进的初心也是一百八人的初心,这初心就表现在“讨个出身”,就是不被“点污”,但是那些英雄好汉却最后落草为寇,“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水浒英雄都有不被点污的初心,但是水浒英雄最后都成了落草为寇的凶物、恶物,金圣叹质问“谁之过”?把晁盖看成是提纲挈领之人,晁盖之梦看成是提纲挈领之梦,金圣叹的这一提纲挈领其实指向的正是“谁之过”的问题,一方面一百八人之事迹从梦开始归于梦,“知无一而非梦也”,这个梦其实就是忠义之梦,“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而另一方面,这梦更是将“初心”真正点污了,而这种点污全因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他就是下下人物之宋江。第十七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是全书入宋江传的开始,“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然后介绍他的为何被称为“及时雨”,这一段对于宋江的介绍是“大书”,在一百八人之中这是一个特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为什么宋江之传会成为一书之纲纪?因为他以未入水泊的“体制”之人做出了一件对水浒来说重要的事,那就是私访晁盖,“私访”的行为证明了宋江的真正用意,证明了忠义之荒谬,证明了水泊梁山初心之点污:“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他在浔江楼题反诗事小,但私访晁盖却是事大,“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如果说宋江是忠义之人,那么他不会放走晁盖,而他放走了晁盖就证明他不是忠义者,不是忠义者就自然成为了权术者,成为了群贼之魁,这就是宋江通天之罪,一百八人也从此从这一初心变成了为天下共击、共弃的凶物、恶物,“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可以说,金圣叹之后的点评处处体现他的“贬宋观”:第二十五回施耐庵写到了武松斗杀西门庆,一方面他在这里就表达了武松“绝伦超群”的存在,“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日第一人,不亦宜乎?”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宋江为对比,如果鲁达是阔人,那么宋江就是狭人,林冲是毒人,宋江就是甘人,杨志是正人,宋江则是驳人,柴进是良人,宋江则是歹人,阮小七是快人,宋江则是厌人……他更是假人、呆人、俗人、小人和钝人,武松绝伦超群,宋江则是比不上一百七人任何一个;宋江被称为及时雨,在金圣叹看来他其实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以银子为之张本”,这就是他的权术,“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何来青天之坦荡,何来明月之皎洁,何来忠义之根本,“以银子为之张本,而于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
武松和宋江形成了一大对比,李逵和宋江更是构成了完全的映衬,李逵出场那一句“干你鸟事!”痛快淋漓,在金圣叹看来更是“骂尽天下”的标志,而李逵的天真就是为了体现宋江之权术,《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李逵大叫:“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金圣叹认为这里偏写李逵之爽直,借以衬托宋江之权术,“一个跪说,一个斧砍,谁是谁非,人必能辨。”第四十二回《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处处体现两人的对位写法:
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倒。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书;李逵遇鬼,见两把板斧。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天书,定是自家带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带来。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到底无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吃仙枣,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愿见子为盗,李逵娘不得见子为官。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还时带三卷假书;李逵取娘,还时带两个真虎。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盗,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联又绝倒。
同样,晁盖和宋江的对位法也极为精彩,同样在四十回中,“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而宋江推脱,金圣叹认为宋江句句都是权诈之极,“让晁盖,还只是论齿,然则馀人可知矣。俨然以功自居,真乃咄咄相逼。”当晁盖终于坐了第一位,宋江开口,金圣叹点评:“看他毅然开口,目无晁盖,咄咄逼人。”当宋江说出“休分功荣高下”时,金圣叹认为这一句就将晁盖从前的号令都推倒了,“别出自己新裁,使山泊无旧无新,无不仰其鼻息。”宋江之后让旧头领去左边心头领区右边,金圣叹连发“贼!贼!”等评语,然后一句“尽入宋江手矣”便展现了宋江之权术。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中箭身亡,看看金圣叹对这一情节发展中的点评:当晁盖决心去打曾头市时,施耐庵写道:“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金圣叹点评曰:“上文若干篇,每动大军,便书晁盖要行,宋江力劝。独此行宋江不劝,而晁盖亦遂以死。深文曲笔,读之不寒而栗。”饮酒之间起了狂风,师奶爱写道,“众人见了,尽皆失色。”金圣叹点评:“大书众人失色,以见宋江不失色也。”晁盖引兵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打探消息,“此语后无下落,非耐庵漏失,正故为此深文曲笼,以明曾市之败,非宋江所不料,而绝不闻有救援之意,以深著其罪也。”所以金圣叹认为这正是宋江之罪;晁盖受伤水米不能进口,宋江守在床前啼哭,“俗士读之,便谓宋江好,不知正极写宋江之诈也。”而且金圣叹认为,“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人。”之后施耐庵写道:“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金圣叹点评:“宋江独哭,难乎其为下也。众人不哭,难乎其为上也。独哭,宋江今日之恶也。不哭,宋江平日之恶也。”最后晁盖去世,小说写道:“宋江焚香已罢,林冲、吴用搀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金圣叹认为,写到林冲和吴用搀扶宋江就是写出了宋江之权诈,其中的“居中正面”四字“丑不可当”,“夫文字,人之图像也。观其图像,知其好恶,岂有疑哉?”
在第五十七回的卷首点评中,金圣叹列举了宋江的十大罪状:
人欲图报朝廷,而无进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于强盗。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骫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郓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惩,便当大戒,乃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贻大僇于老父。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于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 黄信、秦明亦罗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于黄钺、白旄、朱旙、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
这十大罪状也正是否定了宋江是忠义之人,水浒是忠义之举,甚至宋江所说的招安也完全是权术,“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在对宋江的评点上,金圣叹几乎恪守一种定位,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体现了太多的偏见,而实际上金圣叹之忠义观也体现了他的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水浒英雄在宋江的带领下忘了初心成为了寇贼,的确违背了忠义,即使宋江口口声声说招安,也不是为了忠义,“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也。”所以他腰斩水浒就是取消了招安,就是删减了“忠义”,而卢俊义之梦就是对腰斩之必要性的解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对于一齐处斩的解释,化身为捕贼人的嵇康回答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
金圣叹点评曰:“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卢俊义之梦终结,水浒传也结束,“一齐处斩”也是金圣叹对于忠义之“腰斩”。但是另一方面,金圣叹之所以将水浒看成是第五才子书,除却对于施耐庵之才和对文本的赞誉之外,更是寄托着他的自由思想,他倡导的“性即自然”正是效法嵇康的风度,而他率性的个性所要反对的正是礼教,正是君权。所以金圣叹既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自我主义者,又是一个信奉“忠义”的地主阶级民主派,在这种矛盾思想中,他寄希望水浒英雄般众生平等,又嫌恶权术,所以在文本中快意怅然表达自己的看法,现实中却又陷入命运的困境之中,“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而当金圣叹最后在“哭庙案”中以叛逆罪判处斩首,这何尝不是一个“郁郁乎”的文人被所谓“忠义”无情“腰斩”的悲剧人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0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