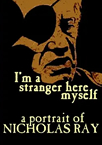2025-09-30《这儿我不熟》:以冷漠回击世界的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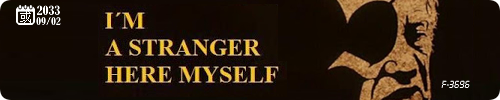
最后的定格,画面中是花白头发的尼古拉斯·雷,是独眼观世界的尼古拉斯·雷,是倾斜着身体的尼古拉斯·雷,大卫·赫本用这样的“姿态”作为纪录片最后的画面,似乎在表达着某种时间被放大的永恒意义,这也是他对于雷的某种定义:“每部电影都是他的一次灾难,他在电影中都是陌生人。”在自己制造的电影灾难面前,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雷的姿态所传递的就是一种坚定,一种肯定,以及一种确定,按照雷自己的说法:“电影是收集的艺术,电影是世界上最好的沟通艺术。”
“这儿我不熟”,实际上对于我来说,尼古拉斯·雷也是一个不熟的陌生导演,仅有的一部被观看的电影是他和维姆·维德斯合作的《水上回光》,这部拍摄于1979年的电影也是雷的最后一部电影,影片杀青后不久,雷就因肺癌晚期逝世——最后一部电影就像他生命的一次“回光返照”。在写影·1975电影作品的补看中,不久前观影的是《与弗里茨·朗一席谈》,竟然发现雷和弗里茨·朗有太多的神似,其中之一就是标志性的黑色眼罩,而且都是右眼,当他们面对镜头,很自然就形成了一种“独眼”的观看方式,这种“独眼”是一种生理型特点,其实也是特立独行的某种标记。弗朗茨·朗的大部分电影都已完成观影,尼古拉斯·雷却只有最后一部回光返照的纪录片,对他的“不熟”却被纪录片的引语拉进了一个好奇的世界:“有戏剧、诗歌、绘画、舞蹈、音乐,今后有电影,电影就是尼古拉斯·雷。”这是让-吕克·戈达尔在1959年所说的话,作为反叛者、革命者和开拓者的戈达尔对雷评价如此之高,对他陌生似乎是一件不应该的事。
这部纪录片也可以看作是走进雷世界的一个进口,但是只有40分钟的视频也无法呈现这个代表电影的艺术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观,甚至这部纪录片只是大卫·赫本对雷在拍摄《我们无法再回家》时的一些片段记录,在定格的画面之后打出的字幕是:“《我们无法再回家》几个月后在戛纳电影节上映。”雷的电影亮相戛纳电影节,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戈达尔对他推崇备至,这也可以看做是好莱坞导演和欧洲电影的对话,而对于雷的电影风格,纪录片中弗朗索瓦·特吕弗的评价更为具体,“我觉得尼古拉斯·雷吸引我们的是来自这个好莱坞导演的欧洲感性,尤其是主角的脆弱性。”他举例说到了《荒漠怪客》,“我对它一见钟情,这是我看过唯一一部苦乐参半的男欢女爱电影。”戈达尔的推崇、特吕弗的赞誉,都是对好莱坞“欧洲感性”的一种肯定,而这种感性在特吕弗那里时主角的脆弱性,是苦乐参半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注解着雷和世界的微妙关系。
| 导演: David Helpern |
1947年至1962年,雷执导了多部电影,在好莱坞立足,但是在西班牙拍摄《北京55日》时因突发心脏病而终止了电影生涯,此后十多年雷一直远离电影,直到1969年雷回到了美国,拍摄了关于芝加哥“阴谋审判”,这次拍摄《我们不在回家》也是和学院的学生边进行教学讨论边拍摄。那十年被赫本称为雷的“冬眠期”,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而回来之后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因为心脏病而离开电影,遭遇眼睛失明的痛苦,以及最后因为肺癌而逝世,雷的身体当然遭受了不同的病痛,但是在他的电影人生中,所遇到的困难远不止这些,比如在好莱坞如何立足,比如电影拍摄时的资金问题,比如和制片、演员的矛盾,比如自己的婚姻问题——在拍摄期间,他也和女学生莱斯利发生了争论,甚至变成了争吵,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微妙,而充满火药味的争吵也并非仅仅是对电影的不同理解。
“他在电影中表现那些被社会逼近的人,他自己也是。”这是纪录片中约翰·豪斯曼对他的评价,在豪斯曼看来,雷脆弱、敏感,具有攻击性,又害羞,这些性格其实体现着雷和世界的相处方式,一方面社会不断逼近他,电影投资、疾病、婚姻,都是外在力量对他的影响,他的敏感和脆弱甚至加重了社会的逼迫感,而另一方面他必须采取一种反击的态度,既和世界保持足够的距离,又不时发起攻击,所以和世界就形成了复杂的双向态度:是世界的冷漠让他不得不做出改变?还是他以自己的冷酷回击着社会?或者是在社会逼迫他时他同样选择了逼近和战斗,所以可能的结局就是两败俱伤的悲剧。
“这儿我不熟”是雷特立独行的标志,但是他所说“仍需妥协”又变成了一种无奈,在镜头前雷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但是他的目光中分明是一种感伤。当赫本说他的电影是一次次的灾难,他永远是电影中的陌生人,这是毫不妥协,这是坚持自我,这是艺术和现实之间做出的选择,但是最后的定格也成为赫本的一种“姿态”:以悲伤的方式为雷画下令人动容的肖像,这是对一个悲剧人物深刻而感伤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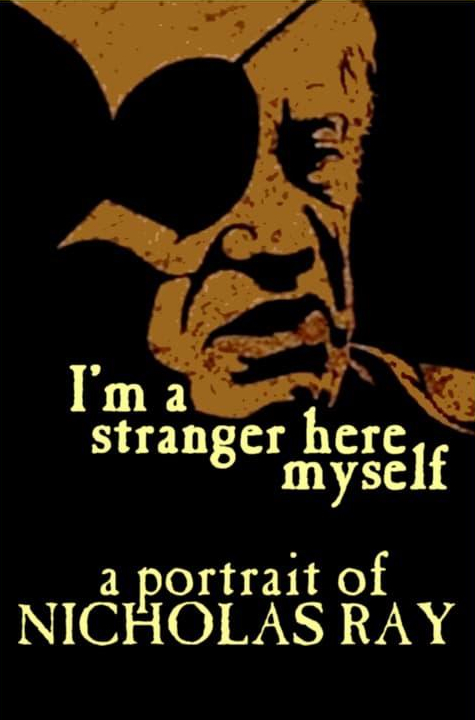
《这儿我不熟》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82]
顾后:红旗下的“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