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4《对活人的治理》:我生产自己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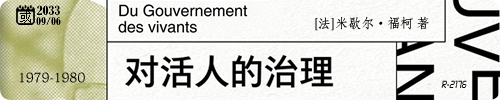
为了被迫揭示关于自我本身的真相,人们不再需要成为国王,不再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不再需要迎娶自己的母亲,不再需要控制瘟疫。
——1980年3月26日
成为国王、杀死自己的父亲、迎娶自己的母亲,这一切无疑是属于俄狄浦斯的悲剧,而俄狄浦斯之所以通过被茫然无知的命运所裹挟,就是为了探明真相,使得“那不可知之处、隐蔽之处、不可见之处、无法预料之处,使得真理自身得以涌现”,但是看上去是属于自我的真相得以显现,实际上这种真相所指向的依然是国家治理下的目的,那就是使得忒拜城免受瘟疫的灾难。俄狄浦斯在悲剧中让真相显现,让国家平安,而我们却不需要成为国王,不需要弑父娶母,就能发现自我本身的真相,当福柯将俄狄浦斯和我们并置在一起,实际上是要进行三重的转变。
第一重转变无疑和这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有关,在福柯的语境中,《对活人的治理》中的“活人”对立面不是“死人”,而是国家,“对活人的治理”相对的当然就是“对国家的治理”,这就是福柯在关于“思想体系史”的教学中完成的转变。在福柯看来,“对国家的治理”体现的是一种治理性的意义,治理性之于国家,就像隔离技术之于精神病学、规训技术之于刑罚体系、生命政治之于医学制度,都是思想的一个支点,它所撬动的是现代治理化国家,而要研究现代治理化国家,必须先研究治理性,要研究治理性,就必须研究对人的治理,也就是说,福柯的这门课所要解决的就是早中期的知识-权力观转变到“以真理而实施治理”的观念,而要从国家治理向“活人”治理的转变,靠的就不是强权,不是暴力,不是国家机器。他1980年1月9日的第一堂课中就指出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他认为,权力的行使总是伴随着真理的展现,它们构成了一种本质关系,他从“alethourges”一词出发创造性地虚构了“alethourgia”,这就是“真理之展现”,也就是“诚现”,它通过一系列可能的言说程序或非言说程序,揭示出被视作真理的东西,可以说,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真理,同样没有真理或没有真理展现的地方就不会有权力。
但是前期的福柯关注的重点是国家理性下的权力体系所构造的知识,“国家理性的形成,完全是对真理之展现所进行的一种重组,而这种真理展现,又离不开权力行使和宫廷机构。”正是从俄狄浦斯的悲剧解读中,福柯意识到要从老生常谈的知识-权力体系中完成转换,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知识-权力具有的局限性就是把现象的客观知识作为形式,根据国家或社会来界定各种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或社会成为了知识的对象、自发过程的场所、暴乱的主体和恐怖所蛊惑的对象,它的分析多多少少是由意识形态所组成的。这一次福柯要“另辟蹊径”,从真理展现的“额外部分”来考察“对活人的治理”,从而提炼出另一种知识观念。但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核心意义上,也是一个关于国家治理的知识-权力体系,也是一种为了国家获救而实施的君主权力并在这种权力下进行真相探寻,但是在俄狄浦斯王故事里,国家治理和“对活人的治理”恰好形成了两种真理机制,它们形成的张力却为“诚现”提供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进路形式。
“《俄狄浦斯王》,作为彻头彻尾的悲剧,它乃是一部关于发现的剧作,一部关于真相的剧作,亦即一次诚现,而且是特别激烈的、根本的诚现,因为正是诚现本身成了这部悲剧的动力。”这根本的诚现就是要让真相被说出,那么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被说出?或者说贯穿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言说程序是什么?俄狄浦斯的权力行使和真理展现又如何被结合起来?福柯考察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这出戏剧,他认为揭开真相这根链条的就是六个“半”法则:一个是阿波罗代表的神和忒瑞西阿斯代表的占卜师,他们各掌握着一半的神谕,两个人一起言说了神谕,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出真相,或者真相程序只是完成了神话的一半、预言的一半、神谕的一半;真相程序的另一半则是凡人的一半,它又被分成两个小半,第一个小半和拉伊俄斯凶杀案有关,第二个小半则是那个唯一幸存的证人。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真相程序:神的一半是宗教诚现、预言诚现、仪式诚现,它与神谕、卜筮的一半组合在一起;人的一半是回忆和调查的个人诚现与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各自掌握一点的凶杀案的一半组合在一起;身世的一半则是科林斯报信人之口和隐居在忒拜城的奴隶之口结合在一起,“这样,真理的持有者便有六个,他们两两组合,互相补充、互相搭配,互相联结。”
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让真相显现,或者说他探寻真相,体现了两面性,一方面,他所要揭示的是事件本身,它包括各种遭遇、各种不幸以及各种幸运,它交织着事件、行为和人物,而另一方面,揭示的目的是要逃避神谕,从而让忒拜从诸神的愤怒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就是真相的掌握者,即使他所面临的是最后的判决,但是他让自己摆脱了诸神加之于他的命运,也让忒拜不遭受瘟疫,所以这里的真相机制就是一种专制君主式的运用,“俄狄浦斯正是在专制君主权力的背景之内,来使这种程序运转的,换句话说,这种真相程序关乎唯一的掌握者,这个掌握者试图运用真相,以便亲自实施治理,以便率领城邦之舟和他自身之舟,通过命运之礁,正是这种运用作了判决”,可以说,俄狄浦斯探寻真相借助的是先有的权力,而且他探寻真相本质上也是关乎他的权力,“于他而言,这个游戏并不是真相游戏,而是权力游戏。”——它所体现的就是福柯前期研究中的知识-权力体系,就是“对国家的治理”。
| 编号:B83·2250901·2345 |
但是,俄狄浦斯在福柯看来,具有一种转变的意义,那就是从一个无知者变成了一个有知者,一方面,这种转变关乎教育、修辞、说服技艺,是古希腊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修辞学以及预言运用的核心,更是雅典民主制的全部问题,是治理城邦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当俄狄浦斯说出“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无知者,而当他通过在现场的你们和应该知道事情真相的你们来探寻真相,就是渴望成为一个有知者,从这个意义上,真相就是在一种言说的系统中,“言说者与真理的来源、起源、根源的这种同一”,所揭开的就是一种主体和真相的关系,而“对活人的治理”的核心就是构建主体和真理展现的程序:真理展现和主体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主体如何自行展现真理;主体性的形式所进行的真理展现,效果超出了知识的直接实用效益——主体融入到真理展现的程序之中。
主体融入在诚现程序之中,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在福柯看来有三种,一种是真理的操作者,第二则是真理的目击者,第三是诚现对象自身这一角色,形象地说,就是演员、证人和反思对象:演员在真理行为中就是用他的话语将处于阴影和黑暗中的事物得以显现,并将它带到光明之中;证人意味着在镇里行为中我“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的目光睹视它”;作为诚现的对象,他所发动的真理展现关键就在于他。主体就是真理行为的主体,福柯区别了反思的真理机制和非反思的真理机制,非反思的真理行为是以信仰、信仰行为和信仰承诺为形式的真理行为,而福柯所关注的是反思的真理机制,那就是由义务加以界定的机制,只有在义务中,个体才能确立自己与知识的持久联系,个体才能揭示自己内心深处令他们困惑的秘密,个体才能展现这些真实的秘密,并通过行动达到超越只是的效果,即解放的效果。这种机制,福柯从基督教主义出发,归结为坦白机制,信仰机制和坦白机制不是异质的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联系,“在这两种真理机制,即信仰机制与坦白机制之间的特殊张力,—直贯穿着基督教主义。”
实际上,在义务的层面上,福柯就已经进入到了真理的“额外”部分,它是一种额外的强力,就是真理的强制力,恰恰是这种看起来是额外却是强制的力量,就在真理自身中,“在真理展现中约束我的、决定我角色的、在真理展现程序中使我服从的,正是真理本身的结构。”而这就是真理的自明性,那么主体在融入真理机制中如何成为操作者、证人和反思的对象?三种主体,对应的是基督教主义中的三种真理展现方式,那就是洗礼、悔改和良心指导。洗礼是印章,是重生,是启蒙,是和上帝保持直接的和总体的知识关系,就像上帝的光照亮上帝的同时也照亮我们,但是洗礼这一行为如何体现着主体对真理机制的融入?福柯从德尔图良的《论洗礼》的解读中指出,德尔图良认为洗礼界定了灵魂净化和真理入口的关系,它把主体构造成了知识的主体,也以某种方式成为知识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教学意义上的,而是在考验意义上的:当基督徒准备洗礼以及洗礼之后,他知道自己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从不放弃恐惧,“他必须一直担心,危险从未平息;他从不安全、从不松懈。”正是危险和恐惧的确定性,对真理也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种信仰机制的建立,而另一方面,主体的焦虑从未停止,他无法肯定自己是完全春节的,也不敢相信自己得到拯救,“恐惧在历史上第一次——恐惧,乃是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即针对自己而言的恐惧,恐惧我们之所是,恐惧[可能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福柯所认为的主体性,主体性就是自我和自我的关系,就是自我对自我的修习,就是自我在灵魂深处所揭示的真相,它甚至是一种主体不断运动的真理,“是灵魂本身朝着善运动,尽力摆脱邪恶,与邢恶斗争并练习打败邪恶的真理。”这种运动就是灵魂的转变,“灵魂通过这种运动、围绕自己转动,把目光从低处转向高处,从表象转向真理,从地上转向天上,经过这番过渡,在这种转动一转变之中,从黑暗转向光明。”而真理就是灵魂和存在“亲缘性”的一种展现,在洗礼中修习,在修习中认识你自己,而且是在与他者的战斗中枯朽、认识你自己,这就是真正的主体性的凸显,“若不以苦修为前提,若不以同他者的斗争和战争为前提,若不以对自己及他人展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为前提,则我们不可能通达真理,主体性与真理之间不可能有关系,主体性不可能通达真理,真理不可能在主体性中发挥作用。”
这种在斗争中凸显主体和真理的关系在悔改中也得以体现,如果说洗礼是主体与自己的决裂从而抵达真理,那么悔改就是主体与真理的决裂。洗礼已经完成了灵魂的净化,为什么还会有悔改?悔改是不是一种“再次堕落”?“已经抵达真理的主体,怎么还可能丧失真理,在这种实质上被视作不可逆的知识关系中,怎么还可能发生从知识到非知识退转,从光明到晦暗退转,从完善到不完善退转以及罪过之类的事情?”恰恰就是悔改的“再次堕落”展开了真理行为,一方面是悔改者作为对象的真理程序,修会、主教或者其他人通过整理程序让悔改者悔改,另一种是更为重要的反思性真理程序,通过永恒向度的认罪仪式,悔改者自己成为了真理展现的操作者,展现了作为罪人的真理本质,也就是说,在头上撒灰尘、伤害自己、喊叫、哭泣等认罪行为中,悔改者展示自己作为罪人的存在,他走在死亡道路上,只有在展示对世界的快乐、财富和满足的抛弃中,才能让“自己之所是”成为一种真相,从而抵达真理。
洗礼是在进行灵魂的考验中展开真理行为,倘若他再次堕落,悔改就是在展现自己的真相时展开真理行为,在这里福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两种程序之间的耦合就是从无知者到有知者的自我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在洗礼时看不到,在悔改时也看不到,于是他提出了第三个主题,那就是修行和通过修行不断完善的主题,“我认为,要真正地理解陈述罪恶与探究自我之间的耦合,只有把它置于它所起源于其中的实践之内,或至少是它所达到其发展的最高形式的实践之内”,也就是说自我对自我的修行,这就是良心指导,它没有洗礼的强制,也没有悔改的惩罚,它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检查、修行和言说,“言说关于自己的一切,无所隐藏,绝不凭自己欲求任何东西,服从一切”,这一实践机制才是真正的主体性表现,甚至它就包括了洗礼、悔改在内的反思性程序的三个原则:无目的服从原则是倾听别人,不断检查的原则是观察自己,彻底坦白原则是向别人言说自己,它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三角形组织结构,在福柯看来,这是真理与主体性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借用“笛卡尔的恶魔”完成了主体性的一次奠基,“既然你可能总是自己被自己所欺骗,既然你自身之内总有一些东西可能欺骗你,那么好吧,你必须说话,你必须坦白。”
这是一种永久地对自己、以坦白的形式、言说关于自己的真相的义务,福柯将这种主体的真正融入看做是“真相生产”,它是在悖论中展开的:对自我的诚现,就必须对自我进行否弃,自我否弃的同时则生产自己的真相,“而我生产自己的真相,仅只是因为我正在致力于这种否弃自己。”也就是说,对真相的生产并没有被集中于我之所是的意志,而是相反,我必须在真相中生产我之所是,因为我必须否弃我之所是,“在我看来,真相生产与自我否弃之间的这种联结,便是所谓基督教主体性的图式,更确切地说,便是基督教主体化的图式,这是一种在基督教主义中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化程序,但它有一个悖论性的特点、即在自我苦修与自我本身的真相的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结。”在洗礼中进行灵魂苦修,在悔改中对罪人进行展示,在指导中对奥秘进行探索,由此构成了福柯关于真理主体性的历史。
从国家治理到“对活人的治理”,这是福柯学说方向的一次转变,俄狄浦斯从无知者到有知者的真理探寻,福柯完成的是真理机制的转变,也许在这门课的教学实践中福柯的决定构成了关于自身的另一种转变。当人作为主体揭示关于自我本身的真相,他不再像俄狄浦斯那样被命运困住,也不必构建知识-权力,“他只需成为任意一个人就足够了。”在无条件的服从、不间断的检查和无尽的坦白中发现真理、揭示真理、生产真理,就是完成对自我的治理,但是探寻自己的真相,在福柯看来并不是确立自我对自我的“自主控制”,而是相反,“人们由此所期待的是谦卑和苦修,是相对于自我的脱离,是确立一种有助于破坏自我形态的自我关系。”不是自我控制而是自我解脱,这也许才是福柯构建“对活人治理”的主体性真理机制的最重要意义,而这也是福柯完成的自我转变。在教授这门课的时候,前后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3月,罗兰·巴特被“事物的愚蠢暴力”所带走,最后一次课那天,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宣读了葬礼悼词;4月是萨特之死,福柯出席了葬礼;更早的是一年前莫里斯·克拉维尔的突然死亡,在死亡的前一天福柯还和他讲过基督教的悔改、言说真相的义务、重生和真理时刻——似乎莫里斯·克拉维尔的死亡启示了福柯的这堂课;除了友人之死,福柯还被卷入的两起大事件,一是伊朗革命,另外则是波兰颁布的反抗戒严的团结工联运动。这些事件一定影响了福柯,他在4月份的《世界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访谈,在访谈中,福柯写道:
我认为[……]哲学是反思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一种方式。还应该补充的是、它是一种自我追问的方式: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与真理的关系、那么我们该如何行事?我相信,有数量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已经完成,或者眼下正在进行着,这些工作既改变了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这发生在一系列研究与一系列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联结之内。这便是哲学的生命本身。
访谈的题目是《戴面具的哲学家》,匿名的福柯像是“戴面具的哲学家”,一方面连续发生的事件让他开始想要摆脱政治现实,面具无疑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但是另一方面,他重新界定了哲学的使命,那就是在自我追问中探寻真理,也许这种探寻就是福柯面对自我的要完成对真理的生产,只有从自我解脱中才能探寻自我的真相,正如他在最后一堂课上所言,“如果我想知道我之所是,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中生产我之所是,这是因为我必须否弃我之所是”。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297]
思前:西游三国,宛如梦粱



